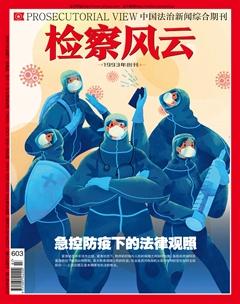感嘆號時代的詩性
楊皓
2020的冬日太過漫長,以至于素來遭受冷遇的詩句重新被賦予了溫度,友邦日本寄來的援助物資上附帶的詩句,成為了大眾熱議的話題,更是這個寒冬里珍貴的一份溫暖。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兩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友邦連連奉上的古詩詞一度引爆中國網絡,網友們更是戲稱“日本給中國開了一個詩詞大會”。
與此同時,網絡上也開始出現一些反思性的文章,集中討論中華詩歌文化失落的現狀與原因。其實,在詩歌背后,更為深刻的是一種對詩性的呼喚,期待一種隱而不昭卻可謂重要的人性品質回潮。
感嘆號時代
意圖理清詩性在當今時代的脈絡,就不得不從文字狀態說起,因為歷來文字便是詩性的最主要體現。
1948年,美國數學家香農提出了對后世影響極為深遠的信息論,其后的時光里,信息論、控制論成為了引導人類科技進步乃至人類生存邏輯的關鍵理論基礎。
文字的狀態同樣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嬗變。與信息論的邏輯一致,在當今時代,作為人類交流的語言文字,越來越注重本身的信息效用,而非表達效用。簡單來講,人們在交流的過程中,閱讀等接收文字信息的行為,越來越指向獲得信息、消除不確定性的意圖,而非文字創作者本身的表達。也可以理解為,人們把文字的實際效用提高到了首要地位,而抒情、表意等其他效用,則理所當然地被逐漸淡忘。舉一個十分直觀的例子,同樣是表現革命熱情的歌曲,《大刀進行曲》中的歌詞“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就要比《保衛黃河》中的歌詞“黃河在咆哮”,傳達了更為明確清晰的意思,不可否認前者的實際效用往往更為直接且直觀,但其中流失的恰就是所謂“詩性”的內容。為了更為明晰地解釋上述內容,在此舉一個反例,蘇聯著名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長詩《穿男裝的云》中有一句極具詩意但缺乏明確信息傳遞的句子:“天空紅得像馬賽曲,晚霞在垂死中飄搖。”
與志在于最大限度消除人類社會不確定性并傳達更多信息的信息論相一致,信息時代來到了當代人的生活中。在信息時代中,人們理所當然以更準確、更快速作為生活的直接追求,乃至最高追求。于是,我們迎來了一個網上閱讀新時代,文字的狀態進一步產生變化。如果說信息論所帶來的是“百科全書”式的科學書籍興起風潮,那么信息時代就主動解構了“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構筑理論,以碎片化、實用化、快速化來主導生活實踐。舉例來講,在我們好奇某種從未了解過的生物時,當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定會求助互聯網,幾秒之后即可解開心中疑問,文字在經歷信息論的“表意祛魅”后,迎來了自己的“閱讀祛魅”。換言之,文字不再是某種帶有儀式化閱讀的載體,而是取之即來的消除任何疑問的工具。
當消除不確定性與“更高更快更強”的信息時代人類信條相遇之后,兩者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合力的最大作用就是塑造了當今網絡當之無愧的熱詞:“定了”“重磅”“權威消息”“速看”“深度”“剛剛”“最新”……不勝枚舉的此類字眼,非常明確地體現了消除不確定性與更快、更準確的特性,無疑,這在某種程度上讓信息溝通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文字狀態暗中變化,正帶來一場情緒僭越意義的反噬。
因為更快更準確更博人眼球的需要,信息時代的網絡熱詞又相當有限,加之網絡生態下極為明顯的競爭態勢,網絡上的文章為了得到更多的關注,又無法突破信息論與更快更準確的束縛時,便只有一個選擇:訴諸情緒。但由于長久以來文字已經陷于貧瘠的狀態,想要通過文字本身的表意來喚起情緒既不簡單也不一定有市場,情緒的出口就只剩下一個諷刺的感嘆號。
于是,我們見到了當今的網絡奇觀:在千篇一律的“定了”“最新”等網絡熱詞“審丑疲勞”后,是更為令人不適的一排排連續感嘆號,當然,這既不壯觀,也不優雅。但無可否認,我們一道走入了這無奈的感嘆號時代。
詩性
“我口袋里經常裝著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隨時準備稱一稱、量一量人性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訴你那準確的分量和數量。這只是一個數字問題,一個簡單的算術問題。”
狄更斯在小說《艱難時世》中寫出了上面這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文字,可惜的是,狄更斯關于人性無法測量的警醒,似乎并未被太多人記在心里。進而可言,人們似乎樂于選擇進入一種缺乏詩性,精于計算的“美好時代”。
當疫情新聞連連轟炸的時候,其中最矚目占比也最大的當屬疫情期間的各種數字了。無數人關注著不斷變化的統計數字,各大媒體針對每天的最新數據,或撰文鼓勁,或宣傳“戰果”。在整個社會輿論圖景中,統計數字當之無愧成為了關注的中心點。在另一面,關于個體的苦難、付出、遭遇,偶爾出現一篇關于個體的翔實報道還有可能遭遇種種不測,即便引起過細小波瀾,也很快被實時更新的數字蓋過。
在美國大學某堂經濟學課程上,有過如下對話,當教師講道:“在一個有一百萬居民的城鎮中,只有二十五個人餓死在街上。”一位學生打斷道:“不管其余的人有一百萬,或者有一億,反正那些挨餓的人都一樣艱難。”日本著名導演北野武在談論到日本地震的遇難人數時,曾說道:“災難并不是死了兩萬人或八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而這,就是詩性。
與更快更準確不同,詩性從來不訴諸速度與效率,甚至不訴諸他人的理解。詩性是一種關乎每個人自己的暢想,而這看似自私的邏輯,卻出乎意料地生出了人世間最美的花朵:移情。當一個人展開只關乎自己的暢想時,就有了把自己代入別人生活的能力,亦是把自己當作別人的能力。當看到他人的災難時,通過暢想,人們試圖去理解這災難可能帶來的感受,更進一步,假借移情,人們用感受來要求自己與他人,幫助這個世界盡可能地減小災難發生的概率與帶來的損失。
質言之,詩性的自私與浪漫帶來了一種把人當作人來看的嚴肅態度。信息論的蜇傷在于,只關注那些能夠進入實用主義計算的東西,對世界有關“質”的豐富性視而不見,對人類是怎樣生活以及如何賦予人類以生活的意義視而不見。在這樣的視角下,人的多樣性和獨特性被拋棄了,人的質性差別被拋棄了,人僅僅被當作一個統計數字來看待,或者被當作一種粗糙的簡陋物體來對待。美國著名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曾這樣描述詩性:像陽光傾注到每一個無助者的周圍,它照亮了每一個曲面,每一個陰暗處;沒有什么是隱蔽的,沒有什么看不見。
我們還需要詩性嗎
反身觀察當下,在詩性愈發難尋的今天,我們還需要詩性嗎?
信息時代的人們,似乎已經尋到了一種不需要詩性暢想,也不需要自身移情的生存法則。極具代表性的是今年二月的一則新聞,一對在山東汕頭打工的夫妻因為種種原因無力撫養所生的嬰兒,無奈之下把孩子放到了醫院門口,并留下手書:“如果生存下來,一個月內一定前往福利院領回,到時多少錢一并補予福利院。”如此新聞出現后,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網絡上出現了相當一部分聲音認為:明知自己窮,為什么還非要生?
上述事件并非個例,有關網友似乎把貧窮視為“原罪”的討論也由來已久,在缺失詩性的精神狀態之下,人們理所當然地訴諸辯論、打擊、尋找借口等手段排解自身的情緒。也正是因此,如今的網絡充斥著一個非常典型的生態:調侃文化。任何事件在網絡環境中,似乎都可以變成調侃的對象。在此無意去討論調侃是否應有界限,只是必須指出,在一部分調侃中,消解了本應關注的實質性問題,讓很多本可能通過努力解決的問題成為了“消逝的苦難”。這種調侃文化風行,究其原因是在詩性移情缺位時,人類情緒的自我保護機制。當心靈的某一柔軟之地被無意觸及時,倘若不想推翻自己思維的其他種種預設,最好的方法即是輕描淡寫地調侃。所以,貧窮的問題永遠在于貧窮者自己,至于可言與不可言的其他種種,只要自己沒有親自遇到,都可當作并不存在的了。
如此,詩性也就消亡了。在這感嘆號時代,我們不妨稍作祭奠:
速看!!!定了!!!詩性快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