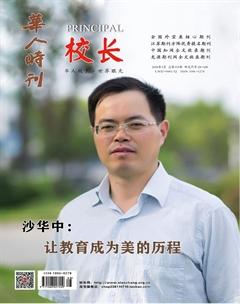每條魚兒都在乎
張正耀

一次去江蘇省興化市楚水實驗學校參加“詩與生活”朗誦會,我見到了印象深刻的一幕:壓軸節目上場了。令我眼前一亮的,是整齊的隊伍,整潔的服裝,燦爛的笑臉,這是全班集體節目,所有學生都站到了舞臺上。在欣賞他們激情洋溢、鏗鏘有力、抑揚頓挫的集體齊誦時,我突然發現隊伍有點特別,站在最前面、最中間的一位男生,個頭非常矮小,與高二學生極不般配:原來他是侏儒!我驚呆了!他不僅在大聲朗誦,而且做了領誦!認真、堅毅、陽光、自信洋溢在他的臉上,他簡直成了這個節目,不,應該是全部節目中的明星!
這位學生何其幸也!他有幸生活在一個有愛與溫暖的校園,一個充滿寬容、包容、自由的環境,一個得到充分尊重、張揚個性的舞臺。沒有人會對他冷眼,也沒有人會因而嘲諷,更沒有人會冷落乃至歧視他。他活得很自在,因為不用擔心冷言冷語;他活得很安全,因為不會遭致另眼相看;他活得很幸福,因為沒有被打入另冊。在一個教學研討會上,連續聽了四節課,我發現來會場上課的學生總是一樣多,不多不少,40個。我有點疑惑,因為年級、班級都不同,學生人數怎么會完全一樣呢?私下了解,原來是上公開課的老師把所謂的“差生”留在教室里自習了,這樣做的理由是擔心那些學生會影響公開課的質量。我很憤然:公開課什么時候也成了一種待遇?乃至成了懲戒學生的一種手段?老師怎么能任意剝奪學生上課的權利?又怎么能剝奪學生享有難得的經歷呢?當老師只在乎自己的個人表演,而不顧學生的心理感受,置學生的學習需求于不顧,那這樣的公開課,又有何意義?
有一年,我參加省四星高中復評工作,在一所學校了解到一個真實情況:對照省級評估標準,該校班級學生數嚴重超標。班額過大,影響到其它指標的達成,比如生均擁有圖書冊數,學校占有面積、建筑面積、綠化面積,生均經費投入、升學比例、師生比等許多指標都達不到標準要求。怎么辦呢?這所學校在專家組現場考察時,讓一部分學生放假幾天。而“被放假”的則肯定是所謂的“差生”。
這對那部分學生來說太不公平了!省級評估這一活動,不僅是學校的大事,老師的大事,更是學生生命中的大事,因為他們也為之付出了很多,他們為學校的創建工作也奉獻了很多,他們想做學校發展、壯大的見證人,想成為學校發展歷史進程中的建設者,而不是旁觀者。這種簡單粗暴的想法做法,會對學生造成情感上的傷害,這種傷害一旦形成,就在學生心中留下永遠無法抹除的記憶。這種公然、集體造假行為,不但有違評估的初衷,更會影響學校、教師乃至教育的形象。我們為什么不能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學生?為什么不能讓他們享有公平的待遇?為什么不給那些暫時落后的學生以改變和進步的機會?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故事:
在暴風雨后的一個早晨,海邊沙灘的淺水洼里,有成千上萬被困的小魚。一個小男孩,不停地在撿起小魚,并且用力把它們扔回大海。
有人問他:“這水洼里有成千上萬條小魚,你救不過來的。”
“我知道。”小男孩頭也不抬頭地回答。
“你為什么還在扔?誰在乎呢?”
“這條小魚在乎!”男孩兒一邊回答,一邊撿起一條魚扔進大海。“這條在乎,這條也在乎!還有這一條、這一條、這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