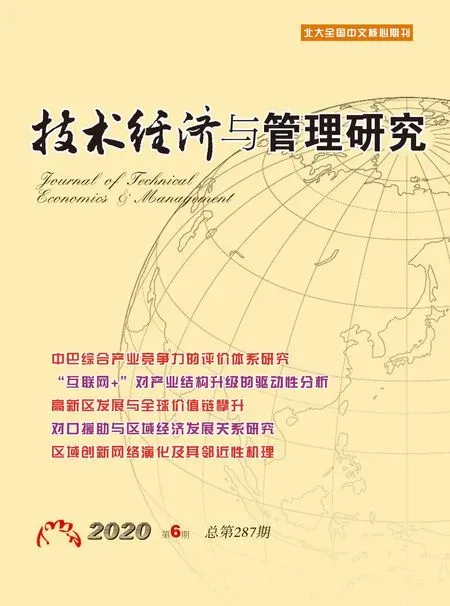區域創新網絡演化及其鄰近性機理
王平平,金 浩,趙晨光
(河北工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天津300401)
一、引言
隨著國家創新驅動戰略不斷深入推進,創新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動態流動和合理集聚促進資源配置的高級秩序演變,進而促進區域平衡發展。知識迭代和技術躍遷正成為提升區域創新能力、推動國家進步的重要動力源泉。伴隨創新活動步入復雜化、高級化,創新的動能正在釋放,創新主體間關系呈現出“多元、動態、融合”的特征,因此構建開放式區域創新網絡,成為區域共生式創新的重要途徑。
各區域內部產學研官中介等多元創新主體協同演化形成的協同創新效應和區域之間通過合作創新形成的空間關聯效應,共同構成了區域創新網絡。受西方經濟地理“關系轉向”和“演化轉向”影響,區域創新的空間格局從等級化向網絡化演變,“流動空間”逐漸取代“地方空間”,信息流、人流、技術流等“要素流”在一定空間范圍內流動,形成區域創新網絡的空間格局。在人才“擇優”、資本“逐利”、知識溢出和政策導向等多重作用下,創新活動在特定的空間單元,實現創新資源的加速配置。區域創新政策的制定者急需更為科學有效的理論指導和決策參考,以優化區域創新網絡演化的空間布局。
二、文獻回顧
區域創新網絡的概念最早由Freeman 提出。隨著新經濟地理學的發展,區域創新的空間效應成為區域創新網絡研究的熱點。我國區域創新活動存在著顯著的空間關聯,區域創新的空間關聯源于創新活動的空間傳導特性。國內學者蔣天穎、李琳等(2014)對引力模型進行了修正,研究了區域創新的網絡結構。創新網絡結構影響著區域創新效率,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嘗試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對區域創新網絡的空間演變格局和路徑等進行了相關研究。
鄰近性被認為是影響區域創新網絡形成與演化的重要因素,是跨區域創新的重要驅動力。Boschma(2005)把鄰近性分成地理鄰近性、社會鄰近性、認知鄰近性、組織鄰近性、制度鄰近性五種類型。伴隨創新網絡主體的復雜自適應過程,創新結網對不同維度鄰近性具有差異化需求。由于研究目的和視角不同,鄰近性的概念存在交叉,還未形成一個規范的框架。Balland(2012)基于SIENA模型證明了地理鄰近對協作網絡的積極作用。夏麗娟、王海花(2017)認為地理鄰近性促進跨區域產學協同創新。TerWal(2014)通過分析德國生物技術網絡證明地理鄰近性的作用在減弱。Scherngell(2011)、Heringa(2014)證明了地理鄰近性的負面影響。可見,地理鄰近在創新合作中既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需要其他維度的鄰近性共同發揮交互作用推動創新。
多維鄰近性之間的作用是系統的、動態關聯的。黨興華(2013)發現認知鄰近性制約跨區域技術創新合作,Broekel(2015)研究發現荷蘭航空業知識網絡中的認知悖論。Paci(2014)基于知識生產函數分析歐洲276 個區域的創新能力,得出地理鄰近性、技術鄰近性、社會鄰近性、組織鄰近性的交互作用對跨區域創新都存在明顯的互補作用。Hansen(2015)發現在丹麥清潔技術行業的協同創新中,地理鄰近性促進非地理鄰近性(認知鄰近、組織鄰近、社會鄰近)的作用,而非地理鄰近性會替代地理鄰近性發揮作用。Geldes(2015)通過智利農業企業集群合作中主要取決于社會鄰近性,地理鄰近性關系不大。Crescenzi(2016)研究發現英國專利創新網絡主要受社會鄰近性的促進作用,地理鄰近性促進作用不明顯,與認知鄰近性無關。多維鄰近性伴隨創新網絡生命周期不斷演化,由于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情境的差異,鄰近性影響創新合作的結論并不一致,多維鄰近性之間的交互作用能更充分地解釋創新合作。
本研究利用《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相關數據刻畫“創新質量”,并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測量空間關聯,彌補了以往研究中運用專利數據詮釋創新的片面性。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分析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的時空演化規律,并利用QAP回歸探析多維鄰近性對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作用機理。
三、研究設計
1.修正的引力模型
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是由創新要素在不同區域間動態流動產生的。按照“地理第一定律”,創新溢出效應隨著空間距離的增加而衰減,鄰近創新源的主體往往靠“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理優勢擁有更好的創新產出和創新績效。本文借鑒引力模型對區域創新空間關聯進行定量測量,符合經濟動力學中的經濟引力論。但是創新領域內的經典引力模型中測算指標過于單一,專利申請與授權量、論文合作量、新產品產值等數據都不能全面刻畫“創新質量”,且關系型數據不易獲取,兩地之間的空間距離等也不能合理表征區域間的“距離”,所以測算結果難以從宏觀角度表征區域創新系統間的創新關聯關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如下:

修正的過程如下:(1)采用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指標得分較全面地刻畫“創新質量”,是綜合了各地區知識創造(權重0.15)、知識獲取(權重0.15)、企業創新(權重0.25)、創新環境(權重0.25)、創新績效(權重0.20)5個一級指標、20個二級指標、40個三級指標和137 個四級指標加權綜合計算出的綜合效用值(表1),數據可靠且權威,更加全面地表征了“創新質量”;(2)考慮到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不對等性,用區域創新質量占比來修正引力常數,構造有向網絡;(3)參考托達羅人口遷移模型,采用地理距離和經濟距離的綜合距離修正兩地間距離,dij為兩個省會城市間的最短公路距離,gi、gj分別代表i、j 兩省的人均GDP。

表1 中國區域創新能力指標體系
本文選取全國31 個省市區作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2002-2018年,區域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類的數據來源于《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地區人均GDP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兩省會城市間的最短公路距離由百度地圖檢索得出。
2.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SNA)方法是用于網絡和關系精準定量研究的重要方法,用圖論工具和代數模型研究網絡中的關系模式。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具有開放性、動態性、多樣性的特征,其關系結構復雜多變,SNA 強調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用圖和矩陣刻畫社會網絡,能對各種關系進行準確分析,包括網絡密度、中心度以及凝聚子群的時空演化。
(1)網絡密度
網絡密度(Density)表示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連接的緊密程度,是網絡中實際關聯數與最大可能關聯數的比值,見公式(1),其中n為兩節點間的聯結關系數量,N為網絡節點數。

(2)網絡中心度
網絡中心度表示節點居于網絡中心位置的程度,度數中心度、中間中心度是最常用的測量方式。度數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衡量與某節點i直接相連的其他節點的個數n(i),可以表示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的創新收益能力及對其他省市的創新影響力,反映各區域在網絡中的地位和權利。見公式(2)。

中間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BC)指節點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其他節點的掌控度,可以表示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各省市對其他省市的控制力,發揮橋梁作用,見公式(3),其中bjk( )
i為節點i位于節點k和j之間捷徑的概率。

(3)凝聚子群分析
凝聚子群用于分析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的子群構成,子群中節點間往往具有直接的、緊密的、經常的關系,可以表示聯系緊密的空間集聚小團體現象。
四、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時空演化特征
1.網絡密度演化
在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全國31 個省市區為網絡節點,節點之間的創新要素流動為網絡連接。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得出各區域空間關聯的強度矩陣,使用Netdraw 軟件繪制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結構拓撲圖,篇幅有限,本文僅列出了2002年、2010年和2018年網絡形態。不難看出,2002-2018年間,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趨于稠密,網絡間聯系不斷增多,網絡密度不斷增大,中心節點位置發生變化,網絡形態呈現差異性。
整體網絡的密度越大,說明網絡中各節點之間聯結越緊密。根據公式(1)可以計算出網絡整體結構密度演變情況(圖2)。從2002-2018 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的整體密度來看,網絡密度由2002 年的0.2860 提高到2018 年的0.5511,網絡關聯數從2002 年的266 增長到2018 年的519,總體呈現增長態勢。其中2002-2012 年表現為快速增長,2012-2018 年表現為平穩增長,但仍與距離最大潛在關聯數930存在差距,說明區域間創新的關聯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圖1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結構演化

圖2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密度演化
2.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心性演化
中心性可以揭示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演化的內在結構特征,度數中心性體現各區域在網絡中心地位的演變。由表2看出,2002-2018年間各省市的度數中心度(DC)基本上都保持增長趨勢,表現出由快速增長向平穩增長的階段性演變過程,與網絡密度演化的階段性相一致。
為了更直觀地體現中心性等級的躍遷,將度數中心度大小按照等間距分段法劃分為三個等級,由表3發現,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由北京、上海的“雙核心驅動”網絡結構演變為以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湖北、廣東、重慶為中心的“多中心驅動”的網絡結構,說明各省市更加主動地與其他省市開展創新合作。其中,北京、上海多年來穩居一級創新中心,在網絡中處于絕對核心地位,其周邊省份天津、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很快被帶動起來,2010年成為一級創新中心,福建、湖北、重慶在2018 年也成為一級創新中心。二級創新中心在2002-2018年間增加了13個,新增的一級創新中心均由二級創新中心躍遷而來,遵循著一定的遞進規律,“多中心驅動”網絡已經形成。

表2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心性演化
為進一步分析各省市在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的“橋梁”作用,即多大程度上處于兩個區域之間,表2同時給出了2002-2018 年中間中心度(BC)的演變情況。不難發現,2002年,北京、上海在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不僅是創新的發動機,并且同時擔任樞紐站的作用,是其他區域產生創新關聯的必經之路,已經把大部分中東部省市聯結起來,部分西部省市還處于孤立狀態。2010 年,大部分省市扮演著“中間人”角色,部分省市尤為活躍,比如天津、江蘇、浙江、廣東、山東。2018年,中間中心度呈現下降趨勢,分布趨于均勻化,各省市在區域創新空間關聯中均充當著“中間人”的角色,平均次數為1.48次。福建、重慶、湖北躍遷成為一級創新中心,其他省市中間中心度均小于1。可見,度數中心度與中間中心度的演變結果一致,更具掌控力的省市往往也更容易獲取創新資源,占據網絡的中心地位。

表3 2000-2016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心度等級分布
在中心度等級分布的空間形態演化上,網絡創新中心呈現從東部沿海省市向內陸地區輻射的態勢。2002年一級、二級創新中心全部分布在東部地區,2010年山西、安徽等6個中部地區和重慶、四川等6個西部地區躍遷成為二級創新中心,空間形態發生質的改變。2018年湖北、重慶分別作為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創新增長級成為一級創新中心。按照中心演變的規律,甘肅、陜西有潛力成為西部地區新的創新增長極。

圖3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中心度時空演化

圖4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凝聚子群時空演化
3.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的凝聚子群演化
凝聚子群分析可以反映整體網絡中區域間緊密聯系集聚形成的區域小群體現象。采用Ucinet 軟件中的CINCOR(convergent correlations迭代相關收斂法)進行網絡簡化,探索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的空間聚類特征(圖4)和相互作用關系(圖5)。

圖5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凝聚子群相互作用關系
2002-2018 年間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在2 級層面上劃分為4個子群,子群內部大部分省市在呈現近似特征。一方面,各省市在自主創新的同時,更傾向于與空間相鄰的區域產生關聯,呈現“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特征,說明地理鄰近仍然是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重要影響因素;另一方面,創新能力相近的區域之間擁有相近的隱性知識基礎,溝通更為有效,進而產生的創新關聯也更多,呈現“門當戶對”的特征。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內部子群形態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各省市之間的聯結關系更加緊密,創新的空間溢出渠道增多,2002-2010年第二子群和第四子群間的關聯從無到有,第四子群與第一子群關系由單方受惠變成了雙方互利(表4)。

表4 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凝聚子群密度矩陣
各凝聚子群在整體網絡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大致可分成四類。第一子群為領導子群,是創新活動的“發動機”和“領頭羊”,不僅自身創新聯系密切,同時對第二、三、四子群均有溢出效應。第二子群為橋梁子群,江浙等區域既保持與領導子群緊密互動,又能輻射帶動第三、四子群等中西部地區,起到橋梁紐帶作用。第三子群為凈受益子群,主要受到第一、二子群的輻射和互動,自身創新聯系較少。第四子群為孤立子群,西部偏遠地區與其他子群互動較少,相比其他子群處于封閉或孤立狀態。四個子群基本上遵循由東部沿海區域向中西部輻射的等級擴散規律。2018年,湖北、吉林與陜西、內蒙古、新疆等西部地區聯系緊密,應充分發揮湖北、陜西作為一級創新增長級的作用幫攜第四子群快速發展。重慶成為第二子群的唯一西部省市,要充分發揮其橋梁作用,輻射帶動西部地區快速發展。未來第三子群要主動與第四子群開展創新合作,進行創新溢出,第四子群更要努力提升自身資源配置能力,向第二、三子群輸送創新資源,打通溝通合作的渠道促成創新聯動的局面,才有益于區域平衡發展。總體上看,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結構發生較大變動,各省市扮演的角色也隨之不斷調整,逐步呈現出“多中心、多層次”的網絡創新空間格局。
五、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鄰近性機理
在分析了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時空演化外在特征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從內在機理層面解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形成與演化的動因。區域創新網絡演化的動力受鄰近性、網絡復雜性和內生性、主體異質性等多重因素影響。本研究分析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矩陣與地理鄰近矩陣、認知鄰近矩陣、社會鄰近矩陣和其交互項乘積的作用機制與驅動效果,并對系數進行非參數檢驗以判斷其可靠性。
很多常規的統計方法并不適用于“關系數據”和“屬性數據”研究,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是探究不同矩陣之間相關系數的非參數檢驗方法,不需要自變量間互相獨立,也能解決多重共線性問題,比參數方法更穩健。本文采用QAP方法探析影響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鄰近性機制,模型如下:

其中,Dij為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矩陣,Geoproxij為地理鄰近性,Cogproxij為認知鄰近性,Socproxij為社會鄰近性,Geoproxij×Cogproxij表示地理鄰近性與認知鄰近性的交互作用,Geoproxij×Socproxij表示地理鄰近性與社會鄰近性的交互作用。
1.地理鄰近性
地理鄰近性表示行為主體間的空間接近程度,本研究用ArcGIS軟件測算兩省會城市間的球面距離,借鑒王貝貝(2013)的研究方法計算地理鄰近,公式如下:

其中,dij表示省會城市i和j之間的球面距離,maxdij表示省會城市間的最大距離。Geoproxij為地理鄰近矩陣,取值在0-1之間。
2.認知鄰近性
認知鄰近性表征個體在知識基礎、技術結構、文化習俗等多方面的相似程度,常與技術鄰近性混淆并被替代,專利數據中技術分類的相關性沒有全面考慮認知鄰近的測量。本研究參照Jaffe(1986)的測量方法并進行修正,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fin、fjn分別為i 和j 兩個區域在知識創造、知識獲取、企業創新、創新環境、創新績效5個維度的效用值,考察區域創新子系統的內部耦合效果和相似系數,數據來源于《中國區域創新能力評價報告》。
3.社會鄰近性
社會鄰近性表示各省市間的親疏關系。本文參考Schemgell(2009)的研究,利用Jaccard 指數測量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社會鄰近性,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ij表示由i點到j點的邊權,Out(i)表示i的所有出強度,In(i)表示j的所有入強度。
基于以上模型,經過2000次隨機置換后得到的QAP多元回歸結果,表5給出了標準化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水平。為體現各變量的影響情況和驅動效果,本文建立模型1-5逐步考察多維鄰近性及其交互作用對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演化的驅動機制。

表5 QAP回歸結果
由模型1-3可以看出,地理鄰近性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地理鄰近性在我國區域間創新合作過程中促進了區域創新空間關聯,從而顯示其存在的必要性。知識的傳播存在顯著的地理衰減效應,地理鄰近性為行為主體間面對面溝通提供了渠道,降低了交易成本,這與很多研究結論一致,同時反駁了“地理已死”的觀點。認知鄰近性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行為主體在選擇創新合作伙伴時更愿意與認知水平相近的主體產生聯系,認知鄰近性為主體間的有效溝通提供了保障,有助于創新主體科學評估隱性知識的價值,進而促進跨區域創新。社會鄰近性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行為主體更傾向于與社會關系親密的主體建立聯系,基于合作慣例和信任機制來減小創新的不確定性風險。社會鄰近性通過已有的社會嵌入關系和合作經歷增進互信,減少繁瑣流程,降低知識轉移和吸收的難度,強化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路徑依賴趨勢。通過模型3 看出,社會鄰近性的回歸系數(0.4937)最大,其次是認知鄰近性(0.2375),地理鄰近性(0.1291)的作用最小,說明“關系型”社會的中國情境在區域創新聯系中依然適用,并且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影響區域創新空間關聯最重要的因素。
多維鄰近性之間的交互作用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考察了地理鄰近性與認知鄰近性、地理鄰近性與社會鄰近性的交互作用。由模型4 看出,地理鄰近性與認知鄰近性的交互作用顯著,表現為負向調節地理鄰近,正向調節認知鄰近。地理鄰近下產生的共同文化和相似的編碼方式,形成“創新的空氣”,促進創新主體間認知水平的相似程度。認知鄰近性雖然不能改變地理鄰近程度,但能在相對程度上克服合作的地理范圍,避開技術鎖定效應。模型4的擬合優度(0.417)與模型3(0.417)相比并沒有提升,說明地理鄰近與認知鄰近的交互作用顯著,但對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結果解釋力不足。由模型5看出,地理鄰近與社會鄰近的交互項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現為負向調節地理鄰近性和社會鄰近性。社會鄰近可以形成“臨時性地理鄰近”,擴展區域創新網絡的地理邊界,削弱對地理鄰近性的依賴,進而替代地理鄰近性。地理鄰近性的主體間在進行創新合作時會放松對社會鄰近性的要求。這種替代關系與Wei Hong、向希堯的研究結論相一致。模型5的擬合優度(0.546)較模型3(0.417)顯著提升,說明地理鄰近性與社會鄰近性的交互作用明顯,相互削弱彼此對區域創新合作的促進作用,并能有效解釋區域創新的空間關聯。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國2002-2018年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的時空演化特征,并應用QAP回歸解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演化的鄰近性機理,得出以下結論:
我國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密度呈現“穩中有進,聯系不足”的特點,網絡中心具有“強者恒強”的特征,北京、上海常年來穩居網絡核心地位,天津、江蘇、浙江、山東、廣東等地區快速發展形成“多中心驅動”網絡,由“少核主導”向“多核互聯”的空間格局演變,“多中心驅動”網絡已經形成,創新中心遵循著鄰近遞減與等級擴散的規律。區域創新的空間關聯存在“近水樓臺先得月”和“門當戶對”的特征,大致可分為領導子群、橋梁子群、凈受益子群和孤立子群。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凝聚子群結構變動較大,各省市扮演的角色也隨之不斷調整,逐步呈現出“多中心、多層次”的網絡創新格局。鄰近性影響機制上,社會鄰近性、認知鄰近性、地理鄰近性對區域創新空間關聯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其作用依次減小,地理鄰近性仍是促進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的重要因素。地理鄰近性社會鄰近性的交互作用顯著,表現為替代效應。“關系空間”能一定程度上代替“地理空間”促進區域創新網絡形成與演化。
基于以上分析結論,提出以下優化區域創新空間關聯網絡發展的建議:(1)培育中西部地區創新增長極,完善創新空間關聯通道。既要充分發揮領導子群的“領頭羊”作用,又要進一步挖掘橋梁子群的“橋頭堡”作用,還要調動凈受益子群的主動積極性,充分發揮各自的區位優勢,才能形成“多中心驅動、多核互聯”的創新網絡發展空間格局。(2)加快區域間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信息通訊技術,弱化地理距離的阻礙,提高各省市間的可達性。(3)鼓勵區域內創新主體形成自身特色優勢,主動學習開展知識和技術交流,提升自身區域創新能力,增進區域間認知鄰近性,實現協同創新。(4)通過搭建合作交流平臺發展各區域間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濃厚的交流合作氛圍,強化創新合作的路徑依賴,克服地理距離對創新合作形成的障礙,建立跨區域創新合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