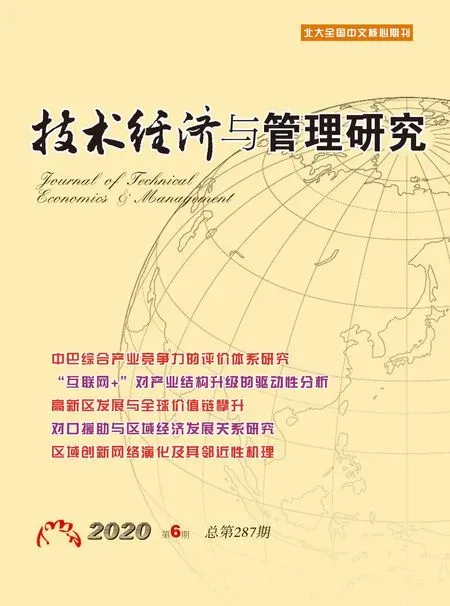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結構研究
賈凈雪,湛 諶
(1.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數學與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430205;2.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430074)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國際分工對象日益細化和碎片化,生產鏈和價值鏈逐漸向全球范圍內延伸。在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簡稱GVC)分工中,不同的國家承擔產品生產中特定的生產環節,而每個生產環節所創造的價值量是不同的,進而導致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不同階段的國家,其獲取產品附加價值的能力也將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厘清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況,將有助于明確該國獲得的分工利益,為其更好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提供參考依據。在全球價值鏈背景下,大量中間產品沿著價值鏈反復跨越國界流動,因此中間品貿易的比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參與GVC分工的狀況。Hummels等(2001)從中間品進口的角度出發,將“出口中包含的進口中間品的價值”定義為“垂直專業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以其在總出口中的比重來衡量一國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同時,他們還從中間品出口的角度出發,將“出口中被進口國加工復出口的中間品價值”定義為VS1,但由于受到數據的限制,并未給出具體的計算公式。Daudin 等(2011,簡稱DRS)在HIY 方法的基礎上,利用“一國出口產品中被進口國加工后(以最終產品的形式)又返回本國的增加值”來衡量垂直專業化。Johnson 和Noguera(2012)將“出口中包含的被國外吸收的國內增加值”定義為“增加值出口(VAX)”,并利用其在總出口中的比重來衡量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Koopman(2010,2014)認為單純地利用VS、VS1等特定指標,無法全面反映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及其地位。他們從國家層面出發,將傳統的總值出口徹底分解為不同的增加值成分和重復計算項,在此基礎上,利用“出口中被他國加工后復出口的國內增加值的比重”和“出口中國外增加值的比重”來反映本國作為供給者和使用者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參與程度,同時也可以反映該國參與GVC分工的地位。隨后,Wang 等(2013)與王直等(2015)進一步將Koopman等的增加值分解方法擴展到行業/雙邊水平。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對外貿易規模迅速擴大,并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1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但是事實上,“兩頭在外”加工貿易的方式是我國對外貿易重要的組成部分,由此導致我國真正獲得的貿易利益很低,傳統貿易統計方法大大高估我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價值創造和分工地位。國內外學者利用不同的指標對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狀況進行研究。目前,學者們大都是在對出口進行增加值分解的基礎上,構建相關的指標,從不同角度考察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分工程度及其地位。樊茂清和黃薇(2014)利用“下游參與度”和“上游參與度”兩個指標來考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發現中國的生產活動正在逐步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周升起等(2014)利用增加值貿易數據庫(TiVA),采用Koopman 等的方法對中國制造業整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況進行考察,并發現在研究期間我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逐漸上升,而在GVC 中的國際分工地位呈現L 型演變特征。劉琳(2015)基于增加值貿易視角,利用WIOD數據庫測度了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及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研究結果表明,1995-2011年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逐年增強,但是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較低,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下游位置。尹偉華(2017)從經濟體作為使用者和供給者參與GVC 分工的角度,通過構建后向垂直專業化(VS)、前向垂直專業化(VS1)等指標,來考察中美服務業在GVC分工的程度和地位。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中間產品在不同國家間流轉,一國對國外中間產品的供求地域分布反映了一國在參與GVC分工過程中形成的價值聯系和經濟依賴特征(潘文卿和李跟強,2018)。劉重力和趙穎(2014)從上游依賴和最終需求依賴兩個角度對東亞區域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依賴關系進行研究。佘群芝和賈凈雪(2015)分別從上游依賴、下游依賴和最終需求依賴三個角度出發,構建相應的指標來考察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依賴關系。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對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很高,從變化趨勢來看,中國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依賴關系均表現出減弱的跡象。程大中(2015)利用WIOD數據庫,分別從中間品關聯、增加值關聯、投入產出關聯三個角度,考察了1995-2009年期間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的關聯程度。研究發現,中國與較高收入的經濟體之間的關聯程度較高。董虹蔚和孔慶峰(2017)發現在2000-2014年期間,中國從上游參與GVC 生產的程度上升,從下游參與GVC 分工的程度下降。從不同國家來看,中國與發達國家(地區)的貿易聯系逐漸下降,而與金磚國家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的貿易聯系呈現上升的趨勢。潘文卿和李跟強(2018)從增加值供給與需求的雙重視角考察了在參與國家價值鏈與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中國各區域之間以及它們與亞太各經濟體的增加值互動關系。
縱觀現有文獻,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構建相應的指標來考察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況,為本文奠定了基礎。但是,現有的研究仍然存在幾點需要改進:(1)從研究方法看,現有文獻大都是在對傳統總出口進行增加值分解的基礎上,利用出口中不同部分增加值在總出口的比重來構建相應指標,進而分析一國及各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況。顯然,對總出口進行增加值分解的方法不同,依此構建指標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同時,WWYZ(2017)指出之前的研究僅體現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國際貿易屬性,不能反映全部的全球價值鏈活動。他們分別從增加值使用者和供給者的角度,提出了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四種途徑,并構建了相應的指標來全面衡量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況。本文將借鑒該方法,全面分析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分工地位及參與簡單和復雜分工的狀況。(2)從研究視角看,目前文獻大都考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程度、分工地位,但是對于參與GVC分工的國別結構鮮有涉及。雖然程大中(2015)根據進口中間品的國外增加值的來源以及出口中間品中國內增加值的去向,分析了中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關聯關系,但是沒有區分中間品在使用上(生產國內消費品和出口品)的差異。本文將根據中間品的使用途徑,更加細致地分析中國參與GVC的路徑及其與他國的依存關系。(3)從數據來源看,目前使用較多的數據庫分別為增加值貿易數據庫(TiVA)、2012年公布的WIOD數據庫,限于研究數據的可得性,之前研究的時間范圍多在2011 年之前,無法反映當前的發展狀況。鑒于此,本文將以WWYZ(2017)界定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活動為基礎,利用最新公布的WIOD數據庫及UIBE GVC Index數據庫,分別從增加值供給者和增加值使用者的角度,對2000-2017 年期間中國參與GVC 的分工程度、分工地位和分工結構進行考察。
二、指標構建
本文利用包含G 個國家(s,r=1…G表示國家),N 個行業(i,j=1…N表示行業)在內的世界投入產出表,根據投入產出理論,可得以下投入-產出恒等式:

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中,上述恒等式還可以繼續分解為:

對式(2)進行變形得:

其中,L=(I-AD)-1表示國內里昂惕夫逆矩陣。令表示直接增加值系數矩陣。對式(3)左右兩端同時左乘V的對角矩陣然后對最終產品矩陣YD,YF和Y進行對角變換,并分別用和表示,則可以證明,以下等式成立:





三、結果分析
1.中國參與GVC分工的整體狀況

表1 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上下游結構分析(單位:%)
本部分利用UIBE GVC Index 數據,根據前文構建的指標,分別從增加值供給者和增加值使用者的視角,考察2000-2017年期間中國參與GVC 分工的程度,同時根據中間品的使用途徑,進一步考察中國參與簡單GVC 分工和復雜GVC 分工的程度,進而全面衡量中國參與GVC分工程度、分工地位和分工結構,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1)中國GVC上游參與度
一國以增加值供給者的角色從上游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可以通過該國中間品出口后作為中間投入參與其他國家生產活動的本國增加值來體現,其在一國總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表明該國在GVC 分工的上游參與度越高。
首先,從中間品出口中國內增加值的絕對額看,2000-2017 年期間中國該部分增加值絕對額呈現逐年快速增長的態勢,由2000年的981.2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0476.2億美元,增長了10 倍多。其中,用于進口國生產國內消費品的國內增加值由2000 年的624.4 億美元增加到2017 年的6363.6 億美元;用于進口國生產出口品的國內增加值由2000年的356.8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4112.6億美元。
其次,根據中間品出口中國內增加值在總增加值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在GVC分工中的上游參與度。從平均值來看,2000-2017年期間中國以增加值供給者的角色參與GVC分工的程度約為10.37%。從變化趨勢看,2000-2017年期間中國在GVC分工中的上游參與度大致分為三個階段:2000-2006 年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由2000 年的8.11%上升至2006年的最高值12.66%;2007-2009年出現下降,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上游參與度迅速下降至2009年的9.37%;2010年以后,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中國在GVC分工中的上游參與度出現輕微的上升。
最后,從參與簡單和復雜GVC 分工結構來看,在GVC上游參與度中,中國為進口國生產國內消費品的中間品投入中包含的國內增加值占比,顯著高于進口國生產出口品中的國內增加值占比,也就是說中國以上游供給者參與簡單GVC 分工的程度顯著高于參與復雜GVC 分工的程度。具體來看,在2000-2017 年期間,中國從上游參與簡單GVC 分工程度由2000 年的5.16%上升至2007 年的7.69%,在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快速下降至5.99%,隨后又上升至2017 年的6.19%。
(2)中國GVC下游參與度
一國中間產品進口中的國外增加值,反映了一國以增加值使用者的角色從下游參與GVC生產程度。該部分增加值在一國總產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表明該國在GVC分工中的下游參與度越高。
首先,從中間品進口中包含的國外增加值絕對額來看,2000-2017年期間中國該部分增加值絕對額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由2000年的1390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058.1億美元,增長近10 倍。其中,用來生產國內消費品的中間品進口中包含的國外增加值,即參與簡單后向GVC分工的國外增加值,由2000年的836.6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7869.9億美元;用來生產出口品的中間品進口中包含的國外增加值,即參與復雜后向GVC分工的國外增加值,由2000年的553.4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5188.2億美元。
其次,根據中間品進口中國外增加值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在GVC 分工中的下游參與度。2000-2017 年期間,中國在GVC 分工的下游參與度平均約為13.4%。從變化趨勢看,自加入WTO 以后,中國在GVC 分工的下游參與度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由2001 年的10.66%上升至2007 年的15.90%,這說明加入WTO 加速了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進程。與GVC 上游參與度的趨勢相同,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 年中國在GVC 下游參與度大幅度下滑至12.03%。2010 年以后,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出現輕微的上升。
最后,從參與簡單和復雜GVC 分工結構來看,在2000-2017 年期間中國從下游參與簡單GVC 分工的程度變化幅度不大,其平均值約為7.48%。但是,對于參與復雜GVC分工的程度,先由2000年的4.57%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8.01%,隨后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參與復雜GVC后向分工的程度迅速下降至2009年的4.99%,隨后出現短暫的上升,但是到2017年重新下降至4.40%。從總體來看,除了2006年和2007年以外,其他年份中國以下游生產者角色參與簡單GVC分工的程度顯著高于其參與復雜GVC 后向分工的程度。但是簡單GVC 分工變化幅度小于復雜GVC 分工,說明參與復雜GVC 分工更容易受到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
(3)中國GVC總參與度及其地位
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上游參與度和下游參與度之和共同構成一國GVC總參與度。從表1中結果可以發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在GVC分工中的上游參與度和下游參與度均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由此導致中國GVC總參與度也呈現顯著的增長態勢,由2000 年的19.34%上升至2007 年的28.47%,這表明中國參與GVC 分工程度逐漸加深。但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GVC 總參與度驟降至2009 年的21.4%。隨后世界經濟復蘇,我國GVC總參與度又出現緩慢上升。從參與簡單和復雜GVC分工結構來看,2000-2017年期間中國參與簡單GVC 分工的程度始終高于參與復雜GVC 分工的程度。
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上游參與度與下游參與度之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由表1中結果可知,2000-2017年期間,中國在GVC分工中的下游參與度始終低于同期的上游參與度,GVC地位指數為負數,這表明中國以下游生產者角色參與GVC分工的程度高于以上游供給者角色參與GVC 分工的程度,中國在GVC 分工中的地位偏低。因此,提高中國作為上游供應者的參與程度,是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國際分工地位的關鍵。
2.中國參與GVC分工的國別結構
為了進一步體現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本文按照增加值的來源及流向,對中國中間品進口中國外增加值的來源結構及中間品出口中國內增加值的流向結構進行全面分析①為了便于分析,本文對部分國家或地區進行合并:將英國、德國、法國等27個(不包括克羅地亞)歐盟國家合并,記為EU;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和土耳其這6個國家合并為一個整體,稱之為新興經濟體,記為BRIIMT;日本(JPN)、韓國(KOR)、中國臺灣(TWN)合并為東亞地區,記為EA。經過合并后,世界投入產出表包含以下8個國家(地區):澳大利亞(AUS)、歐盟(EU)、新興經濟體(BRIIMT)、加拿大(CAN)、中國(CHN)、東亞地區(EA)、美國(USA)以及世界其他國家(ROW)。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依賴關系。同樣的,在下文中,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地區)也選取這8個國家(地區)為對象進行分析。。
(1)作為增加值供給者參與GVC分工的國別結構
中間品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反映了一國作為上游增加值供給者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的上游依賴關系。從與不同的下游生產國之間的依賴關系來看,研究期間,中國出口到歐盟的中間品中的國內增加值在總的中間品出口包含的國內增加值中所占比重最高,呈現緩慢上升隨后下降的趨勢。出口到東亞地區、美國等發達國家(地區)的中間品包含的增加值所占比重位列第二和第三位,在研究期間均呈現出顯著的下降趨勢。與此相反,中國出口到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中間品中包含國內增加值的比重呈現出顯著增長的態勢,由2000年的5.51%上升至2017年的10.92%,增長了近一倍。
總體來看,研究期間,中國出口到美國、歐盟、日韓、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地區)的中間品中的國內增加值所占的比重超過50%以上,該比重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也就是說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中國與歐美、韓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上游依賴關系較為顯著。但是,從變化趨勢來看,中國出口到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中間品中的增加值份額呈現上升的趨勢,即中國與這些國家(地區)的上游依賴關系在逐步增強。

表2 2000-2017年我國中間產品出口中的國內增加值:國別結構(單位:%)
根據中間品出口后的具體用途,對中國出口到不同國家的中間品在進口國的用途再進行詳細分析。研究期間,歐盟作為中國最大的中間品出口目的地,從中國進口的中間品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重平均約為46.78%,并且該比重在研究期間呈現出下降的態勢。對于美國和東亞地區等發達國家(地區),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比重相對較高,平均約為68.67%和63.51%。但是從變化趨勢來看,美國進口的中國中間品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重在研究期間比較穩定,而東亞地區的該比重則由2000年的69.15%下降至2017年的58.05%。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從中國進口中間品后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例在研究期間均位于50%以上,且呈現出上升的態勢,由2000年的52.19%上升至2017年的60.69%。
(2)作為增加值使用者參與GVC分工的國別結構
中間品進口中的國外增加值反映了一國作為下游增加值使用者與其他國家(地區)之間的下游生產關系。從國外增加值的來源國看,研究期間中國中間品進口中來源于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的增加值份額始終居于首位,中間品進口的國外增加值中平均約四分之一來源于東亞地區。來源于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地區)的增加值所占份額分別居于第二和第三位。從變化趨勢來看,在研究期間,中國中間品進口中來源于日韓、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地區)的增加值所占份額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來源于日韓等東亞地區的增加值份額下降了約15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最大。與此相反,來源于俄羅斯、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增加值所占份額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
通過分析發現,中國出口中國外增加值的來源結構存在明顯的國家不平衡性,美國、歐盟、日韓等發達國家(地區)是中國中間品進口中國外增加值的主要來源國(地區),超過一半的國外增加值來源于這些發達國家。也就是說,中國主要參與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上游供應者向中國提供中間投入品。這使得中國很容易受到發達國家支配的被動影響,如果這些國家中斷這些中間投入品,勢必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嚴重的影響。但是,從變化趨勢來看,來源于歐盟、美國、東亞地區等發達國家的增加值份額呈現逐步下降的趨勢,而來源于新興經濟體或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國外增加值份額逐步上升,由此說明中間品進口中國外增加值的來源結構趨于均衡,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過分依賴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從而提高了我國抗擊風險的能力。
根據中間品進口后的具體用途,本部分進一步分析來源于不同國家的國外增加值在中國具體用途結構。東亞地區是中國主要的增加值進口來源國,其中用于生產中國消費品的增加值份額平均約為58.07%,且該比例在中國加入WTO后,由66.32%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51.40%,隨后又上升至59.17%。來源于歐盟、美國等國家(地區)增加值中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例較低,平均比例均低于45%。從變化趨勢看,來源于美國的增加值中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重在研究期間大致呈現上升的趨勢。對于新興經濟體,來源于該地區的增加值中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重較高,平均比重約為58.52%,且在研究期間變動幅度不大,圍繞在50%至60%上下波動。對于來源于澳大利亞及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增加值,用于生產我國消費品的比重較高,平均比重均在60%以上,且均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態勢。

表3 2000-2017年我國中間品進口中國外增加值的來源國別結構(單位:%)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最新公布的WIOD數據庫及UIBE GVC Index數據庫,研究分析中國2000-2017 年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狀況,主要圍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研究。首先,在WWYZ(2017)對全球價值鏈分工活動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從總體上考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程度及地位;然后,按照國外增加值的來源國和國內增加值的出口目的國,進一步考察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別結構,分析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依賴關系。
主要結論如下:(1)從GVC分工總參與度來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在GVC分工中的上游參與度和下游參與度均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中國參與GVC分工程度逐漸加深。但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同時,研究期間中國參與簡單GVC 分工的程度始終高于參與復雜GVC 分工的程度。(2)從GVC 分工地位來看,研究期間中國在GVC 分工中的下游參與度始終低于同期的上游參與度,這表明中國主要以下游生產者角色參與GVC 分工,在GVC 分工中的地位偏低。(3)從作為增加值供給者參與GVC分工的國別結構看,在中國出口到美國、歐盟、日韓等發達國家(地區)的中間品中的國內增加值的份額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且出口到這些國家的中間品被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重較高,但是在研究期間該比重呈現下降趨勢。與此相反,中國出口到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和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中間品中的國內增加值的份額在逐步上升,且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例也呈現出上升的態勢。(4)從作為增加值使用者參與GVC 分工的國別結構看,研究期間來源于日韓、歐盟、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地區)的增加值份額超過50%,但來源于這些發達國家(地區)的增加值份額均呈現不同幅度的下降趨勢。與此相反,來源于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或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國外增加值份額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且來源于該地區的增加值中用于生產國內消費品的比重較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的嵌入全球價值鏈的出口導向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仍然較低,不管是從增加值供給者還是從增加值使用者的角度,中國與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地區)的依存關系均顯著高于中國與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也就是說,中國主要參與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處于全球價值鏈高端的發達國家獲得巨大的分工利益,而對于處于低端和被動位置的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獲取的分工利益較低,嚴重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整體經濟的發展。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以避免長期在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中進行國際代工和出口導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劉志彪,2017)。同時,隨著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程度加深,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依賴關系也日益密切,由此導致我國經濟更容易受到來自其他國家經濟波動的影響(梅冬州和崔小勇,2017)。因此,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我國應妥善處理與各個國家之間的依存關系,避免過度依賴一個或少數幾個國家,從而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在當今發達國家逆全球化浪潮的態勢下,我國應借助“一帶一路”戰略,全面深化與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伙伴關系,重塑全球分工體系,構建互利共贏的區域乃至全球價值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