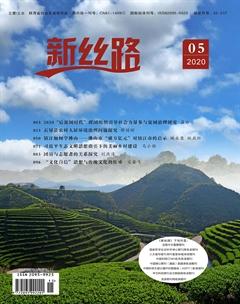淺談革命歷史題材戲曲創(chuàng)作
魯迅先生說(shuō),要改造國(guó)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搞現(xiàn)代戲難,搞革命歷史題材的現(xiàn)代戲更難,而搞出一部?jī)?yōu)秀的革命歷史題材之現(xiàn)代戲則是難上加難。平心而論,我是同意這一說(shuō)法的。
現(xiàn)代戲、革命歷史題材的現(xiàn)代戲由于距離今天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比較近,而革命歷史題材往往還有一個(gè)忠實(shí)于歷史真人真事的問題,自然也就平添了創(chuàng)作上的難度。對(duì)于革命歷史題材戲曲現(xiàn)代戲的創(chuàng)作而言,人物形象塑造的精準(zhǔn)把握,講述故事的切入點(diǎn),劇作結(jié)構(gòu)和情節(jié)設(shè)置,無(wú)不對(duì)創(chuàng)作者提出了更高的、多方面的要求。這就在很大程度上令一些老藝術(shù)家望而卻步,不愿問津。然而,革命歷史題材現(xiàn)代戲的創(chuàng)作是時(shí)代的需要,是人民的呼喚,我們應(yīng)該有更多的、優(yōu)秀的革命歷史題材現(xiàn)代戲馳聘舞臺(tái),發(fā)聲謳歌,詠唱禮贊。
由已故靖邊縣文工團(tuán)著名表演藝術(shù)家梁普先生原創(chuàng),經(jīng)靖邊本土藝術(shù)家改編的秦腔現(xiàn)代劇《蒙漢游擊隊(duì)》,以一種文化自覺、一份文化擔(dān)當(dāng),躋身革命現(xiàn)代題材現(xiàn)代創(chuàng)作隊(duì)列,殫精竭慮、銳意進(jìn)取,成功地創(chuàng)作出了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發(fā)生在陜北“三邊”境內(nèi)與內(nèi)蒙交界地區(qū)的真實(shí)歷史故事。
文藝的一切創(chuàng)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lái)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人情練達(dá)即文章。”藝術(shù)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jiān)實(shí)的大地。文藝創(chuàng)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guān)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蒙漢游擊隊(duì)》是一部藝術(shù)化了的革命史詩(shī),也是一出革命化了的現(xiàn)代戲曲。為了建立蒙漢游擊隊(duì),中共地下黨員鄭子明準(zhǔn)備北上蒙地札薩克擴(kuò)大武裝,實(shí)現(xiàn)蒙漢結(jié)盟。蒙漢兩地土匪頭領(lǐng)巴特魯和孟鎮(zhèn)北為了扼殺紅色種子,暗使奸計(jì),挑撥離間,致蒙漢兩支游擊隊(duì)結(jié)冤生仇,聯(lián)盟之舉陷入困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鄭子明攜獨(dú)生女闖入土匪窩子烏龍寨,在承受了一系列的生死離合、愛恨情仇之后,終于消滅了土匪勢(shì)力,實(shí)現(xiàn)了蒙漢結(jié)盟,建立了蒙漢游擊隊(duì),成為東渡黃河的一支抗日力量。
戲劇打動(dòng)觀眾的唯一途徑是“傳情”。該劇沒有走戰(zhàn)爭(zhēng)題材的“老路”,另辟蹊徑,用人情稀釋戰(zhàn)火硝煙,用人性化解刀槍對(duì)峙,用真情大愛化解了民族糾紛,詮釋了民族團(tuán)結(jié)的真諦。古老的秦腔與悠揚(yáng)的陜北民歌和蒙古長(zhǎng)調(diào)的音樂元素嫁接,開始了“北路秦腔”的第一步探索。
此劇的成功之處在于:
一是劇本成熟,主題立意明確。劇情推進(jìn)有序,人物刻畫準(zhǔn)確。
二是導(dǎo)演精心的二度創(chuàng)作。從舞臺(tái)的呈現(xiàn)看,場(chǎng)面調(diào)度既注重畫面展現(xiàn),又頗有章法;有精雕細(xì)刻,又有輕筆帶過;有濃墨渲染,又有清淡呈現(xiàn);或悲傷、或奮起、或抗?fàn)師o(wú)不飽含著藝術(shù)張力。彰顯出導(dǎo)演揮灑自如,獨(dú)具匠心的大手筆之功力。如地下黨員白志誠(chéng)壯烈犧牲及鄭之明父母化影再現(xiàn),這種慘烈悲壯的場(chǎng)景處理無(wú)不使人動(dòng)情、震憾、黯然落淚。
三是音樂創(chuàng)作設(shè)計(jì)也很成功。全劇優(yōu)美動(dòng)聽、膾炙人口,感人肺腑的音樂聲腔,無(wú)不傾倒眾多觀眾。音樂設(shè)計(jì)地方特色突出,秦聲、秦韻十足。音樂板塊中一個(gè)顯著特點(diǎn)就是多處融入了蒙族音樂元素和陜北民歌。劇目一開場(chǎng)那么深遠(yuǎn)的蒙族音樂及各場(chǎng)幕后多段陜北民歌的獨(dú)唱、伴唱,不但顯現(xiàn)了陜北民風(fēng)、民俗和蒙古族風(fēng)貌,也增強(qiáng)了觀眾對(duì)戲中人物的親切感,強(qiáng)化了戲劇故事的真實(shí)性和地域性,使觀眾情緒鎖定在當(dāng)時(shí)那種悲壯的氣氛之中。
地方性戲曲,越是明鮮地烙印上地方色彩,就越顯得獨(dú)成一體,風(fēng)格獨(dú)具。該劇的音樂創(chuàng)作設(shè)計(jì),自覺地、有意地培植一種新型戲曲模式——北路秦腔。這種嘗試有價(jià)值,有意義。
四是舞美制作也頗具地方特色。體現(xiàn)了舞臺(tái)美術(shù)藝術(shù)的自然回歸,很接地氣。既有大寫意設(shè)計(jì)、又有簡(jiǎn)潔的實(shí)景。這些虛實(shí)景與劇情發(fā)展、以及劇中人的表演融合,天衣無(wú)縫,讓人身臨其境。再有現(xiàn)代聲、光、電的應(yīng)用,也格外妥貼,不突兀,不生硬,做到了水乳交融,互為襯托,互為照應(yīng)。
一部戲,情節(jié)跌宕需要借助情的揮灑,人物刻畫需要捕捉情的焦點(diǎn),結(jié)構(gòu)橋段需要通過情的張揚(yáng)。《蒙漢游擊隊(duì)》恰恰扣緊這個(gè)藝術(shù)環(huán)鏈,以情動(dòng)人,成為全劇抓扣人心的中樞,以情動(dòng)人匯聚成情感色彩渾厚凝重的戲劇沖突,進(jìn)而烘托戲的主題,傳遞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習(xí)近平總書記說(shuō),一部好的作品,應(yīng)該是經(jīng)得起人民評(píng)價(jià)、專家評(píng)價(jià)、市場(chǎng)檢驗(yàn)的作品,應(yīng)該是把社會(huì)效益放在首位。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shù)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chǎng)上受到歡迎。要堅(jiān)守文藝的審美理想、保持文藝的獨(dú)立價(jià)值,合理設(shè)置反映市場(chǎng)接受程度的發(fā)行量、收視率、點(diǎn)擊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標(biāo),既不能忽視和否定這些指標(biāo),又不能把這些指標(biāo)絕對(duì)化,被市場(chǎng)牽著鼻子走。
《蒙漢游擊隊(duì)》的成功,標(biāo)志著秦腔現(xiàn)代戲在戲曲藝術(shù)的大道上又前進(jìn)了一大步,人間需要好戲。我們希望藝術(shù)家們能夠不忘初心,再接再厲,不斷地創(chuàng)作出更多更好的戲劇作品來(lái)。
作者簡(jiǎn)介:
戚改轉(zhuǎn)(1987--)女,陜西省靖邊縣人,大學(xué)本科學(xué)歷。2009年到靖邊縣文工團(tuán)工作至今,從事舞蹈表演。在第六屆陜西省藝術(shù)節(jié)上獲優(yōu)秀表演獎(ji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