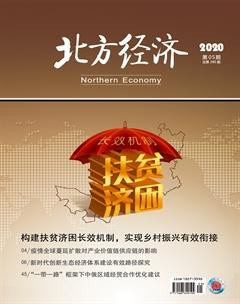疫情全球蔓延擴散對產業價值鏈供應鏈的影響
張燕生
超級全球化及其未來走向
近現代歷史上全球化有過三次較大的波動和曲折。
第一次是1870-1913年,這次全球化是由英國主導推動,最終英國走向貿易保護主義。核心問題是新興大國美國和德國的崛起與守成大國英國和法國的衰敗,引發國際格局和秩序之爭。這次全球化波動和曲折的結果是導致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經濟大蕭條,導致30年代貿易戰全球貿易萎縮2/3。
第二次是上世紀70年代,越戰、冷戰、政府干預經濟等,導致全球化波動和曲折,結果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兩次石油危機,全球經濟滯脹,一直到冷戰結束。
第三次,90年代以來的現代全球化,進而被人們稱之為超級全球化時期,其深度廣度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結果是東升西降、南升北降、中升美降。即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和西方經濟治理主動權的下降。因此,當前真正反全球化的國家正是全球化的領頭羊,例如美國。無論是逆全球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美國要為超級全球化重新建章立制,并從規則、科技、經濟上按住中國復興。因此,這次逆全球化表現在英國脫歐和美國優先,要推動公平貿易和對等開放,背后是西方治理衰敗和非西方尤其是中國的崛起。
疫情對超級全球化的沖擊
科學抗疫進入現階段。這次超級全球化遇到了逆全球化大挑戰,疫情全球蔓延擴散形成了對超級全球化的病毒沖擊。在國內,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現在中國抗疫核心問題已經轉為防控輸入型病例,需要采用大數據、透明度、專業化、法治化和輸出與輸入地協調機制來掌控階段。無論各級各地政府、醫療機構,還是企業、民眾,都不需要一人生病、億人吃藥的大撒網抗疫方式。
恢復國內供應鏈。這次疫情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以及對全球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例如,武漢的重點產業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汽車、新一代電子信息技術以及生物醫藥。在2月份的時候,疫情對武漢以及對整個中國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的影響,基本是停擺。但疫情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我認為是局部的和短期的。3月份開始,各級各地政府的工作重點應轉向加速復工和經濟社會生活正常化,把抗疫工作交給大數據公司、專業機構和輸入地政府主管部門。
全球抗疫開始。從3月份開始,全球三大生產網絡,也就是日本和韓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北美,都面臨巨大疫情考驗和挑戰。疫情蔓延到全球,就不再是短期和局部的,而是全局性和長期性的影響。它既影響日本、韓國、中國東亞生產網絡核心塊,也影響歐洲經濟的核心塊—德國、法國、意大利,還影響北美。這次疫情的特點是隔離和自愈,隔離對全球三大生產網絡產生的經濟、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
疫情加劇去全球化、去國際工序分工、去人際交流的沖擊,可能會促進逆全球化進程。過去逆全球化的表現形式是貿易戰、科技脫鉤、技術封鎖。因此每個國家都會考慮自己產業鏈供應鏈備份的問題,一旦發生了最壞的情況,可以有一個應對準備。但從韓國的三種材料被日本斷供產生的負面影響看,全球的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在逆全球化和貿易戰的情況下發生了逆轉。全球的新科技革命,無論是機器人、人工智能,還是云計算、大數據和工業物聯網,它們產生的趨勢是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本地化、區域化和分散化。從這個角度來講,疫情增加了對全球化和對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重組的負面外部沖擊。
對于中國來說,要高度重視疫情對全球三大生產網絡的重創,對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以及對WTO改革可能出現的沖擊。也就是說,疫情加速了最壞場景發生的可能性、復雜性和長期性,這不僅對中美經貿關系,而且還對中國和世界的經貿關系。
中國希望繼續推動超級經濟全球化前行
中國作為全球開放的受益者,希望推動新型全球化向前發展。無論是應對逆全球化、貿易保護還是技術脫鉤,中國采取的基本對策仍是擴大對外開放,包括海南自貿區港、上海新片區的建設,上海進博會、外商投資法及配套行政法規,中國還是希望能夠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成為新型全球化的推動者。
全球抗疫需要同舟共濟,需要建立中央、地方、企業和全社會多層次推動新型全球化。第一,加強東亞生產網絡,加深中國和日本、韓國之間的全方位、高層次、多元化合作,恐怕是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的考慮,不能像過去一樣四分五裂。無論是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還是加快RCEP、CPTPP,關鍵是構建各層次戰略互信。第二,中國和歐洲生產網絡之間的合作也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合作關系。包括中歐BIT、FTA、一帶一路與歐亞互通戰略對接。第三,中國要加強和美國方方面面的合作。僅僅有5%的極右分子支持脫鉤,而95%的企業仍希望能夠跟中國建立一個更緊密的經貿聯系,機遇在中國。
中國應該敞開胸懷,與世界共同抗疫,從口罩、防護服和設備,到醫療機構互助。既然是一個長期性和全局性的負面影響,就一定要加強口罩、醫療設備等生產的全球供應鏈打造,加強治療方案的合作。這方面也是中國展現自己負責任大國風范所應當做的。
從美國貿易戰可以發現,5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產品加征25%關稅,打擊的60%是外資企業;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征25%關稅,打擊的50%是外資企業。即貿易戰很大程度是想把過去40年在中國建立起來的美國企業、歐洲企業、日本企業的供應鏈打出中國。美國非常清楚,剩余3000億美元中國自己企業生產的輸美產品是能夠給美國消費者帶來最大消費剩余和經濟福利的產品,美國將一半產品加征關稅從15%降到7.5%,另一半為零關稅。中美貿易戰實質上是產業的供應鏈和價值鏈之戰。希望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從非理性對抗轉向理性合作,是大國戰略最終博弈的結果。
從這個角度來講,隨著疫情的下一步發展,中國要從全盤戰略上做全局上的考慮,做好95%的美國企業、地方政府和民眾的工作,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同抗疫不要貿易戰,要掛鉤不要脫鉤。
本文系作者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舉辦的以“疫情沖擊下的經濟全球化”為主題的專家網絡座談會上的發言。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