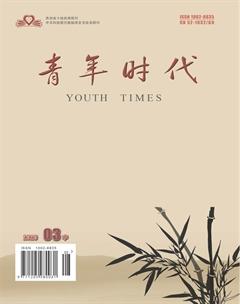淺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研究轉向
楊瀾
摘 要:隨著《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的下發,大眾視野再度聚焦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的傳承與發展。本文重點關注了劇烈的社會變遷沖擊之下,非遺如何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非遺的相關研究又是如何實現由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由傳統媒體到社交傳播與微傳播風行的轉向。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傳播;研究轉向
一、引言
文化遺產不僅僅是傳承遺留下來的物質形態集合,還包括人們繼承的傳統習俗、生活方式,如表演藝術、社會實踐、節日儀式、生產工藝等。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全球化浪潮下保存文化多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他們是由特定社群創造、傳承,并隨著歷史和社會演變過程中不斷再創造的文化遺產。近年來,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非遺的內涵、非遺傳承人、非遺與文化產業、社會變遷等領域。本文重點關注的是非遺的傳播與相關研究如何實現由純粹的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由傳統媒體傳播為主到社交傳播與微傳播風行的轉向。
二、從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
從傳播學視角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過程,其傳播空間和傳播方式等也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蛻變。不少學者落腳于對非遺的傳播路徑的縱向梳理,探討了人際傳播模式不能適應現代非遺傳播的要求與趨勢等問題,肯定了非遺走向大眾傳播的必要性。孫信茹等從傳播學視角視角出發,通過對大理石龍白族非遺文化實踐活動的體察總結出了由“即興表演為主的族群內的技藝傳習”向“展演式的傳播實踐”“媒介式傳播實踐”轉變的非遺傳播路徑。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曾經相對完整的“家庭和村際傳播場域”不再能滿足非遺傳播跨越時間、空間限制的需要。非遺在當代的保護與傳承由人際傳播走向大眾傳播,實際上是社會文化建構變遷的表征。張傳壽也提出,非遺傳承人在政府自上而下的保護力量下仍面臨后繼無人、瀕臨消亡的生存現狀。非遺人際傳播陷入了保護盲區,大眾媒介傳播則有希望為“非遺保護的可操作性提供重要依據”。可以說,非遺自身需要代代相承的屬性,就決定了其特別需要大眾媒介的廣泛關注。
同時,大眾媒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的傳播優勢也是一個研究熱點。“報紙、圖書、電視、網絡等媒介形式都給予了非遺較多的表達機會和展演空間”。大眾媒介一大特征就是能夠深入日常生活。借助大眾媒介的力量,各種非遺文化資源才能進行跨越時空的流變與共享,非遺才能完成文化與傳播的互動,才能實現更為鮮活的傳承和延續。劉詩迪認為,昆曲的現代演繹正是為“充分利用大眾傳播資源弘揚國粹、激發大眾對傳統文化的熱愛”提供了一個思路。以昆曲為代表的很多非遺文化實際上是一種小眾的、地緣性很強的精英文化,而大眾媒介正是其走向大眾的依托。大眾傳播媒介“在表面上磨平了一切地域和民族差異……以直觀的電子畫面和聲音為載體”,推動非遺成為文化認同度更高、走入大眾消費市場的文化形態。
三、從傳統媒體到社交媒體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廣播、電視等傳統主流媒體不再一枝獨秀,新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用戶量攀升,眼球與流量開始成為媒體爭奪的核心。相較于傳統媒體,學者們也愈發重視起社交媒體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研究。
不可置否,傳統媒體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人際傳播走向大眾傳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但在“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5G等新興技術交織呈現的畫面中,傳統媒介的局限性一目了然。胡德強、李龍指出,在多元化信息傳播環境下,“傳統大眾媒介凸顯其‘一對多的窄化傳播、靜態的僵化傳播等特點”,開始出現了“傳統大眾媒介小眾化的趨勢”。傳統媒體視野下的非遺傳播“在與娛樂性較強的影視劇、通俗小說、網絡游戲等大眾文化的交鋒中舉步維艱”。傳統媒體靜態化、定向化等傳播特征與當今受眾求新求快的心理似乎背道而馳,難以為繼。
因此,不少研究者開始將目光投向社交媒體與非遺傳播的辯證關系。一方面,社交媒體的興起實際上擠壓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和傳播空間。“新媒體的發展使人們的娛樂、消費乃至價值觀和審美水平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得非遺顯得越發格格不入。此外,“世界各地的文化、風土人情及風俗習慣更加容易互相滲透和影響”,非遺等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現代化傳播如履薄冰。而另一方面,新媒體特別是社交媒體環境下的非遺傳播也就順勢成為了一個炙手可熱的研究話題。一是大數據大流量、多向動態、超文本性等屬性使得社交媒體在非遺傳播上有著無可比擬的優勢。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工作,群眾的廣泛參與是關鍵,這也正是社交媒體多元化形式介入的意義所在。二是全媒體傳播格局的建設要求大大推動者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等新媒體的融合發展,有利于非遺傳播的全方面整合與創新驅動。“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相互滲透、資源互補”,使得社交媒體時代非遺的傳播效率、傳播效果和信息覆蓋面蒸蒸日上。新舊媒體融合形成了非遺傳播的合力,非遺傳播方式在適應社交傳播移動化、視頻化等特征的基礎推陳出新,被賦予了嶄新的時代內涵。
四、“微”時代的非遺短視頻傳播
在愈來愈多的學者將非遺傳播的研究視角從傳統媒體轉向社交媒體之余,除了微博、微信、客戶端和社區網站等,社交媒體上迅猛增長的短視頻應用和短視頻平臺也吸引了大量眼球。社交媒體短視頻對于傳統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影響可見一斑,“微”時代的非遺短視頻傳播激發了學者們極大的研究興趣。
首先,非遺短視頻的社交傳播影響力不容小覷。短視頻體量輕型再加上視頻拍攝和剪輯技術的發展等,使得這種“訴諸視聽聲畫于一體的傳播方式”招攬了一大批受眾,特別是拉近了非遺文化與當代青少年的距離。創作門檻低、即時社交、精準推送等特征更是不斷增強非遺短視頻傳播的受眾廣度與黏度。此外,官方力量的介入,如“共青團中央入駐抖音弘揚國粹”,更是標志著非遺短視頻的新型傳播方式開始獲得主流認可。可以說,借助了權威資源與力量的非遺短視頻傳播之路不可限量。
然而,資本與市場為非遺短視頻傳播注入動力的同時,曲高和寡、泥沙俱下等行業現狀亟需迫切關照。抄襲現象與同質化問題、良莠不齊的視頻創作、正確價值導向的缺席等,都是短視頻市場存在的嚴峻挑戰。而非遺短視頻的傳播內容是否深入、對受眾能否產生持久的吸引力等問題也都有待商榷。因此,全民信息化時代,信息更迭迅速、短視頻創作成本低下,在推動非遺傳播走向大眾視野的同時也必須謹慎應對頻繁涌現的各種問題。
五、結語
不難看出,社會變遷、媒介生態不斷改變的沖擊之下,非遺的傳播實踐也在不斷適應著新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現實。相應地,非遺傳播的相關研究實現了由人際傳播到大眾傳播、由傳統媒體到社交傳播與微傳播風行的轉向。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標志,是經過長期歷史積淀的精神文明內容,非遺傳播的現代化議題亟需更深刻的思考。
參考文獻:
[1] Lenzerini 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Living Culture of Peoples[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22):101-120.
[2]葛艷奇.“非遺”文化在新媒體時代的呈現與傳播[J].傳媒,2019(8):78-80.
[3]胡德強,李龍.新時代非遺傳承下創新媒介的建構與研究[C].第十六屆沈陽科學學術年會論文集(經管社科),2019.
[4]李微,余建榮.試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媒體傳播策略[J].新聞知識2014(2):50-52.
[5]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什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https://ich.unesco.org/en/what-is-intangible-heritage-00003.
[6]劉詩迪.從昆曲的成功傳播看中國精神文化遺產的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中的媒介力量[J].消費導刊,2008(19):226.
[7]尚春燕.新媒體環境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策略[J].青年記者,2015(26):110-111.
[8]孫信茹,趙亞凈.非遺傳承人的傳播實踐和文化建構——以大理石龍白族村為研究個案[J].當代傳播,2017(3):23-26,31.
[9]王利芹,苗巧針.“微時代”移動社交媒體微視頻傳播問題及對策研究——以快手和抖音為例[J].新聞愛好者2018(8):81-83.
[10]王雪倩.傳統文化在移動短視頻應用中的傳播分析[J].傳媒論壇,2018(18):169,171.
[11]張傳壽.“非遺”視角下的傳統手工藝人保護[J].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集刊,2013(3):44-52.
[12]鐘蕾,周鵬.新媒體多元化形式下的非遺數字化保護探析[J].包裝工程2015(10):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