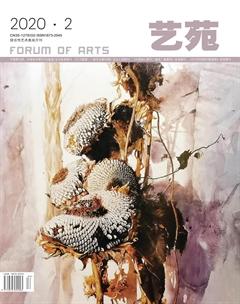出走還是屈服,她們當何去何從?

【摘要】 以《同仇》《一江春水向東流》兩部電影中的女性人物為主要研究對象,根據這些女性人物的身份背景及人物形象將其進行類型劃分;在分析彼此差異性的同時,進一步闡釋影片中女性人物形象意蘊的深化,從而探尋出不同歷史時期女性人物的行為選擇及其歷史命運。
【關鍵詞】 女性人物;形象意蘊;個性解放;救亡;出路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程步高在1934年的《新年感想》中寫道:“我希望以后我所做的片子,本身要有一個健全的意識。同時應用適合這個意識的技巧,來完成它,使它可以吸引大量的觀眾。最近我完工的《同仇》,就是這試驗的初步。”[1]《同仇》是1934年由夏衍編劇、程步高導演的一部電影。電影講述了車站管柵人殷桂生救了從馬上摔下來的年輕軍官李志超。在桂生女兒小芬的精心照料下,李志超逐漸痊愈。在這過程中,兩人漸生情愫。小芬不顧父親的反對與李志超私奔,誰知道李志超竟拋棄已經懷孕的小芬,帶著交際花張曼琳上任。小芬打電報給李志超,卻被張曼琳以李志超的名義與小芬斷絕關系。小芬帶著孩子回到家鄉的時候發現她的父親已經不會說話。父親死后,小芬在痛哭之中聽見外面的嘈雜聲,她看到了群眾正在歡呼送別即將奔赴戰場的李志超,她扔下了手中的銹刀,終于原諒了李志超。
《一江春水向東流》作為20世紀的經典影片,在電影界有著不可忽略的地位。陸茂清在《影人蔡楚生屢創輝煌》中是這樣概括《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蔡楚生著力從深具感染力的故事性、迭宕曲折的情節下功夫,以一個家庭作為社會的窗口,橫跨抗戰前后10年間的變幻升沉悲歡離合,直至家破人亡的命運,展現了時代和歷史的悲劇。”[2]29-33
一、女性人物的類型轉變
從1934年的《同仇》到1947年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不變的是諸多勞苦大眾的命運。女性人物作為影片的主要構成部分,她們身上所展現出的時代特質不容忽視,她們身上也存在著異同點。根據女性人物的身份背景及形象主要將兩部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兩部影片中的女主角,即《同仇》中的小芬和《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素芬;第二類是影片中的交際花,即《同仇》中與李志超共同赴任的張曼琳和《一江春水向東流》中在重慶與張忠良結婚的王麗珍;第三類比較特別,看似身份正當實則人物形象最為復雜,人物展現最不模式化臉譜化,即《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王麗珍的表姐何文艷。
之所以說小芬和素芬是同一類人,是因為她們身上都打著很深的中國傳統社會女性的印記。小芬精心照顧受傷的李志超,面對李志超的告白無比羞澀,素芬在面對張忠良的求婚時也是這樣的反應。尤其是素芬在張忠良走了之后面對種種困難仍毫無怨言地照顧婆婆和孩子,足以證明她便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勤勞善良、任勞任怨、忠貞不渝。但小芬和素芬兩人仍舊有著極大的區別。除了小芬并沒有同李志超結婚,素芬卻是張忠良明媒正娶的妻子這個差異以外,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區別便是小芬同李志超私奔,不顧父母之命,這是小芬對個人解放的追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封建禮教的一種反叛。正是由于兩人的這些差異,才導致了小芬面對李志超的拋棄第一反應是持刀報復,而素芬選擇了自戕。此外,小芬自身也經歷了很大的變化:“這個時候,小芬不是從前的樣子了,細長的眉毛,蜷曲的頭發,居然也會裊裊地跟著王鎮安和李志超走進繁華沉迷的跳舞廳。”[3]甚至于小芬的父親桂生看到自己的女兒竟然“因她變得太過分的美麗了,又有些不敢上前”[3]。這樣的變化是素芬不曾經歷過的,在《一江春水向東流》中有類似經歷的只有男主角張忠良。
在第二類人物中張曼琳是交際明星,王麗珍亦是。區別在于張曼琳自開始便知道小芬,并且在看到小芬給李志超的電報之后,假借李志超的名義與小芬斷絕關系。而王麗珍與張忠良結婚是因為她一直以為張忠良的家人都正如張忠良所說不知蹤跡,這也是她見到素芬后反應如此之強烈的原因。雖然王麗珍在影片末尾已完全是潑婦形象,但較之于刻意插足的張曼琳她并沒有什么讓人指摘的地方,她亦是受害者。兩人結局也有很大的差異:李志超終于理智戰勝了情感,對張曼琳說:“曼琳!你可以使我做一個背叛妻子的丈夫,但你不能使我做一個背叛大眾的民賊!”[3]但《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王麗珍是得勝者,單從張忠良聽到接連不斷的汽笛聲的焦急反應便可以得知。
之所以將何文艷作為第三類人物單列出來,是因為她的復雜性。首先,她有正當名義上的丈夫,但她卻在丈夫被抓之后為將財產改在自己名下與張忠良發生了不正當的關系。“她前夫在抗戰時與汪偽政權相勾結,發不義之財,抗戰勝利后鋃鐺入獄,她漠不關心,卻很快與張忠良勾搭成奸。”[4]75-78此處忽略的是她有此行為的動機點在于當她為丈夫奔走時發現有其他女人來探監,由此得知丈夫與他人關系不明。其次是素芬在宴會上說出自己是張忠良的妻子后她的種種反應。面對丈夫的出軌,她不像小芬、素芬一樣傷心欲絕,也不像王麗珍一樣大吵大鬧,而是在監獄里對丈夫說出:“我為你東奔西走,想盡辦法,吃盡苦頭,你現在還瞞著我,跟這種不要臉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還有良心沒有……你這個死烏龜,你這個無恥的王八蛋,也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這個沒有良心的狗東西,一輩子受你的欺騙……你還要叫我去請律師?那你為什么不叫那種不要臉的女人去給你請律師?你呀就等著槍斃,要不然就在這里住上一輩子。”緊接著她當機立斷,通過張忠良將丈夫所有存款的戶頭名字通通更改,這樣的果斷決絕令人訝異。當王麗珍從重慶回到上海時,她的反應也十分引人注目。她一方面與王麗珍表面上交好,另一方面又要在王麗珍面前隱藏她與張忠良的私情。在宴會上她察言觀色,意識到王麗珍沒有被感謝而不爽時,她舉杯感謝王麗珍張忠良夫婦,使得王麗珍由陰轉晴。當她看到王麗珍因為素芬的出現而崩潰時,她為此十分得意,當她看到素芬傷心欲絕時也開心不已。她仿佛一個坐收漁翁之利的勝利者,但后來她與崔經理的眉眼交流,也顯示出她不得不放下個人尊嚴求生存的卑微處境。相較于第一二類較為單一的人物形象,何文艷這個女性人物較為復雜,與同時代普遍的女性有所差別。
由此可見,從《同仇》到《一江春水向東流》,女性人物的類型朝多樣化的方向發展。賢妻良母式的中國傳統女性形象、追求個人解放的女性形象,在三四十年代影片中都出現過,但何文艷的出現更是對那個時代臉譜化的女性人物形象的一個沖擊。“她不會為任何人而犧牲,什么時候都只會關心自己,堪稱中國的‘蛇蝎美人。”[4]75-78置于當時的歷史語境,何文艷的形象的確不是一個正面人物形象,但她卻不足以被稱為“蛇蝎美人”。她背叛丈夫的前提是丈夫早已背叛她,她的部分做法值得人同情,且其所帶來的思考和啟發具有不可忽視的時代意義。
二、女性人物形象意蘊之深化
小芬和素芬的命運結局有所不同。小芬因李志超的演講和周圍群眾的劇烈反應變得搖擺不定,緊接著手里的銹刀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在劇本末尾:“士兵們從窗口伸出手來不斷地揮著,志超也揮著手,群眾們更是揮手揚巾相送,小芬恨恨著也舉起手來,滿臉的淚痕,但在大眾的歡呼聲,也引得她微笑地頻頻揮動她的手。”[3]“恨恨”與“引得”說明很大程度上小芬是被周圍環境迫使的,在她心中并沒有真正地原諒李志超,只是在這國家民族危難之際不得不做出的妥協與退讓。小芬為了李志超而拋棄父親,最終自己卻也慘遭拋棄,只剩下她于動蕩中撫養孩子長大。素芬同小芬一樣經歷了甜美的戀愛。她因為張忠良的一句“以后每當月圓的晚上,在這個時候,我一定在想念你們”,日后遇到再難過的坎,都真正做到了“我一定用我的全心全力,來擔起這個責任,一直等你勝利回來”。然而素芬面對與小芬相似的境地時卻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選擇。
素芬自殺的原因是復雜的,小芬與素芬不同命運結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兩人的經歷差異:小芬是在李志超帶著張曼琳赴任之時便已經知曉兩人之間的關系,此時小芬與李志超相識也不過數月,沒有十足深厚的感情基礎。素芬對張忠良自然是深愛的,因此當她在宴會上發現那個有妻子且與其他女人勾搭在一起的竟然就是自己的丈夫時她難以接受,甚至一度說不出話來。除此以外,素芬的生存狀況遠比小芬惡劣得多。小芬在等待李志超時尚且有仆婦的照顧,由此可見她的生活仍十分富足。素芬數次面臨的是生死考驗,她在張忠良離開后經歷了公公被吊死,她一個人照顧一家老小,甚至去當女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風雨交加的夜晚,祖孫三人緊緊相擁避雨,暴風雨吹落了本就搖搖欲墜的窗戶,素芬沖出屋外,在電閃雷鳴之中拼盡全力將掉落的窗戶裝了上去。她在照顧了婆婆和兒子抗生近十年之后才知道張忠良早已背叛她,且不止跟一個女人。由此可見,素芬在張忠良離開期間經歷了諸多磨難,這些磨難多與生死息息相關,但她都咬牙挺過去了。面對張忠良的背叛她卻選擇了輕生,“因為千百年來我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以男人、家庭為生活中心,一旦這個中心無法繼續維持下去,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就沒有了繼續下去的動力,只有毀滅自己一條出路”[5]100-102。她長時間以來的心理寄托消失了,產生了幻滅感。其次,就外部環境而言,素芬經歷了從日本侵略至抗日戰爭的勝利,她原以為戰爭結束后張忠良便會回家,她就可以過上以前的生活。可是現實證明即使戰爭結束了,她也不會恢復至以前的生活。這是素芬的第二重幻滅。小芬在結尾處經歷了個人的思想轉變,雖然她對李志超的這種態度轉變是被迫的,是在時代大環境下不得不做出的轉變。但是素芬卻因為自己的幻滅感無以消解而最終走上了絕路。
從《同仇》到《一江春水向東流》,小芬和素芬誰的形象更具備現實意義?無疑,兩者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時代價值。小芬最后的選擇對于30年代的民族抗戰情緒是一種很好的鼓舞,兒女私情在國家危亡之際應當置于其后。素芬的結局既是婦女對時代的控訴,又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無論是敢于追求個性解放的小芬或是作為中國傳統女性縮影的素芬,她們都是被時代裹挾著被迫前進的堅強生存者,身上都散發著堅強勇敢、為母則剛的大無畏精神的光芒。但小芬最終為了家國存亡而選擇忘記個人的愛恨情仇,素芬沒有死于時代的苦難,卻喪生于她對愛情和家庭的幻滅。素芬的自戕在某種程度上亦是她對個人命運的一種消極反抗——僅憑個人微薄之力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通過死亡來做最后的抗議與掙扎。活著和死去都是受罪,正如影片末尾處素芬婆婆哀嚎:“可憐的是我們還活著受罪啊!”相較于有一定教化色彩的小芬形象,素芬的舉措更加接近生活真實,對時代所產生的影響也更加振聾發聵。
三、女性出路何處探尋?
《傷逝》是魯迅1925年創作的短篇小說。20世紀20年代,當整個社會正沉浸在五四運動給社會帶來的巨大沖擊之時,子君作為在女性解放運動中的典型代表,與小芬和素芬兩人有相似之處,但又與她們都不相同。子君和小芬一樣,敢于違背家庭的意愿與自己喜歡的男人在一起,這是對封建傳統禮教的挑戰。葉生記在《痛讀彷徨》中提出男女青年的方針為子君所言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6]她又與素芬一樣,在婚后遭遇了許多困難且試圖努力克服,最終卻都選擇了不歸路。子君區別于素芬的一點是她的苦痛一部分來源于不合理的經濟環境以及涓生、子君兩人的弱點——沖破舊禮教束縛后并沒有與生活搏斗的勇氣。[7]素芬戰勝了生活中的瑣碎與艱辛,卻失去了原本以為最不會失去的東西,即丈夫的忠誠。20年代的子君在時代的鼓舞下,敢于像娜拉一樣“出走”去尋求個人解放,然而卻由于時代及個人的局限性,最終湮沒于時代的洪流中。正如楊占升在《略談<吶喊><彷徨>對現代小說發展的影響》中提到的:“《傷逝》中的涓生子君有敢于同封建勢力作斗爭的先進性,但也有不考慮實際、孤身戰斗的局限性。”[8]
小芬身上的時代色彩非常明顯,涉及到了救國圖存的問題。啟蒙和救國之爭的問題早在啟蒙運動之初便已有端倪,啟蒙者們提出了個性解放的主旨,新潮社一代繼承了陳獨秀所提出的“改變中國比救國更重要”。因此此時個性解放高于民族救亡。啟蒙者與民族主義者的爭論與合作持續許久。當面對內憂外患之時,啟蒙者們不得不與民族主義者合作,將愛國主義作為前提,但自始至終,啟蒙在他們心中仍舊高于反帝。也正是因為此,啟蒙者們被大眾所詬病。啟蒙者在初期對于自身的地位十分自信,直至五卅慘案發生以后,他們由革命主導者變為革命旁觀者、追隨者,他們由自信、激情轉為失落,這也使得啟蒙者們開始個人剖析式的自省,意識到知識分子的有限性,這樣的心態一直持續著。30年代的小芬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歷史需要中產生的,此時民族危難高于個人追求個性解放,這也是她為何選擇扔下手中準備刺向李志超的刀。
《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明月意象在影片中反復出現,明月在影片中是素芬對丈夫歸家的心理寄托。同時,電影圍繞素芬和張忠良所展開的兩條線索同時發展,在這時明月意象的出現更是對電影結局的一種暗示。阿隨這個意象在《傷逝》中也頻繁出現,它對全文的主題表達有一定作用。嚴家炎認為阿隨先后四次出現在文中,這加深了全文的悲劇性,起到烘托渲染的作用。[9]張世垠在《阿隨·子君·文化革命》中提出從阿隨及阿隨的命名可以看出子君的愛和愛的消逝。[10]43-45從這里看來,明月的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素芬命運的悲愴,明月雖已圓,愛人與昔日的溫存卻早已不在。
40年代的素芬和子君一樣,在愛情伊始都對未來生活充滿憧憬,但最后卻都選擇了最極端的方式結束生命。素芬是中國廣大勞動女性的代表,她們勤勞樸實、堅強善良。但素芬全心全意地付出,最后卻換來了丈夫的背叛。她在自戕之前必定做了許久的心理斗爭,她無法理解亦無法排解,終究無法接受現實,選擇了縱身一躍。縱身一躍于她而言是一種解脫,又何嘗不是她的心中不甘。正如路人所言“他媽的,現在這年頭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素芬縱身一躍后只余后人的一聲嘆息。
從20世紀20年代的子君到30年代的小芬再到40年代的素芬,這些女性人物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出路。然而時代背景在變化,不變的是悲慘的命運。無論是有聲的抗爭或是無聲的反抗,至少都對那個時代產生了一點波紋。這些文學作品與影視作品中的女性也豐富了藝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并在不同歷史時期產生極有價值的社會意義。
參考文獻:
[1]程步高.新年感想[N].申報·電影專刊,1934-1-1.
[2]陸茂清.影人蔡楚生屢創輝煌[J].文史天地,2019(09).
[3]慧蘭.同仇[N].申報·電影專刊,1934-1-6.
[4]李煥征.月兒彎彎照九州——試論蔡楚生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女性形象建構與左翼立場[J].當代電影,2016(12).
[5]俞蕾.試論鄭君里影片中的現實主義特質[J].美與時代(下),2019(07).
[6]葉生記.痛讀彷徨[N].世界日報副刊,1926-9-30.
[7]巴淑.戀愛與結婚——再讀《傷逝》[N].大公報,1948.
[8]楊占升.略談《吶喊》《彷徨》對現代小說發展的影響[J].魯迅研究,1983.
[9]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J].文學評論,1981(5).
[10]張世垠.阿隨·子君·文化革命[J].溫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01).
◆ 基金項目: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代電影文學資料發掘、整理與資源庫建設”(編號18ZDA262)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趙雪晴,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專業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