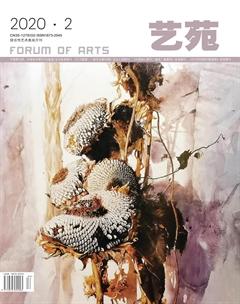開放式編纂與女性主義自覺
【摘要】 蘇珊·海沃德的《電影研究:關鍵詞》在英美學界暢銷多年,該書精選了近200個關涉電影研究的關鍵詞,對重要的電影類型、電影理論和電影運動做了歷史的概覽。海沃德緊緊掛靠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理論,對階級、種族、性別等議題采取了高度關注的姿態。同時作為一名女性學者,海沃德的行文中具有一種女性主義的自覺。該書開放式的學術思路和編纂方法同樣十分有趣,可以為國內學者提供一些啟示。
【關鍵詞】 《電影研究:關鍵詞》;歐洲中心論;女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英國學者蘇珊·海沃德撰寫的《電影研究:關鍵詞》[1](Cinema Studies:the Key Concepts)一書自1996年出版至今已經再版了四次。在這本書中,作者拋開那些繁雜的技術術語與專業詞匯,精挑細選了近200個關涉電影研究的核心詞匯以饗讀者。這些關鍵詞的選取雖然并非毫無爭議,但就電影研究這一復雜的現代知識生產實踐而言,該書無疑是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最為優秀的著作之一。海沃德的聰明之處在于她并未將這些電影研究中的關鍵詞當作僵化的概念,而是讓各個關鍵詞隨時都處在一種動態的對話關系之中。作者宣稱她最初的構想是將這本書做成一部有深度的專業術語匯編,但通過“最初”這樣的表述,讀者應該能感受到其學術“野心”。熟悉英國文化研究歷史的讀者不難發現《電影研究:關鍵詞》與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一書的內在關聯。這一跨時代的學術對話不僅顯示了海沃德本人的學術師承,亦清晰地昭示了1970年代之后英美文化研究的重心轉移。
作為一名女性學者,海沃德的學術視野中具有一種女性主義的自覺。在一些我們常識里認為不指涉性別意涵的詞條中,海沃德也總是能敏銳地將其放在女性主義的框架里來進行討論,并發現其父權制話語修辭。對于我們習以為常的異性戀思維方式,海沃德同樣提出了警告,在她看來,那些雙性戀的、跨性的、易性的電影文本同樣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此外,作為一名西方白人學者,海沃德亦難得地保持了一份警醒。在她的論述中,我們常常會看到她對“歐洲中心理論的偽普世主義”的反思。縱觀海沃德的理論實踐,她一直努力“試圖表征能擺脫父權制的、歐洲中心論的和異性戀的常規化的主導性”。[2]4爭議當然是在所難免的,文化和學科背景的差異都將導致學術觀點的不同。幸運的是,《電影研究:關鍵詞》中所有討論都是開放式的,很多話題如果繼續展開將打開一片電影研究的新天地。
一、開放式的學術思路和編纂方法
《電影研究:關鍵詞》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其開放式的學術思路和編纂方法。該書中的所有關鍵詞都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并配有中英文對照的詞條目錄,讀者可以像查詢傳統詞典那樣很容易就找到自己想要查找的內容。正如書名《電影研究:關鍵詞》所顯示的,作者對詞條的選擇頗費苦心。既然是有關電影研究的關鍵詞,那么那些無關電影研究宏旨,只有專業人士才明白的技術術語就被排除了出去。同時,作者的學術思路更靠近時下流行的文化研究。種族、性別、階級、性取向都是作者理論關注的焦點。而像中國學者耳熟能詳的一些詞匯并未出現在這本大部頭的著作中,如巴贊的“攝影影像本體論”[3]1、德呂克的“上鏡頭性”[4]9等。
關鍵詞只是該書的一部分,由這些關鍵詞輻射出的討論和派生詞群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我們可以將該書的閱讀過程描述成一種輻射式閱讀。讀者從一個點出發,思維向四面八方輻射,這一過程猶如邁入了馬爾赫斯筆下小徑分叉的花園,直到最后才又重新回到起始的地方。書中用黑體標注出了與該關鍵詞相關的其他關鍵詞,讀者如果對這個概念不甚理解,或者想更全面地理解這個詞匯的內涵與外延,則可以通過前后跳躍式的閱讀去獲得自己想要了解的內容。作者同時在每一個詞條的后面提供了一條線索,告訴讀者如果想更好地了解該關鍵詞應該去哪些相關的詞條中去查找。
以該書的第一個關鍵詞“缺席/在場”為例,作者在書中用黑體標出了“敘事”“性別”“話語”“類型片”“西部片”“觀影者”“主體”“俄狄浦斯軌跡”“想象界/象征界”“凝視”等關鍵詞。此外,作者在解釋每一個關鍵詞的時候,并沒有將其限定在一個狹小的范圍中,而是突出了對話性。一言堂式的獨白讓位于話語霸權裂解后的眾聲喧嘩。海沃德并沒有用權威的語氣告訴讀者每個關鍵詞的定義,而是在對每一個關鍵詞的論述中放置了好幾種觀點。讀者只有認真比較了這幾種觀點,才能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當然讀者也可以不同意這些觀點,而是在這種討論的氛圍中去發展自己的觀點。《電影研究:關鍵詞》這種開放式的編排打破了傳統的線性文本閱讀習慣,而更像網絡超文本的閱讀習慣。在閱讀一個超文本的過程中,讀者的信息量總是呈幾何倍數增加的。
海沃德在書中還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鮮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視角。這些新研究領域很多都是國內從未認真關注或者很少關注的。還有一些電影研究中的核心問題,雖然每個學習電影的人都非常熟悉,但我們的認知中卻存在著很多的誤讀。如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從文化的視角研究華語電影中的身份認同和離散經驗,但對于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問題與電影的關系則甚少關注。研究美國電影的學者的主要興趣也都集中在好萊塢主流電影上,而對美國電影中的抵抗性文化和亞文化則了解不多。盡管“在一個等級森嚴,由階級、種族和性別組織起來的社會,真正的客觀性絕無前景可言”[5]218,然而這樣的研究方法無意中正好重復了父權制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異性戀主導話語的霸權,很多值得認真研究的議題被我們自動遮蔽了。如處在好萊塢邊緣的美國黑人電影國內學界的研究就很不充分,我們既不了解非洲裔美國人電影的歷史,也不清楚其真實的現狀,以及它與其他地區的黑人電影之間的關系。將美國電影想象為單一的主流好萊塢電影的發展史無疑是十分危險的傾向,這就意味著我們犯了同質化的錯誤,由此得出的關于美國電影的結論自然也經不起推敲。
三、余論
電影學研究的概念何其豐富、龐雜,任何試圖將這些概念一網打盡的做法最后只能淪落為看似面面俱到的泛泛而談。對于那些初窺門徑的初學者而言,要想從這些汗牛充棟的理論概念中步入電影研究的殿堂是何等地艱難,更別說深入到當下學術研究的前沿和核心地帶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蘇珊·海沃德從電影研究的迷宮中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捷徑。那些苦苦尋找不到論文選題的初學者如果順著海沃德開放性的論述繼續討論下去,沒準兒將發現一塊電影研究的新大陸。
盡管每個作者都希望自己的論著能夠盡可能的客觀與全面,但爭議和紕漏仍然是在所難免的。如在“理論”這一關鍵詞中,作者根據多樣性和單一性將電影理論劃分為三個時期:1910-1930年代為多樣性時期;1940-1960年代是一系列單一理論時期;1970-2000年的世界電影理論則又回到了多樣性時期。這樣簡單的劃分不僅牽強,也無法說明各個時期電影理論之間的內在關系。被劃入“多樣性時期”和“單一性時期”中的電影理論內部的差異也被模糊化了。再比如對女性的觀影快感,海沃德為我們提供了三種解釋:認同銀幕上被動的、物戀化的女性角色(受虐狂);采取易裝的策略認同銀幕上的男性主人公;觀影時獲得一個雙性戀的位置。但是這又如何解釋當下的電影生產所建構的女性觀眾對男明星身體的視覺消費呢?現代社會,隨著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流行文化中對“男色”的消費已經是一個隨處可見的現象。筆者認為,女性觀影者在觀影過程中也可以獲得一個主體性的觀看位置,女性同樣也可以在男明星的身體中注入自己的女性欲望。
學術對話、學術爭鳴乃是學術的生命力之所在。中西文化的差異、學術背景的迥異都會造成學術視角、學術觀點的不同。我們盡可以對這本《電影研究:關鍵詞》提出批評,但只要它能為國內的電影學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視角和啟示,幾位翻譯者所付出的艱辛就是非常具有價值的。
參考文獻:
[1]蘇珊·海沃德.電影研究:關鍵詞[M].鄒贊,孫柏,李玥陽,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羅崗,顧錚.視覺文化讀本[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3]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4]楊遠嬰.電影理論讀本[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5]陶東風.文化研究讀本[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6]齊亞烏丁·薩達爾.東方主義·出版導言[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楊夢晨,江蘇師范大學傳媒與影視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