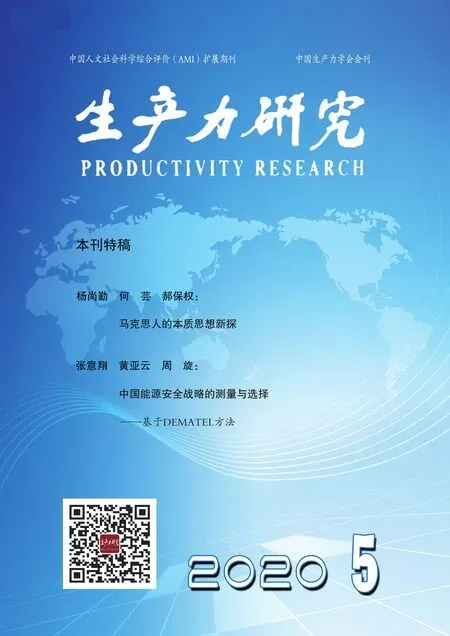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因素的時變性研究
——基于TVP-VAR 模型
吳志芳,張青龍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237)
一、引言
在我國及世界經濟疲軟的當下,研究人民幣匯率波動及其影響因素的時間波動性,對鞏固人民幣國際地位、加快我國經濟結構升級、維護全球經濟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匯率波動常出現參數不穩定的情況,研究匯率中常用的GARCH 或是VAR 模型不能描述出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可能會給出有偏的參數估計,錯估變量之間的真實影響,而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TVP-VAR)模型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捕捉到經濟變量相關關系的時變性特征。我國最早引入該模型的是陳宗義(2012)[1],基于2001 年6 月—2011 年3 月的數據實證分析后發現人民幣匯率對于中國長期貿易順差的影響較小。鄧黎橋和王愛儉(2015)[2]建立人民幣均衡匯率決定的中美兩國兩階段理論模型,利用TVP-VAR 模型實證分析發現國際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越來越大,金融機構在匯率決定中逐漸占據重要位置。江春等(2018)[3]用含隨機波動的TVP-VAR 模型分析人民幣匯率的動態變化,發現拓展泰勒規則匯率模型中的變量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并在短期與長期內表現明顯區別。
盡管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素及其變動特征進行了研究,為本文研究人民幣匯率問題打下了基礎。但是,國內學者在運用TVP-VAR 模型研究匯率波動影響因素時考慮的影響變量較少,不能全面解釋匯率的變動,特別是沒有將中美貿易差額這個變量引入TVP-VAR 模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運用TVP-VAR 模型,選取了5 個影響匯率的因素,特別是引入了中美貿易差額這個變量,以2005 年7 月以來的三次匯改為時間點,探討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隨時間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并且通過中美貿易差額衡量我國對外貿易情況,既能反映我國產業升級背景下對外貿易對匯率影響程度的變動,也能反映中美貿易戰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情況。
二、模型選擇及數據說明
為了研究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因素的時變性,本文構造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之間的時變參數向量自回歸(TVP-VAR)模型。該模型由國外學者Primiceri(2005)[4]首先提出,Nakajima Jouchi(2011)[5]證明時變參數確實能提高模型的精準度。我國學者陳宗義在2012 年引入國內研究人民幣匯率對中國貿易順差的影響。TVP-VAR 模型是一種非線性時變分析模型,模型的系數、協方差都隨著期數的變化而變化,可以靈活捕捉經濟變量相關關系的時變性特征。
(一)模型建立
TVP-VAR 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其中yt為(k×1)階向量,B1t,…,Bst,Bst為(k×k)階時變系數矩陣,遞歸識別約束條件;At是一個下三角矩陣,對角元素為1;∑t=diag(σ1t,…,σkt);定義βt是由B1t,…,Bst堆積而成的行向量;at=(a1t,…,aqt)為At的堆積行向量;ht=(h1t,…,hkt),且(Nakajima Jouchi,2011)。
(二)變量解釋與處理
本文截取2004 年9 月—2019 年3 月的月度數據,除匯率外選取衡量利率、貨幣供應量、國家外匯干預、對外貿易量、資本開放度等變量[6-7]。其中匯率選用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利率水平用中美利差衡量,中國利率選用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美元利率選用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貨幣供應量選用中美廣義貨幣供應量即M2 的差;外匯干預變量用國家外匯儲備衡量;對外貿易因素選用我國對美進出口差額衡量;資本開放度用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和金融項下資本流入與流出凈值來衡量。
選用中美利率差和貨幣供給量差是為了識別中美貨幣政策的不同給人民幣匯率帶來的沖擊,分別代表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選用中國進出口貿易差額指標是為了表示中美貿易往來和摩擦問題給人民幣匯率帶來的影響;本文采用以往學者的做法使用國家外匯儲備作為外匯干預的衡量指標。根據王永中(2013)[8]的研究,主要有三種關于中國外匯儲備數據的統計口徑,本文選用中國人民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外匯占款數據,因為央行外匯干預是外匯占款余額變動的主導因素;選用資本開放度指標是為了衡量資本在國內外的流動情況。
對匯率、中美利差取一階差分,對外匯儲備、中美貿易差額取對數差分,取中美M2 差額的增長率,以確保諸數據的平穩性。以上六個變量,外匯儲備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資本開放度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其余數據均來源于wind 數據庫。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模型結果及檢驗
通過參數滯后一階和滯后兩階的比較發現對TVP-VAR 模型中參數滯后兩階結果較合理穩健,所以本文的模型參數選擇滯后兩階。用MCMC 方法迭代10 000 次,得到有效樣本。
本文模型估計結果可以說明,基于Geweke 的CD 收斂診斷統計值均未超過5%的臨界值1.96,不能拒絕原假設;且無效因子都比較小,最大的僅70.61。這兩個值能說明參數和狀態變量的抽樣是有效的,即滯后兩階的TVP-VAR 模型結果比較合理。
(二)不同時期脈沖響應圖
脈沖響應圖可以用來考察擾動項的一單位標準差變化在當前以及未來各時期對模型中各內生變量的影響。TVP-VAR 模型可以在時變參數估計的基礎上得出兩種不同形式沖擊反應圖。
圖1 給出的脈沖響應圖含義是在樣本各個時期,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的單位沖擊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的影響。其中短虛線代表滯后1 期即1 個月,長虛線代表滯后6 期即6 個月,實線代表滯后12 期即1 年。

圖1 不同時期人民幣匯率與各變量的脈沖響應圖
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反應分別是圖1(2)中的εi↗→e 和圖1(5)中的εm2↗→e。中美利差變動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如圖1(2),當中美利差正向變動,中短期內人民幣匯率下降,即人民幣升值;長期的脈沖響應圖表現出時變性,在50 期前對人民幣匯率影響為負,這可能是由于此前我國對資本管制比較嚴格;50 期至60 期,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利差對匯率的影響正負反復;60 期后,中美利率水平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符合非拋補利率平價理論,即若本國利率高于外國,本幣在遠期將會貶值。但匯率對利差沖擊的脈沖響應數值上比較小,這可能是因為我國存在資本管制的原因(蓋靜,2017)[9]。
匯率對中美貨幣供應量差沖擊的脈沖響應圖如圖1(5)所示,無論在長期還是短期,響應圖都表現出了時變性。中美貨幣供給量差在60 期,即2009年10 月前數值為負,在60 期以后為正。從匯率對中美貨幣供給量差波動的反應得出,在50 期以前影響程度有下降的趨勢,在50 期至60 期間影響程度突然猛增,后又回到一般水平,這可能是由于4 萬億的短期作用,在60 期以后匯率的響應程度有小幅上升。從數值正負看,貨幣供應量對匯率的影響符合匯率超調模型,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因為中美貨幣供應量差額的增大迅速上升,而中長期中由于商品市場價格的調整,人民幣匯率下降,人民幣升值。
圖1 中(6)顯示了資本市場開放度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εf↗→e)比較大。當資本市場開放度有1單位正向沖擊,即資本流入國內規模擴大時,短期人民幣會升值,因為資本流入引起本幣需求的擴大,但長期看當期的資本流入會導致遠期匯率上升即人民幣貶值。導致長期中資本流入對匯率的正向影響有兩個原因,第一是資本流入國內后取得了預期目的,國內的經濟環境無法繼續吸引資本活動而外流;第二是由于樣本區間內人民幣匯率一直在進行市場化改革,而匯率市場化改革會有效消弱資本市場開放程度引起的人民幣升值,甚至導致人民幣貶值(趙茜,2018)[10]。在60 期以后,資本市場開放度對人民幣匯率中長期的正向影響有所降低,可能是由于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步入正軌,上述削弱效應有所下降。
圖1(4)的中美貿易量對人民幣匯率的脈沖響應圖(εt↗→e)表現出明顯的時變性特征。中美貿易量對人民幣匯率的沖擊為負,且主要表現為短期影響,在樣本區間內負向沖擊程度一直在下降,從2013 年中美貿易對匯率的影響以更快的速度下降。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導致這個結果:第一,中美貿易順差通過經常賬戶使人民幣有持續升值的壓力,但我國資本管制越來越少,資本流動可能會取代貿易因素成為匯率變動的重要因素;第二,我國正面對經濟結構升級,致力于刺激國內消費和產業結構向高科技產業升級,以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這也意味著貿易會在匯率決定中占據越來越小的地位。
央行外匯干預對人民幣匯率作用(εr↗→e)的脈沖響應圖如圖1(3),當外匯干預有一單位正向沖擊,即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率當期增加一單位,人民幣匯率在1 期內將會上升,即人民幣貶值,說明央行外匯干預在短期內對穩定人民幣匯率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幅度有限。從中長期看,央行外匯干預反而會引起人民幣匯率波動更加劇烈,這與司登奎等(2018)[11]結果有所不同,但匯率波幅限制也不能過度放松[12]。
(三)不同時點脈沖響應圖
圖2 給出的是時點脈沖響應圖,圖中短虛線、短虛線、實線分別代表第9 期、第68 期、第130 期的沖擊反應過程,即2005 年7 月、2010 年6 月、2015 年8 月,滯后期數為12 期。這六個變量對匯率的沖擊在三個不同時點走勢圖大體上保持一致,可以說明TVP-VAR 模型的穩健性。

圖2 不同時點人民幣匯率與各變量的脈沖響應圖
來自匯率自身的沖擊(εe↗→e)在三個不同時點的走勢相同,如圖2(1)所示,在沖擊剛發生時就達到最大,后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減小,在約10 期時沖擊減小為0;來自中美利差的沖擊(εi↗→e))如圖2(2)在第1 期時達到最大,后隨時間逐漸減小,在130 期時給中美利差1 個單位沖擊對匯率的影響比其他兩個時點更加反復,可以說明當前的經濟形勢更加復雜;圖2(5)中中美貨幣供給量對匯率的沖擊(εm2↗→e)開始為正向,在第1 期達到最大,后逐漸轉為負向沖擊,但三個不同時點上負向沖擊達到最大的時期不同,130 期上中美貨幣供給量對匯率的負向沖擊延續的時間更長,這可能是我國貨幣供給量近年來保持高速增長的結果;圖2(6)中顯示資本開放度對匯率的沖擊(εf↗→e)在三個時點上保持高度一致,開始時表現為負向沖擊,在第1 期達到最大,后表現為正向沖擊,在第5 期達到最大后逐漸減小。從最大影響和持續時長看,資本流動是匯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分析中美貿易對匯率在三個不同時點上的沖擊走勢(εt↗→e),如圖2(4),無論從最大沖擊幅度還是沖擊持續時間都可以看出對外貿易在匯率決定因素的重要性越來越小;圖2(3)中外匯干預變量(εr↗→e)對匯率的沖擊開始為正,在第1 期正向沖擊最大,表示央行外匯干預在初始能穩定匯率,但是穩定效果并不持續,很快會加劇匯率的波動,擾動在第5 期達到最大。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立TVP-VAR 模型研究人民幣匯率波動影響因素的時變性特征,模型中包含六個經濟變量,得出兩種不同形式的脈沖響應圖形,并就脈沖響應圖具體分析了2004 年10 月—2019 年3 月間人民幣匯率影響因素的動態波動性特征,得到如下幾個結論并就此給出建議:
第一,利率對匯率的影響時變性不明顯,貨幣供給量對匯率的時變性波動影響較大。因為我國資本流動管制仍較嚴,導致貨幣政策對匯率作用的傳導機制受阻。貨幣政策對匯率解釋程度相對較小,說明動用貨幣政策來影響匯率的手段效果可能達不到預期,故國家在采用貨幣政策干預經濟時可以較少考慮對匯率的干擾作用。
第二,我國資本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很大,是人民幣匯率的主要決定因素,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加大,其對匯率的影響可能還會增加。資本市場擴大開放在初始會給人民幣帶來較大的升值壓力,但并不長久,匯率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影響會抵消升值壓力,所以國家應該保持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同步協調進行。
第三,隨著資本流動在國際收支中重要性的顯現以及我國產業升級的國家戰略,對外貿易因素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程度在逐期下降。面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國家應專注于引導國內產業升級,提升我國綜合實力。
第四,央行外匯干預短期內能穩定匯率,但會在長期內導致匯率更大幅度的波動,所以央行應更謹慎的干預外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