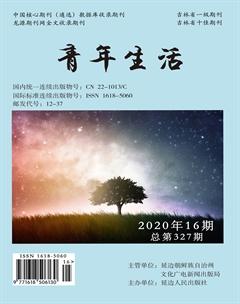淺談政府官員如何提升自身媒介素養能力
方志向
摘要:作為一個特殊且重要的信息生產者----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在當下不斷變化的全媒體時代,其工作職責、社會功能、責任等方面都隨之加入了“媒介屬性”這個新的要素。由此政府部門和官員在工作生活中所表現出的言行舉止、思維意識,也就被賦予了更高的對媒介素養的要求。
關鍵詞:媒介素養;危機應對;輿情掌控
早在2012年,不少學者或單位都對政府機構,尤其是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給出了具體的要求或是定義,如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就提出:官員的媒介素養是指官員認識和使用媒介,運用媒介進行輿情分析、管理公共事務、塑造政府形象等能力①。那么政府官員在日產工作生活中應該具備哪些基本的媒介素養,用以提升自身的危機公關的能力呢?
一、全媒體時代,政府機構和官員應具備的一些基本媒介素養
1.提升對信息是非真偽的辨別能力,加強主動糾錯的意識
許多政府公務人員之所以對新媒體持有偏見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網絡新聞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假新聞、謠言或是來源不實、內容故意扭曲夸大等特征。相對于他們比較特殊的身份和可能會引起的社會影響而言,這些特征導致了政府公務人員不敢,也不愿參與到新媒體的使用中來。雖然在傳統媒體占主流的時代,對于信息的分析、理解、判斷能力的教育培養就一直在被不斷地強化,但社會化媒體時代傳播主體的多元化、傳播渠道的多樣化,都使得信息構成更加復雜②。于是,無論是在接受信息、處理信息,還是生產信息的過程中,都會存著一定的風險性。而政府機構和政府公務人員作為信息生產環節的重要一環,其生產的信息本身就具有真實的屬性,一旦在此屬性上出現了偏差,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必將大打折扣。這對于政府機構進行社會管理、推行執政理念、樹立政府威信和傳播政府形象是非常有害的。因此,提升政府公務人員對于信息是非真偽的辨別能力就顯得更外重要。
主動糾錯意識還應該體現在,政府機構和公務人員對于網絡上傳播的虛假新聞和不實信息的處理措施,不能寄希望于網絡自律和滯后于媒體辟謠。例如2016年6月,南方各主要城市,尤其是武漢市再一次進入了“看海模式”,甚至在一周之內上升到了城市內澇災害的等級。這個時候,在網上傳出了“德國防洪神器”的新聞,并附有圖片和文字解說。一時間,抨擊政府不作為,指責中國防洪技術“軟弱無能”的新聞訊息充斥在各類網站和社交平臺上。雖然,在幾天之后就被網友成功逆轉,如“德國防洪神器,德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以及使用了類似防洪工具但依然阻擋不了洪澇災害的新聞、圖片和視頻被網友們自發的傳播于網絡上,消除了這一次的政府信任危機。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這是網友們自發的力量,許多圖片、視頻明顯是源自國外的網站。也就是說,網絡環境的自律性幫助政府度過了這次危機,但是下一次呢?
2.建立開放式信息交互平臺
有一個現象,我們不難發現。凡是由政府向社會公布的信息,幾乎都是用網站的形式或通過者官方微博、微信的方式進行廣而告之。而政府公務人員似乎并沒有自己的微信號或者微博,或者說這些信息交互平臺其實他們都有,只不過不向社會公開而已。
原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概括了中國官員面對媒體的三種心態:不愿說,不敢說和不會說。他認為“不愿說”是中國官員的低調和內斂;“不敢說”是怕“引火燒人”;“不會說”則是不懂新聞傳播規律③。這是對目前政府公務人員對于媒體態度的總的概括,雖然并不全面,但也算切中了要點。
由于以上各種原因,在加上政府機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貫徹執行,讓政府公務人員的媒介素養變得越來越淡薄。一旦有媒體對某些重大或突發的社會實踐進行采訪,或者詢問相關信息時,公務人員則非常自然地告知對方“請關注官方網站”、“我們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具體信息我不方便透露”或者干脆說“你去問領導”,在某些人員極不配合情況下,則會發生要么不見面,見面不交流,交流無內容或者干脆直接驅趕、搶奪攝像機的情況。最終造成的現象或者產生的影響是,媒介素養確實和政府公務人員有關,但是卻和具體的某一個人員無關。即便涉及到某個人身上,也可以推卸給單位或者群體。至少自己是不會主動去承擔責任,展現自身的媒介素養水平。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部分政府公務人員他們與媒體交流的意識和能力是缺失的。而加強這種交流的能力,不能僅靠官方網站和微博來代你發言,更不能完全依賴于新聞發布會上,新聞發言人的通訊文稿。只有在日常,開放自己的微博,公布自己的微信,將與媒體、與民眾的交流變為一種常態,逐漸熟悉與媒體交流的狀態,這樣才會在發生一些需要官員第一時間面對媒體和民眾進行回答時,不至于搞得群情激奮。
再者,2007年1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通過,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代表著,至少在制度層面,政府機構必須向民眾搭建一個信息交流的平臺,至少是信息公布的平臺。一時間,在政府的官方網站上出現了“信息公開”、“交流互動”專欄,甚至是“市長郵箱”、“市長熱線”等直接可與政府主要領導人對話的渠道。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不少地方政府網站上發現如下問題:公開內容有限,相當一部分內容較為形式化,缺乏時間特征;信息公開的渠道與方式不足,往往是政府公開什么,公眾才可以了解什么,對于某些公眾申請的政府官員個人行為信息公開的要求,政府往往響應冷淡等等④。另外,也存在著信息更新速度慢、政績性訊息大量充斥網站、維護優化性能差、頁面布局混亂、主要信息指示不清等其他問題,這些都會導致網站最終成為一片廢墟、無人問津。
二、對于公共突發事件的應對,政府機構和官員應該走在媒體前面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移動終端設備性能的不斷提升,民眾接受新聞
訊息的渠道不再只能通過傳統媒體,而更多的可以選擇自媒體。到了2016年,我們明顯地發現,社會重大、突發事件的發生頻率比以往更頻繁了,這并不是因為社會秩序相較以往變得動蕩不安,而是我們了解社會事件的渠道太多了。隨著全媒體時代的到來,政府的確面臨著頻繁應對危機事件的挑戰。
因此,在一次又一次處理危機事件的過程中,政府機構和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更加注重自身處理突發、重大社會事件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得以改進。
1.轉變觀念,變掌控為引導,從提防到交流
2009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春季開學典禮上就提出“官員要具備同媒體打交道的能力”、“尊重新聞輿論的傳播規律,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要不媒體保持密切聯系,自覺接受輿論監督”。而到了2013年,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習總書記強調大力提升政法干部的“五個能力”,其中就包括“新媒體時代輿論引導能力”。
以上習總書記的話語,其實就是在強調在新媒體時代,政府官員應該著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素養。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應該是要轉變觀念,不再把媒體當做因為要受到政府某部門管轄,就必須按照政府部門要求辦事,決不能自作主張、自主發聲的“傳話筒”。更不能敵視媒體,甚至是仇視媒體。對于媒體角色的定位、功能和權利,應該正確認識并堅決維護。因此,媒介不僅是政府的管制和掌控對象,還應該是政府合作的對象。
在發生重大、突發社會事件后,政府應該積極地向媒體公布信息,允許媒體就事件的過程和產生的后果進行提問并給予正面回答。由于該類事件往往多帶有群體性、傷亡性等特殊屬性,因此民眾對此的關切程度要遠遠大于一般的新聞內容。如果對此,政府總是保持緘默不言,或者遮遮掩掩,必然會引發媒體的追究和民眾的猜疑。在事件起初,政府若不能開誠布公地對社會發布主要信息,就會在一開始喪失主動權,漸漸地就失去了主導權。1947年,美國社會學家奧爾波特和博斯特曼總結出一個決定謠言的公式,即謠言=(事件的)重要性X(事件的)模糊性,并指出謠言產生和事件重要性與模糊性成正比關系⑤。當政府機構不愿想社會公布真實準確的信息,而媒體和群眾自發組織的探究活動往往會存在模糊性,這些探究活動所得出的細節和結論又有可能與政府之前對于該事件采取的規避行為產生沖突,如此一來必要的溝通交流就更加無法正常推進,更何談爭取引導社會輿論的效果呢?
因此,政府在工作中要建立完善信息發布制度,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在公共危機事件發生后,積極與媒體進行交流,具體真實地向媒體告知內容細節,和媒體一起向民眾發布信息并接受咨詢,才能達到安撫群眾情緒,緩解緊張氛圍的效果,也才能讓政府在一開始就掌握事情的主導權。
2.提供更多形式的媒介素養學習機會和制定考核機制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政府公務人員在入職之前都參加過應對社會公共危機的專業訓練,也不能要求他們在入職期間就掌握高超的與媒體打交道的本領。因此,在工作期間參加媒介素養培訓學習就顯得格外重要。
目前,政府公務人員往往是通過參加課程培訓、聽講座的方式學習和積累媒介素養,這些停留在紙面上或是PPT上的培訓教育會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政府公務人員,尤其是那些崗位性質要求經常和媒體打交道的人員,更需要的是能夠直接產生實際效果的技能培訓。因此,可以嘗試與媒體、高校進行合作,請資深記者、編輯、新聞發言人以及在高校里從事新聞學、傳播學領域專業教育的教師,與這些人員進行模擬現場教學、一對一演練、實戰訓練等,切實提升他們的危機公關能力。在這一點上,北京市行政學院在中國傳媒大學建起媒介素養基地,由傳媒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幫助其組織針對公務人員的媒體實戰演練⑥。我們認為,這種形式值得推廣,它既有助于參加培訓的政府官員將所學到的知識技巧與實際結合起來,也有利于在校的相關專業教師和學生了解社會。
另外,考核機制的建立是對日常媒介素養培訓的制度性保障。要想真正把媒介素養轉變為政府官員的基本素養當中,適當的考核手段和淘汰機制就必須成為考察、提拔或是審核、淘汰一個官員的重要判斷依據。其次,還可以繼續在全國各省、市級電視臺推進“電視問政”或類似的欄目。借助媒體的力量,讓政府官員一方面重視自己的工作職責和工作業績,另一方面也進一步進行了媒介素養的實踐,并將官員每一次問政后所做出的回答效果和群眾代表所給出的評判分數作為其提拔或是降職的判斷依據。
參考文獻:
[1]周大勇,王秀艷,《官員的媒介素養與政府形象傳播》[J].中共中央黨校報,2013(8):94-98.
[2]彭蘭.《社會化媒體時代的三種媒介素養及其關系》[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3(5):52-60.
[3]魏盼盼.《從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看我國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J].赤峰學院學報,2011(4):189-194.
[4]田曉平.《新媒體語態中政府官員媒介素養的缺失與提升》[J].寧波教育學院學報,2015(8):111-113.
[5]裴志林,張傳香.《政府的媒介素養與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J].學習與探索,2012(6):53-55.
[6]袁軍,王宇,陳柏君.《政府官員的媒介素養現狀及提高途徑》[J].新聞學與傳播學,2009(5):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