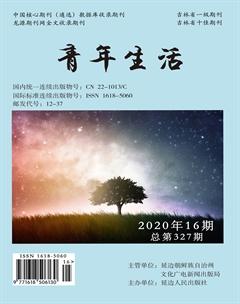試論述歷史學科領域內真理與價值的內在統一
解嬌
摘要:在中國史學研究中,求真與致用一直以來都是難以兩全的問題,如何才能達到求真與致用的統一,學術主張與現實需要應該怎樣調節,這些情況雖然存在但并不影響求真與致用貫穿史學的發展歷程。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出發,在真理與價值的統一方面看待史學的求真與致用,能夠深入剖析史學發展中出現的求真與致用的情況,探求真理與價值同求真致用的關系,強調史學的求真與致用相統一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史學;真理;價值;求真致用
自古至今,史學發展一直離不開求真和致用的雙重性質。不論是比較《春秋》、《左傳》與《史記》的敘事真實問題,還是近代史學家致力于探討史學究竟應該繼續求真還是迎合社會的發展需要走向現實生活的情況。我們不可否認史學的發展是離不開求真與致用的,但是求真與致用應該如何協調以致統一,由此促進歷史學進步和推動科學前進呢,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也許能窺得其中的一點奧妙。
目前來看,學者主要從史學的角度出發來研究求真與致用的聯系[1],或者直接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語境下分析史學的這兩種品格[2]。不論是直接以史學觀點為基礎,還是著眼于馬克思主義史學,鮮有將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融入其中去探討史學的學術追求和經世致用應該如何調節的論著。本文致力于從微觀的角度,通過結合真理與價值的統一理論,重點梳理史學發展過程中關于求真和致用的情況,剖析真理與價值同求真致用的關系,強調史學的學術求是與實際生活相互促進與統一的必要性,以及求真與致用推動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意義。
一、史學發展中的求真和致用
(一)先秦時期史學的求真與致用
早在上古時期的中國,歷史以口耳相傳、結繩記事的方式記載下來,那時就已經有了史官的存在。上古的史官分為左史官和右史官,左史官負責記錄國家的農業情況、天文或人事等,右史官掌管祭祀占卜、國家要事的記載。可見當時的史籍記錄既追求客觀,也注重實用價值。直到先秦時期,周王朝禮崩樂壞,分封的諸侯國紛紛變得強大起來,雖然周王室失去了對各諸侯國的統治力,但各地的思想文化、學術法制依舊能夠蓬勃發展,其中史學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在當時的社會中發揮著無法替代的作用。
歷史自古便有鑒戒的功能,其基礎即史事的真實和敘事的真實,而史學的求真傳統可從“趙盾弒其君”與“崔杼弒其君”見其端倪。先秦的史官能夠客觀記載歷史事件,還能為后人留下以古鑒今的依據,由此作為教育、指導后人做事或為人的一些準則和啟迪,這些依據也能視為歷史的真實性判斷與價值判斷結合在一起的體現。從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史事的客觀性和價值性融合于一體,史事的真實中蘊藏著價值,而價值也要依托事實才能存在。
(二)漢代史學的求真與致用
漢代史學中,以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影響最為深遠。司馬遷根據既往史料撰寫了《史記》,他參考、對比《春秋》《左傳》等書的記載,詳細記錄了黃帝時代至漢武帝時期的帝王將相、英雄人物、地理沿革及典章制度等內容。太史公追求歷史真實,并加以合理想象還原當時的對話場景。他還在每篇文章的結尾附加“太史公曰”,對歷史事件進行褒貶評價,蘊含著主觀性色彩。
從真理與價值內在統一的角度出發,對于史學研究要達到所謂的“正確”,不是單純認知意義上的真假、對錯,還包括價值觀的是非、對錯。[3]而司馬遷的《史記》正是具備了這樣的特點,以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基礎,司馬遷針對事件中的人物做出針砭時弊的評價與判斷,傳達史官的價值觀,再將價值觀的是非曲直賦予事件本身,讓史事兼及價值判斷,使歷史事實具備了訓誡和教育的功能,給予后人以指導和準則,這也實現了歷史學求真與致用的統一。
(三)唐代史學的求真與致用
劉知幾作為唐朝著名的史學理論家,他的代表作是《史通》。這本書中不僅記載了系統的史學理論,還主要表明了史家記載歷史的原則,就是要堅持秉筆直書的品質,反對曲筆描寫和模糊事實的做法。書中的《直書》與《曲筆》兩篇文字,深化了直書這一史學理論,強調了求真在中國史學的地位與作用。
《史通》一書不僅追求了史事記錄的真實,還具備了自身的獨特價值,即為后輩史家做出了學術研究的標準和要求。實現了史學求真與致用的統一與協調,讓求真成為制約史家實際活動的客觀尺度,而致用則成為追求真實史事的根本目標。求真與致用相互作用,真理與價值相互促進,使得真理和價值得到內在統一。
(四)宋至明清史學的求真與致用
金石學在宋代逐漸形成,這門學科在清代受到乾嘉考據學派的影響,在歷史領域內方興未艾。金石學以研究青銅器、銘文、石刻碑文等內容,意在考證文字,從而實現史事的求真,繼而證實文字記載的真實性。它的經世致用與清代的乾嘉學派有著密切的聯系,二者相互促進,考據學、金石學、考古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傳承。
明清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學者強調學術的“經世致用”,積極推行儒家經典,大力發展經學,重視考據學,尤其是其中的小學。考據學雖然以漢學、經學為主,乾嘉學派亦側重事實,但很多學者在注重考據的同時也不會忽視宋學的經世致用。
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個基本風氣。[4]雖然考據學重訓詁考訂,但難免不受到宋學中義理、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清代的考據,可以說漢學和宋學交織在一起,共同促進了清代學術的發展。從金石學到乾嘉考證,史學也從求真到兼顧求真與致用,而追求史事真實與現實的價值作用一直貫穿在歷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中。
(五)民國史家的求真與致用
1926年顧頡剛曾說,“薄致用而重求是,這個主義我始終信守。”[5]他一直注重學術研究的求真求實,即使編寫教科書也將這一治學理念貫穿其中。他以嚴謹的學術態度撰寫了本國史教科書,還得到廣泛傳播,并且闡述了一個關于“三皇五帝”是否真實存在的質疑觀點于教科書中,卻在1929年時被人指出有誤導國民之嫌,因此教科書被禁止發行。學術追求與現實需要的糾葛不僅使史家陷入兩難境地,也使得他們的治學宗旨發生了變化。
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民族危機導致顧頡剛從關注求真轉而注重史學的經世致用。他創辦了學會、發行刊物,希望將學術成果普及大眾,還想呼吁更多的青年參與進來。無獨有偶,傅斯年于戰時編寫了《東北史綱》,以期喚醒國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用自己的學問為抗戰奉獻綿薄之力,同時他們也批判那些只重學術而不關注國家變遷之人。
顧頡剛認為抗戰時期不應該丟失對待學術研究的認真態度,而傅斯年則視抗戰為特殊時期,認為政治中的現實需要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6]雖然兩個人對學術追求和時代需要的態度并不一致,但是可以看到他們作為史家自身的學術素養和選擇為國家做出貢獻的擔當。學術研究離不開求真與致用,也離不開真理與價值的統一。在史學領域內,尤其到了國家生死存亡之刻,如果過能夠運用學術的力量影響到國民,促進國民覺醒,那么學術的致用功能就不僅僅是普及教育,還能增強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更好的服務國家。
二、真理與價值同求真致用的關系
作為科學研究的史學,真理與價值的體現仍然在其中非常明顯。真理可以成為衡量史學研究的客觀尺度,追求史事的真實和敘事的真實,考證史料的真實性,彌補歷史內容的殘缺或修正歷史記載的錯誤,豐富史料與史觀,才能促進史學蓬勃發展。對于價值而言,它亦能成為評判史學研究的主觀尺度,學術的進步不只是學術內部能得到進一步的推動,還能使學術的致用功能作用于社會和國家的發展中。無論是內部學術的提升還是外在的影響,對于史學的研究來講,都是一種求真與致用共同發揮其價值的結果。
從歷史學科的角度來看,只追求真實,卻缺少了經世致用,難免無法實現史學的全部價值。而只談論致用,也無益于學術本身的發展。所以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出發,基于社會認知與評價方法,注重真理與價值的內在統一,能夠促進學術研究的繁榮發展,強化史學的求真與致用相統一的理念,也能讓人們更好的認識科學、重視科學研究。
三、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對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意義
從先秦時期史官的獨立地位,到漢唐時期的秉筆直書風骨的延續與傳承,再到兩宋明清之際漢學與宋學相互促進的發展,不論是史官還是學術本身,都沒有離開求真與致用這兩種特質。雖然在嚴峻的民國時期,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響的中國先覺分子開始極其推崇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但在國家危難時刻,知識分子仍然沒有忘懷滿腔的愛國之情,用自身的學問和的擔當肩負起光復中華的使命。他們懷抱大志,雖有遇到學術追求和現實需要之間存在兩難的困境,但在不同程度上依舊將學術的求真作用于現實政治,希望通過一己之力可以奉獻社會與國家。
現代中國的史學發展,還是需要求真與致用的統一,但在此過程中,如何有效促進求真與時代需求的協調,如何真正實現史學的求真與致用的兩全,這都需要現代中國的史家不斷的努力。即便學術與政治存在糾葛,但平衡兩者的關系仍是當今要務,在不妨礙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為現實服務,即不要忘記學術經世致用的功能。而致力于歷史研究的中國學者要堅持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心存這兩種情懷,為學術追求和時代需要奮勇前進。
四、結語
從根本的學術研究來看,史家就是要求真,史學也必須求真。如果一味注重經世致用反而違背了史學的本質,但學術是存在于國家和世界中的,史家亦如此。學者很難理清學術與現實政治的聯系,也始終無法置身事外。從這一點出發,就要關注史學中求真與致用的限度問題,求真離不開實際生活的限制,致用也只能達成它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如何在這限制之中使史學的求真與致用的影響發揮到最大,就需要求真與致用協調統一。
雖然求真與致用一直都是難以兩全的問題,但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重視科學研究的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問題,能夠更好的深入研究史學的求真與致用。調節二者的關系,可以促進史學學術追求和現實需要的統一發展,同時對中國史學的未來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劉家和,《史學的求真與致用問題》,學術目刊,1997年第1期;李帆,《求真與致用的兩全和兩難——以顧頡剛、傅斯年等民國史家的選擇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2]左玉河,《求真與致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雙重品格》,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5期.
[3]教學大綱編寫課題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75.
[4]羅志田.“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J].近代史研究,1998(1):3.
[5]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全集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1:23.
[6]李帆.求真與致用的兩全和兩難——以顧頡剛、傅斯年等民國史家的選擇為例[J].近代史研究,2018(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