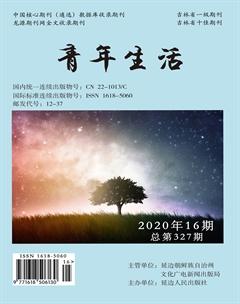徐童獨立紀錄片的創作分析
孫天雨
一、創作主題:徐童眼中的游民與江湖
游民是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的群體,他們出現在中國的各個時期,掩藏在中國真正體制外,影視作品中表達的僅是鳳毛麟角。小人物刻畫著大時代。游民形象在徐童的“游民三部曲”的展現中并沒有因弱而弱,反而展示出了弱勢群體的強——樂觀而頑強的活著。這種生命綻放的美出乎常人,他們的美包括著真實和殘酷。《算命》中“算命神棍”厲百程是,他的乞丐朋友老鄭是,唐小雁也是。
江湖生活不管是在小說還是生活,都擁有一種普遍的共性和理想化的人生追求。總結出來有兩點:第一,是平等的人格。即在江湖,不受制約,平等是游民理想化的人際關系。《算命》的主人公厲百程,身為江湖算命先生,接觸過各式各樣的人。他卑微討好殘疾人聯合會的工作人員,希望能拿到雙份的殘疾人補助。游民渴望的平等和諧在權貴面前被打擊的體無完膚。第二,是大俠風范。金庸的作品能一直被翻拍傳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書中的大俠風范。《算命》中的唐小雁也是生活在江湖中的典型代表,擁有江湖俠義的“老鴇子”,她的豪爽仗義曾讓她經歷輝煌也遭受背叛。干女兒被警察抓進去出賣了唐小雁,唐小雁出獄后還費盡心思救她,脫離了宗族的游民們渴望被愛,沒有血緣關系,卻像兄弟姐妹們一樣在扶持著。既在江湖內,都是苦命人。
二、作品風格:“真實電影”風格受質疑
“真實電影”的來源可以追溯到吉加·維爾托夫在1920年創造的生活即藝術的一種新藝術形式,他開創了一種不征用實際演員,純紀錄性質的敘事類電影。真實并非真相,紀錄片記錄的是真實,攝影機拍到的是真實,但有時它并非是真實背后的真相,只是拍攝者通過鏡頭剪輯盡量還原真實下的時代或個人,對其能夠達到相對一致的情況下,這就是所謂的“真實電影”了。
紀錄片的靈魂是真實性。在我國的獨立紀錄片中,跟蹤拍攝成為了主要的拍攝方法。這類紀錄片沒有演員,不需要刻意布景打光,不干擾被攝者,只要把攝像機處在一個旁觀的位置上,不干涉和影響事件的過程,沒有旁白解說等制作。徐童在采訪時曾提過自己在拍攝《老唐頭》的過程,老唐頭給孫子講家譜的時候這一過程徐童作為一個旁觀者把這場戲用長鏡頭的形式呈現給觀眾。長鏡頭具有不可置疑的真實性,不間斷的記錄事件讓觀眾更能直接確切的感受真實的存在。
拍攝者常會遇到這類情況,為了使得影片更加有真實性,拍攝者無法參與其中。不可否認的是,拍攝者是在不斷地消費著被攝者的生活。《麥收》的主人公牛苗紅曾控訴徐童,因為他沒有告知自己的情況下公映了片子,影響自己及家人的生活。雖然拍攝前徐童征求過主人公的同意,但仍有很多觀眾為牛苗紅表示不公,因為她本想平淡生活,《麥收》卻把她推到了風口浪尖,因其是不合法的性工作者。一部好的作品能被大眾熟知,這是每一個導演在最初拍攝時所期待的。徐童的不足之處是太過真實,把牛紅苗的故事未加粉飾的公放。現實不可能靠著拍攝去搬演,也不可能因為太過真實而剪輯。因為作品內容過于真實,內容與現實的距離也需要拍攝者的精準把控。
三、徐童獨立紀錄片的創作挑戰
徐童的作品基本都在國外參展,在國內也是參加個別的獨立影像展或者高校巡回展出,亦或小眾群體間放映。可以說徐童的受眾大部分是外國觀眾和中國知識分子以及高校學生,他們大部分是社會地位較高的或者是有高學歷的人。雖然中國的觀影人群逐漸多樣化,但也只限制在院線內。提升國民對高水品作品的消費水平和審美素養離不開的是中國電影市場的成熟,要友善地對待獨立紀錄片,首先要給予一定的平臺。
紀錄片拍攝時間較長,并且還需要尊重被拍攝者的意愿,在不斷更新迭代電影市場,紀錄片很不吃香。它對于拍攝時間和金錢成本的支出很大,大部分是電視臺或者大型公司出資,很少有投資人愿意投資這種不賺錢的買賣。徐童拍攝的人文類紀錄片,很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收集素材,但這些素材往往很散碎。《老唐頭》的素材花費了150小時,但最后成片中展示出來的只有86分鐘。低效率、非商業的紀錄片恰恰不在投資人的目標范圍內。所以以徐童為代表地中國獨立紀錄片拍攝者,通過參賽提高知名度,這就可以獲得海外紀錄片投資基金會的資助。中國對大型的紀錄片這幾年的投資越來越多,《我在故宮修文物》、《舌尖上的中國》、《大國崛起》等都是優秀的產物,但獨立紀錄片這一領域還未完全開發,成本因素導致許多獨立紀錄片導演的夢想止步不前。時間、經費等外部因素,讓中國的獨立紀錄片依舊小眾化,在無限的成本藝術創作中繼續走著……
相對于外國電影藝術,中國的電影體制還不健全,更別說獨立紀錄片。因其題材的敏感問題,國內官方對其審查非常嚴格的,并且明令禁止這種挑戰中國禁區和底線問題的紀錄片。獨立紀錄片的特殊題材和獨特表現形式很難通過官方的電影審查,因此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為觀眾所知。在拍攝獨立紀錄片的道路上,有很多像第六代導演張元一樣的人因為拍攝題材敏感被下令禁止從事電影工作的例子,但因為其“獨立”題材的特殊性和高水準的藝術表現能力,依舊讓很多創作者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它呈現出來,它與主流紀錄片在現在的中國紀錄片文化中呈現出一種矛盾現狀。
四、徐童獨立紀錄片的創作機遇
徐童對“游民”和“江湖”的關注,轉變成了專屬于他的系列性質的影片,為他在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市場上留有一席之地。但因為獨立紀錄片從表面上來看使產業化和市場化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沖突的境地,一旦涉及到利益變現,其存在是否合理也變得難以保證了,但不能說為了紀錄片產業文化和市場就要放棄獨立,紀錄片的市場化并不是為了追逐利益回報,而是更需要提供一種創作的多元環境。
在新媒體快速發展下的中國,個人應與官方共同努力從多方面為獨立紀錄片尋找資金和傳播途徑,抱有更加專業的態度去面對目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創作現狀。創作者應在提升創作水平的同時,與受眾和解,以平穩沉和的心態去呈現自己的創作初衷和內容,在這種作者與受眾之間的良性互動中,才會讓獨立紀錄片值得被關注,中國的獨立紀錄片發展才會越來越好。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發展會隨著時間的積淀慢慢走向正規,當其受到中國官方的肯定后,才能更好地對外傳播。立足于中國本土,綻放于世界各地。
參考文獻:
[1] 安麗平.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2009.
[2] 王慶福.不一樣的獨立:內地獨立紀錄片與海外華人獨立紀錄片之比較.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3] 張麗.徐童獨立紀錄片研究.2015.
[4] 王冬冬、劉躍.紀錄片拍攝中記錄者與被拍攝對象共謀關系分析.《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京).2012年5期第93-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