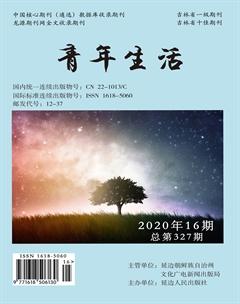近十年《動物兇猛》研究綜述
翟思雨
摘要:因作品中獨特“流氓氣質”備受關注的作家王朔,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中國當代文壇聲名鵲起,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位不可忽視的作家。其中篇小說《動物兇猛》一經發表便大獲好評,憑借其廣大受眾與電影改編的巨大成功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占據重要地位。本文試圖對近十年國內對該書的典型研究成果進行分類,建立起一個相對完整的近十年《動物兇猛》多維文學批評體系。
關鍵詞:王朔;動物兇猛;陽光燦爛的日子
成名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王朔,憑借其戲謔諷刺的語言、有趣獨特的創作風格出道后實現了“爆紅”。其中篇小說《動物兇猛》一經出版便引發了各界關注,其后由姜文根據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上映后更是引發轟動,促使社會各界對該書的關注進一步加深。《動物兇猛》一書具有鮮明的“王朔”風格,小說用“京味兒”十足的語言展現“文革”這一特殊時期中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狀態,數十年來吸引著評論界的關注,近十年對《動物兇猛》小說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三方面:作品的主題研究;中外小說、小說與電影的比較研究和小說中“我”的形象分析。
一、《動物兇猛》的主題研究
《動物兇猛》的主題研究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自其問世至今,研究者對其主題的解讀一般都是圍繞著文化大革命這一小說背景展開。王朔在《動物兇猛》中展現了在“文革”混亂的時代背景之下,青少年失去了父母的管束從而獲得了一種特定時期帶來的“自由”。但是在這種毫無約束的自由世界中,年輕的生命與情思失去規范引導也就容易走向一種徹底的“放縱”,青少年們走向了獸欲的釋放與情欲的滿足。趙軍奇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動物兇猛——讀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1]中就認為小說中的人物是一些在混亂時代中懷有偉大理想的青少年,卻在令人無奈的現實環境中走向了一種無節制的自由困境。
“青春”也是書中重要的敘述主題之一。作者王朔在小說中表達的情感更偏向于對青春的懷念,張芳在《從小說到電影——淺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改編藝術》[2]中分析了小說到電影的改編實現了青春主題由“兇猛”向“燦爛”的表達方式的轉變。“青春”是小說和影視改編中王朔和姜文共有的情感主題。經歷了長期對王朔痞子文學的批判,當前批評界對王朔作品的評價更加客觀,更加關注其戲謔痞氣語言下真摯動人的情感主題表達。
二、《動物兇猛》的比較研究
從中外文學比較這一維度出發,研究者經常將《動物兇猛》與對王朔本人創作風格有著重要影響的塞林格文學作品進行比較。王歡歡、陳璟在《空間理論視域下的〈麥田里的守望者〉與〈動物兇猛〉比較研究》[3]中對兩者開展了空間理論領域的研究,從學校空間、家庭空間與精神空間三個領域對其進行比較,分析表明了兩部小說主人公進行反叛的不同原因與內心共有的美好寄托。除了不同文本之間的比較研究,對于《動物兇猛》與其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之間的比較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電影實現了對小說青春主題的進一步深化。調整后的人物形象和語言表達體現出的個人風格成為了小說改編電影的加分項。同時,作為一部上世紀90年代拍攝的電影,將影片重新放置于當下的文化語境中,一代青年人依舊可以在各式各樣的人物身上發現自己影子,這也是《動物兇猛》這部小說和其改編電影的可貴之處。
三、《動物兇猛》的“我”的形象分析
在《動物兇猛》中,王朔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大院子弟形象,他們桀驁不馴、追求自由,彰顯著無拘無束的原始情感與個性表達。而作品中的“我”作為小說的敘述者則真實地體現出了青少年躁動的青春。在對主人公“我”的研究中,除了通過文本分析展示人物行為,彰顯人物性格與情感之外,還有研究者使用心理學理論深入分析人物的心理狀態與人物行為。安霖、賀曉嵐在《用拉康心理學理論解讀〈動物兇猛〉中的我》[4]中指出,主人公“我”的心理發展歷程契合拉康主體心理結構三個級別的理論。二人實現了理論與文本、心理學與文學相結合的文學研究,這為對《動物兇猛》開展更深層次的多維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同時研究者們也對“我”的主體身份書寫進行了深入研究,通過與“他者”這一文學范疇的比較分析,彰顯了“我”在小說中的不同身份與這些身份的不同作用。張藥滟在《王朔小說〈動物兇猛〉中的主體身份書寫》[5]中指出作家在文本中實現了“自我”與“他者”、“自我”不同身份之間的相互對抗,實現了對文本中“我”這一人物形象的深刻探索,反映出作家對“我”這一主體身份的深刻理解,表達了當時時代背景下人物復雜矛盾的內心特點,這對“我”這一人物形象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四、小結
近十年來研究者們對《動物兇猛》開展了多角度的分析與研究,除了以上提及的三方面,還有研究者致力于對其進行敘事特點方面的研究。值得肯定的是,除了對文本本身進行探討外,研究者還將文本放置于特定的歷史時期開展文化解讀,對其開展心理學等多方面的探索與研究。這種研究趨勢對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重要的開拓意義與價值。
參考文獻:
[1]趙軍奇.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動物兇猛——讀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J].戲劇之家,2015(10):257.
[2]張芳.從小說到電影——淺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改編藝術[J].視聽,2019(10):117-118.
[3]王歡歡,陳璟.空間理論視域下的《麥田里的守望者》與《動物兇猛》比較研究[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7(01):72-79.
[4]安霖,賀曉嵐.用拉康心理學理論解讀《動物兇猛》中的我[J].文學教育(下),2014(04):13-16.
[5]張藥滟.王朔小說《動物兇猛》中的主體身份書寫[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5,35(07):15-16.
[6]史曉丹,靳然.陽光是怎樣燦爛的——談《動物兇猛》的電影改編[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4,26(05):105-108.
[7]湯驍暉.《動物兇猛》個人化書寫的現代性意味[J].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3(05):72-76.
[8]蔣婷婷,楊東.解構崇高——從《動物兇猛》看王朔的反英雄敘事[J].廣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5,8(06):58-61+67.
[9]柴俊秀.《動物兇猛》與《陽光燦爛的日子》之比較[J].文學教育(上),2015(11):47-50.
[10]王朔.動物兇猛[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