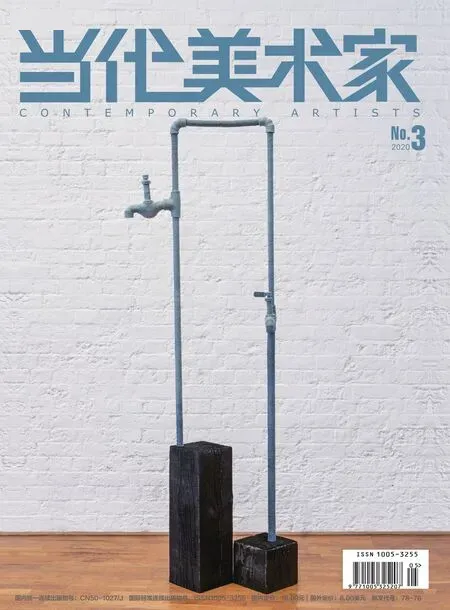變化中的西南行為藝術(2008—2018)
藍慶偉 王婭蕾 Lan Qingwei Wang Yalei

1胡佳藝冰刀行為錄像6分1秒2014
世紀之交是中國行為藝術最為風靡的時期,也是中國藝術市場的蟄伏期,而行為藝術的消弭期同時又是藝術市場的瘋漲期,也是基于這樣的時間關系,行為藝術家們常有句“市場不好行為好”口頭禪,來暗諷行為藝術與藝術市場的絕緣,每每市場低迷,藝術從業者便開始重視和反思藝術的價值。這與行為藝術的本體也不無關系,“在所有的藝術形態中,行為藝術也許是最沒有商業價值的,它的時間性、現場性、偶發性及其以身體作為媒介的特點使它的重復幾乎成為不可能,因而在流通和傳播方面大打折扣,行為藝術似乎也從來沒有追求過它在商業上的可能性。行為藝術對商業性、物質主義、拜金主義的反抗卻不屈不撓。”1而從藝術市場的數據來看,2003至2008年之間,是藝術市場最為火爆的時期。
2007年5月26日,一場集結四川、北京、陜西、湖南、重慶、香港、澳門、臺灣藝術家的行為藝術交流展——“‘八方’蜀京陜湘渝港澳臺行為藝術交流展”在成都K畫廊舉辦。2007年9月12日,成都千高原藝術空間開幕,其首展“回響——成都新視覺藝術文獻展1989—2007”對成都的行為、裝置、影像等活動進行了梳理,同時選擇戴光郁、余極、周斌、陳秋林作為代表進行作品的集中展示。王林在文章《行為藝術與城市化生存——關于“回響:成都新視覺藝術文獻展”》中,通過文章題目為行為藝術在過去發展中的特征總結為“行為藝術與城市化生存”,除此之外王林還梳理了在2007年前成都藝術發展過程中的藝術生態,這個由人構成的藝術生態包括了長期生活在此的行為藝術家、批評家,藝術機構投入者,“一大批藝術家聚集成都,余極、羅子丹、周斌、陳秋林、尹曉峰、劉成英、朱罡、曾循、張華等,還有后來四川音樂學院美術學院的師生,再加上查常平、陳默、張穎川等人的批評投入和陳家剛、鄧鴻等人的場館投入。一時間成都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當代藝術的重鎮。”2高名潞用“街頭前衛”一詞來指稱20世紀90年代成都的前衛藝術,在高名潞看來,成都這座沒有藝術學院支撐的城市有著中國前衛藝術的另類性——反學院、非職業化和市井、街頭等特點。3
千高原藝術空間的首展總結了過去的藝術發展,同時也構成了之后的藝術生態,也是在這一年的1月,成都“K空間”畫廊成立,與了了藝術機構、成都廊橋re-C藝術空間、昆明TCG諾地卡畫廊、苔畫廊等共同為西南的藝術構建了畫廊生態。四川大學美術館、A4畫廊4、藍頂美術館、成都當代美術館、高小華美術館、重慶嶺空間、重慶星匯美術館、原·美術館、108智庫美術館等的成立構建起了美術館生態。非營利空間是西南藝術發展中舉足輕重卻常常被遮蔽的,重慶器·HAUS空間、序空間、喜馬拉雅藝術書店、十方藝術中心是其中的代表。
2008年是中國當代藝術具有轉折性的一年,這樣的轉折作用對中國也不例外,2008年是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年,也恰恰是在這一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在這年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呂澎在《靈魂的冬天》一文中告誡“‘嚴冬’已經來臨”,呂澎同時描述了這一年作為藝術時期轉折點的判斷,“對于那些年輕的藝術家來說,拍賣場上不斷出現的流標消息和藝術市場的驟然蕭條的確讓人心里不安,可是,從1978年以來的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為中國新藝術提供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講,經濟領域出現的危機與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暴露的種種問題很快將成為藝術家的資源,產生出大量更加富于創造性和充滿活力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結束的這個時刻,將很自然地成為一個藝術時期的轉折點。”5在呂澎看來,經濟上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經濟的低潮也往往是藝術創作的最好時間,從呂澎的進一步論述中,我們可以知曉導致今天現實的原因所在,“靈魂的冬天首先意味著缺乏歷史理解力的自以為是。當我們討論藝術的發展,討論藝術市場問題的時候,我們一開始就應該了解導致今天的現實的原因,是什么背景、什么條件、什么資源導致了藝術市場昨天的春天?是那些‘炒作’藝術市場的投機分子在某一天突發奇想,他們在某個黑暗的角落里精心策劃后發動的一次毫無意義的市場游戲,以至于在短短的三年里創造出了‘天價’的短暫奇跡?”6

2王彥鑫當我們再次相遇行為錄像2018
金融的危機的影響并非如太陽雨般東邊下雨西邊晴,而是方方面面并持久的,有幾個特征是顯而易見的,一是經濟的乏力,其影響首當其沖的便是作為社會結構中毛細血管的藝術;二是去中心化,經濟乏力使得如北京這種中心城市的唯一性變為橄欖球般的扁平化,曾經不斷涌入北京的藝術家、資本、展覽等也在不斷地向其他城市轉移,地方性、個體化、邊緣、自組織等成為關鍵詞;三是重資金的藝術展覽、活動的減少,低成本、實驗性的藝術活動得以釋放;四是藝術的自我組織和替代空間的增多,越來越多的藝術家強調自我及自我組織,一種有別于官方美術機構和白盒子空間的探索實驗在不斷增多。當代藝術語境的變化也在悄無聲息地影響著西南行為藝術發展的方方面面,從行為藝術本體到行為藝術生態,這些變化既悄無聲息又轟轟烈烈。
自我組織與替代空間
2005年1月8日,在正杰、木玉明、向衛星、和麗斌、羅菲、林善文發起“江湖”系列實驗藝術展,第一回在昆明實域藝術空間舉辦,熱鬧程度出人預料,以致最后分不清藝術家與觀眾的界限。“江湖”實驗藝術展以一月一次的頻率先后在昆明、麗江、荷蘭阿姆斯特丹、北京、深圳等城市的美術館、畫廊、學校、酒吧、街道、鄉村等不同環境里舉辦了15回共27場展覽,后因資金資助方“麗江工作室”資助項目轉移而終止。“江湖”實驗藝術展不拘泥于展覽場所、參與人群,旨在探索藝術創造的無限可能性,給年輕藝術家帶來了創作的刺激與啟發,信王軍、吳子界是其中突出的藝術家代表。
2008年周斌以項目策劃的身份發起了“驟然的變異:三峽庫區自然、人文生態的藝術考察創作計劃”,這是一次以三峽庫區(重慶萬州、巫山)為考察創作的藝術計劃,活動的資金支持為亞洲藝術網絡,邀請藝術家為蔡青(新加坡)、杰爾姆·明(Jerome Ming,英國)、米迪歐·克魯茲(Mideo Cruz,菲律賓)、拜散·畢連邦常(Paisan Plienbangchang,泰國)、王楚禹(中國)、周斌(中國);重慶501藝術基地作為研討會支持,閆彥與周斌作為研討會策劃;器·HAUS空間作為文獻展支持,倪琨與周斌作為文獻展策劃。三峽因三峽大壩對區域生態的改變成為無數藝術家創作關注的地區,“驟然的變異”藝術計劃在行動的過程中因經歷“5·12汶川地震”而變得更加困難。
2009年3月8日晚“慶典——自由的1/6注解”在成都廊橋當代藝術空間登場,倪琨擔任活動主持和學術批評,共有劉成英、吳承典、周斌、李帶果、李琨、毛竹6位藝術家參與表演,時長90分鐘。表演因6位參與者的不同身份與專業而變得驚喜不斷,充滿實驗性。女音樂人毛竹和李帶果、李琨都是聲音藝術家,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即興演奏了自制樂器、鋼琴、葫蘆絲、薩克斯管、小提琴等樂器。劉成英、吳承典、周斌3位行為藝術家則在過程中分別進行各自的行為表演,劉成英不斷將寫有國名的石頭放入自制的天秤中,而天秤則一直處于不平衡狀態;周斌則像無所事事般穿梭于現場,甚至在睡袋中睡覺;吳承典則在角落品嘗功夫茶并請現場觀眾喝茶,直到最后用假手槍砸碎茶杯。6位藝術家的即興表演糅雜著行為藝術、實驗音樂、現場影像和互動裝置,形式新穎讓觀眾流連忘返,是行為藝術在語言形式上的一次實驗。談起“慶典——自由的1/6注解”的緣起,周斌在訪談《成都行為藝術的一次變臉》中談到受到2008年在泰國看到行為藝術團體“國際黑市”現場作品的啟發,并談到這一作品的核心是“在現場即時發生,并一直處于演變之中”,強調個人直覺和經驗的探索與實踐,倪琨在導語中也談到了這一點:“這是一場即將上演的慶典,這也是一場既有預謀,又充滿未知和自由的慶典。”
“慶典——自由的1/6注解”自2009年3月起,在成都(2019年3月8日)、重慶(2009年5月17日)、長沙(2010年7月26日)、澳門(2010年12月4日)、成都(2011年3月5日)、西安(2011年11月13日)、烏鎮(2012年3月6日)實施了9次,包括中國、德國、北愛爾蘭、日本、西班牙、泰國、以色列、法國、英國、美國的46位藝術家參與,其創作媒介包括行為、聲音、影像、戲劇、現代舞、舞踏和互動裝置。“慶典——自由的1/6注解”與其他的藝術自主組織不同的是,它有著明確的源起、原則、邏輯,它的源起是:“慶典”由藝術家周斌于2009年在成都創立。“慶典”不是一個團隊,而是一種現場創作理念。它的原則有6點,分別是:1.“慶典”沒有主題,反對預設作品方案,追求現場最大限度的不確定性,“即將出現的”永遠是懸念。2.“慶典”讓不同的表現媒介和創作者在現場自由遭遇、互動和偶發。3.“慶典”相信并執行即時的靈感,放棄“做出好作品”的念頭。4.“慶典”鼓勵無所不可地在現場制造混亂,在混亂中尋找可能性。5.“慶典”沒有導演,所有參與者在現場都是自由呈現的個體。6.“慶典”每場創作者6人以上,穿淺色服裝,時間最短60分鐘。它的邏輯是:慶典是一場既有預謀,又充滿未知的現場狂歡;慶典是關于建構的“陰謀”,是對所指的批判性否定;慶典是多種媒介的同場混搭,它們彼此滲透、游移組合;慶典由不確定的碎片組成,充滿觀看盲點和非邏輯敘述。
“頻率:frequency”現場藝術是由吳承典、康書雅(美國)策劃發起的藝術項目,第一回的主題為“強力符號”,于2010年11月8日在成都白夜酒吧舉行,參展藝術家有何利平、康書雅、劉成英、李琨、馬占東、吳承典,參加人員包括行為藝術、聲音藝術、錄像藝術三個領域。關于“頻率:frequency”的定義,康書雅在前言《頻率為根,物質為花》中有一個簡單明了的定義——“頻率”是個多媒介現場藝術的實驗性國際組織。吳承典在前言《旋轉基因》中對“頻率:frequency”現場藝術的意義又做了補充:“探索當下多重背景、多重節奏、多種規律、多重融合的現狀和未來。試圖找到根植于文化交融下本土基因在當代狀況下萌發的可能。”自2010年至2013年持續三年半的時間,“頻率”現場藝術共舉辦了5次活動。而在2016年之后,康書雅用英文寫作的西南行為藝術方面的文章不斷在國外刊物發表。
2008年1月11日,由魏言發起的北村獨立工場成立,并于5月4日舉辦了首次展覽,參展藝術家有魏言、張羽、宋唯、仲磊、薛博文、郭巖、馮德奎、劉風雅、馬海蛟。這次展覽之后,北村獨立工場采取每年按照春秋兩季的形式舉辦“北村獨立工場SOLO季展”,雖然北村獨立工場所在的北村藝術區于2010年1月解散,但“北村獨立工場SOLO季展”一直持續到2012年6月第七次季展。“北村獨立工場SOLO季展”在藝術家的選擇上是跨地域的,這正如魏言所寫《北村獨立工場宣言/非機構自助群體生成宣言》中的兩句:“和而不同,岔道相通!”“過去、將來與我們的此刻共時性地發生著。”北村獨立工場更像是一個泛平臺,在這個平臺上,無數的藝術家在此討論、交流,“北村獨立工場的系列行為實踐實質上是一種弱普遍主義【The Weak Universalism.波里斯·葛羅伊斯(Boris Groys)語】的嘗試。在當代藝術的體制邊緣,以自發和自覺的方式進行著。無論是它每次展覽的主題還是策展機制,都有意無意地回避了一種強勢的符號化沖動(即使引用‘弱普遍主義’這樣的概念也需要異常地小心謹慎),而總是選擇了一種言不盡、欲說還休的低緩、逍遙姿態。”7
在批評家田萌看來,除了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對重慶的藝術環境來說也是一個變化之年,四川美術學院校區遷至大學城,使得生活在四川美術學院老校區所在地黃桷坪的藝術家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危機。這是一種較為復雜的情緒,這當然有著藝術市場的因素,有著四川美院校區搬遷后的冷寂感和無奈。田萌認為除此之外,他們有一種深層的危機感,“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無論是機構邀請的展覽還是藝術家自我組織的展覽從未間斷,可他們卻常常說展覽匱乏。即是說,實際的行為與心理的認知發生了分離,抑或這些實際的行為缺乏某種更強有力的價值支撐。因此,危機感不僅僅是現實生存層面的,更是價值認知與自我再定義層面的。”8
2011年在重慶嶺空間舉行了一系列討論,在之前嶺空間兩次展覽研討會涉及到的“黃桷坪的危機”“藝術的處境”兩個話題基礎上展開,主要包括“肉身的經驗與知識譜系”“外省青年與自我定義”“現代性與烏托邦”,參與者有李一凡、王小箭、張小濤、王海川、田萌、曾宏、沈樺、李勇、彭逸林、天乙、康宇等。在此基礎上,一個更為系統的認知結構與活動框架“黃桷坪的‘浮士德’”形成,包括5個主題:“廢墟的臆想”“子曰”“荷爾蒙時代”“后荷爾蒙時代”“烏托邦”。除此之外,他們以“外省青年”為名開設微博,以“黃桷坪生態”為題開展活動。在李一凡、王海川、楊述、田萌等召集“水土鎮游玩”(又被稱為“藝術訓練營”)之后,藝術家們開始了更為廣泛的藝術實踐,藝術家在沒有批評家、策展人的基礎上完成自我組織,主要活動和作品有:8mg藝術小組《釘子》(2011年8月13日)、沈樺《綠色》(2011年8月22日)、王海川《16.9m2》(2011年8與25日)、文靜《啞》(2011年9與15日)、錢麗麗《窒息的棉被》(2011年10月9日)、馬力蛟《如是我聞》(2011年10月9日)等。
發生在重慶的這一系列活動,我們難以用一個準確的詞匯來概括,是一個夾雜著無限自我的文化現場,是一個在一定時間內的藝術現場,田萌在2018年為《外省青年:從“自我定義”到“文化自治”》一文作的“后記”中再一次就“外省青年”做了概述:“‘外省青年’并不是一個特定的組織,沒有特定的現實目標與利益訴求。‘自我定義’與‘文化自治’只是一種提示,或者說是一種實踐的觀念,而且這些實踐都只能基于個體的自覺而完成,而不是通過一種由某一群人建立一個組織,并由組織去改造其他個體。”9
替代空間、自組織既是21世紀以來西南藝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特點,“靈活、快速、敏感”是它的特征,這與行為藝術有著天然的契合度。替代空間、自我組織在西南的出現并不斷發展有著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第一,優秀藝術家的熱情參與。優秀藝術家身體力行的參與是對青年藝術家最大的鼓勵與支持,同時他們有著資源、視野、經驗、關注度等優勢。第二,有著美術學院教師身份的藝術家的廣泛參與,如楊述、閆彥、曾途,他們分別是器·空間、501-序空間、十方藝術中心的發起人,這樣的空間成為串聯國內外、校內外,國際性交流/駐留、展覽的有機平臺;重要藝術家個展/工作坊;青年藝術家個展/駐留等固定項目,讓無數國外優秀藝術家的展覽在此呈現,這開拓了年輕藝術家的視野;同時這樣的空間也成為扶持青年藝術家的穩定機構,無數在校或畢業的青年藝術家正是在這些機構的伴隨下迅速成長。第三,低成本、持續性,替代空間與自組織與其他藝術機構、藝術展覽相比,對展覽空間沒有特殊的要求,甚至會根據不同的空間展開不同的活動,給發起者或組織者所帶來的壓力較小,這樣的特點同時也在最大程度上對青年藝術家開放。
行為語言的個體化
2008年以來,西南從事行為藝術創作的藝術家沒有固定的人數,活躍于西南的行為藝術家包括但不限于周斌、和麗斌、任前、陳建軍、張羽、幸鑫、何利平、劉偉偉、胡佳藝、王彥鑫、童文敏、普耘、董潔、劉緯、信王軍、時永華、羅菲、楊俊峰、鄧上東、邱文青、常雄、楊輝、黎之陽、尤佳、唐維晨等。他們在行為藝術創作的語言上更加個體化,作品也與20世紀90年代的行為藝術作品有著明顯的不同。“之前的行為有三種方式:一種是以時間的長度來進行創作,一種是以身體的承受力來進行創作,還有一種是反復重復無意義的勞動,這三種方式很經典,也很古典。”10這是何利平在雅昌藝術網訪談中對于過去行為藝術主要創作方式的總結。不僅如此,何利平也回答了未來行為藝術的三個發展方向:“一個是行為藝術精致化,比如在現場拍360度無死角的照片,很精致;其次是走進公共空間,介入社會;第三是跟影像、實驗戲劇和科技等結合,綜合媒體的跨界,再借助身體的方式來進行創作。”11何利平的回答給出了作為行為藝術從業者的一個視角,也是一種被廣泛認同的看法。在回答記者提問會選擇哪個方向時,何利平的回答是走向公共空間——不想做“古典”的作品,他覺得自己沒有那樣的氣質。同樣使用身體作為媒材進行創作,但所表達的方式卻跟以前很不一樣,童文敏的作品則是在不斷探索身體與環境之間的關聯,童文敏的身體不是“身體”,是自然中的一沙一樹,是一種身體的“變色龍”。
何利平被公眾認知始于作品《@41》,這件作品因爭議而被廣泛傳播,2015年何利平再次被廣泛傳播是因為作品《只要心中有沙,哪里都是馬爾代夫》。這件原名為《給我兩平方米,我會把它做成沙灘,然后靜靜地躺在上面思考人生》的作品,是于2015年7月30日下午3點在成都沙灣路光榮北路十字路口一側實施的行為藝術,何利平裸露上身、著沙灘褲、外裹浴巾、肩扛沙袋,穿過人行橫道,在路邊人行馬路將沙鋪成兩個平方米大小,自己手持一杯果汁,斜躺在兩平米的沙灘上,做休閑旅游造型。作品圖片傳至網絡后,瞬間被傳播、模仿,何利平用一張作品照片訴說了這個時代“屌絲”的內心和現實。這樣的創作方式正是何利平所一貫堅持的:“用調侃、詼諧的手法,結合日常、生活化的語言來對這種時代共性不斷演繹,讓更多人產生共鳴。”12何利平堅持自己作為時代的個體文本,通過作品來放大個體文本在時代中的共性。
與大多數行為藝術家所呈現的“什么是行為”不同,何利平常思考“行為藝術不是什么?”換句話說,何利平不斷追問“行為藝術之外的可能性是什么?”一直追問行為藝術模糊邊界的何利平在談到行為藝術時說道:“我從不強調行為藝術家這個身份,說自己是行為藝術家只是覺得別人好理解。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詞來替換,做的作品是不是行為藝術或者是不是在行為藝術的定義里面,這個一點都不重要,它的邊界本來就越來越模糊,沒有必要去強調它。”作品“MC.行為參考”系列便是何利平藝術主張的代表作品。
對陳建軍的熟知來自于其創作于2006—2007年“崗位”系列的行為作品,陳建軍身穿綠色泳褲、軍鞋,手戴白手套保持固定姿勢,在崗臺上為空氣、土地、森林、水靜止“站崗”兩個小時。與慣常的行為作品不同,“崗位”的四個場地都有著不同的地點,分別是成都簇橋家具加工場地(2006年9月16日)、郫縣三道堰(2006年10月28日)、都江堰趙公山(2007年4月16日)、都江堰魚嘴(2007年5月8日)。在“崗位”系列作品的創作自述中,陳建軍對城市體會到了一種混亂迷惘,他反思城市化進程是怎樣的存在?隱藏著什么?同時“以一種儀式化的身體方式,與現場展開關聯,展開自我的情感敘事與對抗,并以此來回應社會。就像生命經驗中直覺的東西,一種理想和恐懼的那種狀態。”13“崗位”系列作品雖然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行為的錄像與圖片,但之于藝術家來講,這個過程更像是一次田野調查或社會實踐,2010 年參與發起藝術項目“昆山在造”,并與從錄像開始的藝術家曹明浩合作;2012 年參與策劃藝術項目“梁山路徑”;2014 年“頂樓之眼”;同時2014 年開啟了“水系計劃”的前期工作。陳建軍和曹明浩將這些藝術工作歸為新的問題意識“平行懸置”14,討論都市消解了城市擴張與鄉村間的沖突。以社會互動、研究性作品的形式展開對隱匿在社會結構深處的歷史、當下、在地等展開創作實踐。陳建軍將始于行為創作的工作方法延伸到了非行為作品的創作,是從“行為”到“行動”的轉變,即從關注人自身向關注在地社會藝術實踐的轉向。
周斌有著旺盛的藝術創作力,梳理周斌的藝術創作方法可以讓我們找到以下關鍵詞“藝術介入空間”“無意義的意義”“身體性”“日常經驗”“場域與互動”“多媒介實驗”,除此之外,近似專題研究式的實驗項目也常常穿插在藝術創作中。在為其撰寫的評論文章中,我將重點放在對藝術家藝術創作中的轉向而非具體的創作方法上,它們分別是從繪畫到行動、從“身體失控”到“思考力失控”以及行動與圖像的共生。“身體失控”是周斌在行為作品創作中常常使用的手段,他通過一些方法對身體或行動進行限制,讓主觀的控制力失效,從而讓行為的過程遠離刻意的表演狀態。例如他會讓螞蟻引領自己的行動路線以將自我——一個原有的行動主體的行蹤交給他者控制;通過單腿站立、張大嘴巴或長時間持續地重復念一個單詞等手段讓身體的生理功能紊亂,而作品的概念和所指就在身體所呈現的真實狀態中得到呼應和呈現。他在創作中恰到好處地使用著自己的身體媒介,既不會刻意傷害,也不會點到即止。2010年,周斌通過設定30天里每天創作一件作品的規則,力求把自己的創作力逼到極限。在這個近似課題研究式的30件作品中,呈現出了自由多樣化的創作手法:即興、偶發、身體性、行動、觀念、互動、場域、日常體驗等方式都有采用。這不同于過去通過某種方法讓身體生理上失控的方式,讓藝術家及其身體更像是一個社會裝置,在日復一日的時間重復及思維創新中,舊的思維與新的創意沖撞,舊的思維模式在失控中更新,時間概念讓身體暫時退場,而“思考力失控”卻始終在場。按照周斌的說法,在執行完這個項目后,“最大的收獲不是作品,而是領會了自己的身心在何種情況下才是最好的創作狀態,那就是首先要保持安靜、規律的日常生活,從而獲得專注的知覺,也才可能有源源不斷的創作力”。周斌的“30天行為計劃”可視之為創作上的第二次轉變:從“身體失控”向“思考力失控”的轉向,同時也充分拉近了身體的直覺體驗和理性思維之間的分離。“吾圄計劃——行動與圖像的共生”項目則被筆者認為是周斌藝術創作的第三次轉向,這個在2015年全年實施的項目采用每月一件獨立作品的形態來討論行為藝術領域“行動”與“圖像”的關系問題。2016年周斌開始了以365天為一個單位進行的“個人改造計劃”,用高強度的持續創作打亂自己固有的創作方法,并讓創作和日常生活強行融合,審思自己過去的藝術工作以及自己和藝術的關系,包括《周斌:365天創作計劃》《閑敲棋子》《寫本書》。
胡佳藝常被人冠以不善言辭、冷酷等詞匯,但作為女性,沒有柔弱的詞匯出現,這與她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力量有著直接的關系。2014年9月,四川美術學院新媒體藝術系“冰刀”展覽的名字是直接取自胡佳藝作品《冰刀》的名稱,策展人尹丹對展覽名稱的概述讓觀眾讀到了對作品《冰刀》及同名群展的解讀,“大概(張)小濤老師希望以‘冰刀’一詞來象征此種精神,明知不易,卻偏要為之。冰刀鋒利,作為展覽名稱或許還有另一種象征,人的精神也許應該像冰刀那樣,穿透冰封,自由馳騁。”《冰刀》既是胡佳藝藝術精神的寫照,也是人生的寫照,畫面中她穿著冰刀鞋在鏡面上滑冰,不斷地滑動、摔倒、重來,直到筋疲力盡,這直接搖晃著每位觀眾情緒的五味雜陳瓶。“看起來不對”曾是胡佳藝個人展覽的題目,也是一種自我警惕的創作態度,是藝術家面對市場、成功學、流行學的必要素養,也是對觀眾慣性思維閱讀作品的提示。
“明知不易,偏要為之”也是胡佳藝的創作精神,但她在創作的方法上處事不驚,《除夕守夜》(2015年2月18日)便是這樣的一件作品。藝術家在自己的出生地——吐魯番葡萄溝水庫——為水庫守夜,從夜色朦朧開始一直到太陽東升結束。關于作品的最大追問是關于意義的討論,以及個體與環境、文化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除夕夜是中國最為傳統的節日,一般要與家人一起團圓,為水庫站崗、為夜晚站崗,恰恰是對世界另一面的關懷。胡佳藝在2017年的英國駐留期間的作品不得不提及,這些作品是關于自己的態度和質感的思考,更像是“囚室創作”,這或許跟駐留期間有著足夠時間的思考有關,藝術家希望哲理的思考有別于之前的作品,不再按照一種預期的模式發展,駐留的空間、自我的身體、公共空間成為胡佳藝創作品的材料,除此之外還有關于大小事的思考紀錄——雖是小小的紙片,或是短短的幾個字,但都充滿著思考的想象。這更像是一種思考日記——沒有兒女情長的創作日記。
王彥鑫2017年前的作品看起來有點笨,是典型的行為藝術創作方法中的身體性創作,強調作品中的痛感,尤其以自己身體的不可控來換取觀眾的心靈痛感。王彥鑫的此類作品通常都是在與觀眾的互動中完成的,有時候像是英雄般引導觀眾的思維,讓觀眾難以分別真實與戲謔,并逐步讓觀眾將戲謔作為真實,加之對身體的介入,使得觀眾主動或被迫主動加入到現場的思考中。來探討觀眾與觀眾、創作者與觀眾、現場與內心之間的矛盾點與細微差異,讓觀者對現場的定義有著新的認知。慣性思維常常會把人導向王彥鑫的自虐,但創作作品與生活并非全然吻合,王彥鑫的態度也是極為明確的:“在用行為藝術創作的過程中,我很開心,每天都可以學習到進行新的東西,有新的靈感,對生活很積極。”王彥鑫從身體出發,不斷探討身體、身體與他者的關系,在這不斷探討的過程中也不斷加入現實關懷與人文關懷,對身體語言的探索和現場的定義有獨特的個人理解,并由此力求向觀眾呈現個人獨有的藝術語言。王彥鑫執著,相信時間積累在藝術創作中的作用,正如他的自我勉勵“喜歡就去做,不停地做,一意孤行,才能另辟蹊徑。”
“身體需要叛變,讓身體顫栗,重新思考可控和不可控下的身體。讓身體介入公共空間與現實與自然發生關系,重新構架身體與空間的關系。讓身體通過互動與觀眾發生關系,重新感知人與人之間的細微變化,書寫自己的身體語言與創作脈絡。”王彥鑫在自述中對身體有著自己明確的見解,2016年開始,王彥鑫的作品產生了一些列的變化,創作了《白塔》《白》《灞柳風雪》《重影》《紅墻》《烏云》《阻擋一小時》《紅毯》《銹刀》《消亡的軌跡》《黑夜想起黎明》《信仰》《藍圖》《歷史的書寫》等一系列在公共空間中的作品,這些作品構織了新的脈絡,這些變化主要圍繞著以下幾個特征展開,首先是語言的放棄,作品中的聲音不再是人為的制造,而是自然而然;其次是空間的變化,從白盒子或建筑空間走向公共空間與自然空間,完成了藝術家從構建自我向解放自我的過渡;第三是從身體的使用向身體的利用的轉換,身體置于環境中,所表達的是作為問題提示存在的身體。同時王彥鑫也在不斷豐富個體身體介入空間的方式,開始用LED冷光燈線勾勒出的身體形象消解傳統的“肉身”形象的探索。王彥鑫追問的是:“當行動剝離了身體本身還剩下什么?”作品《當我們再次相遇》《冷陽》《PP》等便是跨媒介的探索。
注釋:
1.魯虹、孫振華:《異化的肉身:中國行為藝術》,河北美術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06頁。
2.王林:《行為藝術與城市化生存——關于“回響:成都新視覺藝術文獻展”》,《大藝術》2007年第2期,第61頁。
3.高名潞:《“街頭前衛”與“成都敘事”》,《大藝術》2007年第2期,第62頁。
4.2010年更名為A4當代藝術中心,2016年搬遷至新館址,更名為麓湖·A4美術館,并正式注冊為民營非營利美術館。
5.呂澎:《靈魂的冬天》,2008年11月21日。
6.同上。
7.魏言:《非機構自助群體的生成意象》,2012年9月。
8.田萌:《外省青年:從“自我定義”到“文化自治”》,2012年11月27日。
9.同上。
10.訪談《何利平:行為藝術不是什么?》,雅昌藝術網。
11.同上。
12.同上。
13.陳建軍:《“崗位系列”創作自述》。
14.“平行懸置”為陳建軍、曹明浩2014年成都千高原藝術空間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