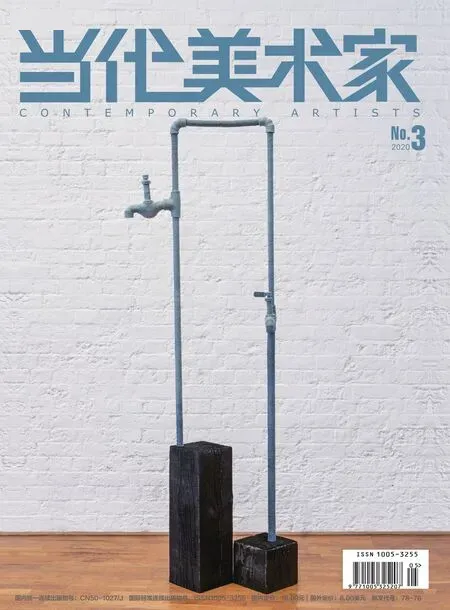材料、媒介與觀念
李松林 李昆績 Li Songlin Li Kunji

1李松林相遇影像裝置冰、木頭、投影儀、影像等2015

2李松林天題-2016攝影作品紙本印刷等2016
李昆績:你從2010年進入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工藝美術系玻璃專業學習,并于2016年考入羅德島設計學院玻璃系。你認為不同院校的側重點有哪些不同。
李松林:雖然我就讀的都是玻璃專業,但是我認為它們的側重點有非常巨大的不同。清華美院工藝美術系的玻璃專業更偏向傳統造像、審美、工藝美術,通過玻璃材料入手,在審美的評價體系內去做一些工藝美術和雕塑。而羅德島的玻璃系建系已有50年,由于歷史發展的原因,最開始也是從玻璃入手,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很快就進入了當代藝術領域,所以研究生教育并不太在意材料本身的使用和工藝的精進,你可以使用任何材料去表達你的任意想法。
李昆績:你以玻璃為媒介進行創作多年,從創作玻璃工藝制品、玻璃雕塑,到以玻璃為元素的行為、裝置、影像等觀念藝術,你怎樣看待“玻璃”這種材料?你的創作發生轉變的契機是什么?
李松林:我對玻璃材料的理解是非常深的。我從2010開始接觸玻璃窯鑄、燈工,后來又澆鑄、冷加工、吹制、霓虹燈,包括各種實驗性的玻璃技巧,基本上都嘗試過了。大概在2013年左右,我當時還在國內參加各種展覽,我發現很多國內的玻璃藝術家嘗試用玻璃這種材料去創作各種各樣不同的東西。我認為玻璃材料有很多美的地方,但是作為一種材料,它依然有局限性,例如易碎、不堅固等。我在思想上產生了轉變,認為一種合理的材料應該用在一個合理的位置。我的追求更多在于思想、觀念、不斷嘗試多元化的屬性方面,而不是對一種材料的精進。我不想把自己單純定義為一個玻璃藝術家,也不愿意把自己定義為某一種單一材料的使用者。
李昆績:你是如何思考中國傳統元素符號在作品中的運用的?
李松林:在大學本科的時候,我比較認同一位歸國學姐的一句話:“中國人做的就是中國風格。”一代代前人并沒有刻意地模仿傳統,他們吸收傳統是自然而然、潛移默化的。我認為我們這代很多的藝術家會被很多的中國傳統所束縛,所以我們年輕的藝術家應該去吸收多元的事物,經由現代的語境,重新將這些進行歸納整理,做出新的創作。
李昆績:你在2015年創作的影像裝置《相遇》和2017年創作的行為藝術《背包行走系列—冰書包(夏)》中都使用了“冰”這種材料,相較于玻璃而言,“冰”給你的創作帶來了哪些可能性?
李松林:其實最開始《相遇》中的“冰”我使用的是玻璃,但我感覺顏色方面效果不夠好,就嘗試換成了冰。那時我對冰的理解就是用來替代玻璃的一種材料,而且成本較低。使用冰進行創作之后,我發現冰的融化是具有時間觀念的,作品從此多了一個時間維度,它不能被永久保存,只能存在一陣子。所以后來我的“行走系列”作品也運用了冰的概念。不過“行走系列”也不僅僅只有“冰”這一種觀念,整個“行走系列”受藝術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s)的影響。我還做了“冬天”“春天”“夏天”系列,在做“夏天”的時候我背著一塊冰,等它全部融化。冰可以被闡釋的概念太多了,我還是堅持“合理的材料應該用在合理的地方”這一理念,才能夠把材料的屬性、概念真正地展現出來。
李昆績:除開藝術家,詩人和導演也都是你的身份,你是怎樣同時以這三種身份自處的?
李松林:在創作上,我主要有這三種身份,我認為這三種身份很有趣。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寫詩,我對詩歌的創作早于繪畫,我是在大學時才開始進行藝術創作的。而導演這個身份是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電影,認為電影就是現代人的造夢,所以我特別想成為一個可以去創作電影的人。到美國之后,我在學校有意識地選修了很多關于電影的課程,有機會去創作影像。我認為這三種身份實際上都是“創作者”,這三者沒什么區別,只不過需要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團隊,根據不同的感覺去進行不同的創作。
李昆績:在川美藝術家駐留計劃期間,你有哪些收獲與啟發?
李松林:在川美駐留計劃期間,我認識了很多很棒的藝術家,跟他們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一起交流很多想法。我認為這對一個藝術家很重要,因為藝術家需要在一個環境中與人溝通,不斷地批評、反思自己目前的思維狀態,去做一些新的、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而且我沒有在國內的藝術圈呆過,回到川美這樣的環境,讓我感受到川渝地區藝術家關心的是什么、感興趣的是什么,他們的生活狀態怎么樣,這對于我思考藝術、生活都會有經驗輔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