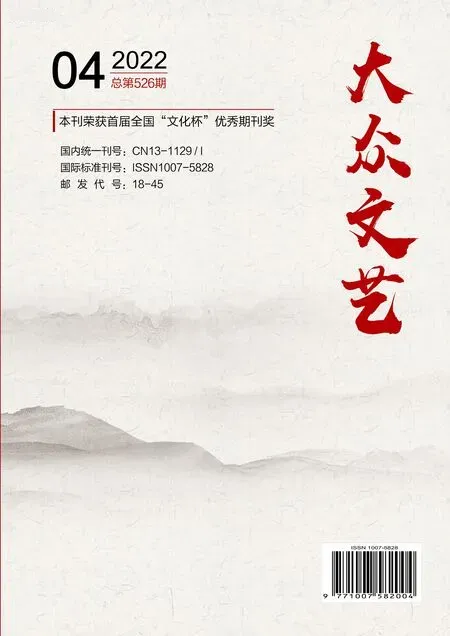郭象《莊子注》中“志”范疇研究
(揚州大學 225002)
《莊子》繼承老子空無、虛靜的理論,創造性討論了至“道”的途徑:只有通過直接訴諸本心的內省直觀之法,保持內心的虛潔清明,才能體悟“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莊子·天地》)的“道”。這種審美活動過程,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心齋坐忘”,即用心去齋戒 。至于如何“心齋”,《達生》中說道:“用志不分”,即要求心志專一。那么,《莊子》所論的“心齋”與“志”之間是怎樣的一種聯系,使得二者可以在價值層面上達到統一呢?筆者從對《莊子注》中“志”的范疇研究出發,進而考察“心齋”與“志”間的關聯,以究郭象“內圣外王”的內涵及旨趣。
一、“志”之釋
在解釋郭象所言“志”之前, 先從語義學的角度對它的用法和含義做整體上的考察, 以便更清楚地把握《莊子注》中“志”的范疇含義。
(一)“志”字義考察
《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葢古文有志無識,小篆乃有識字” 。因古時“識”字的志韻與職韻音韻不分,意義又相通,因此古文作“識”為“志”。則志者,“記也,知也”。如左傳曰:“以志吾過”。《說文解字》謂“志”曰:“志,意也”。《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之所之不能無言,故識從言”。由此可以看出,漢時“志”與“識”已經有明確的區分。現代漢語一般將其理解為志愿、志氣、志趣等,表示心之所向,內于心中的遠而大的打算。總而言之,“志”的普遍意義為人仍未實現的志向、意念或抱負,體現出一種精神追求和價值追求。
從結構來看,“志”分為上“士”下“心”。《大戴禮》說“士”的關鍵詞為“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推斷:“不可易”者即是士人的“志”。儒家重志,“志于人”、“志于道”(《論語·述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無論面對怎樣的艱難險阻,都不能降其志,說的都是主體個人的志向和抱負的重要性。至于這種內在的感性理念如何得以顯現,儒家提出了以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能達到的社會理想狀態為證明。在此意義上,儒家將個人追名逐利的志向自然而然地合理化。
(二)《莊子注》之“志”
據《老莊詞典》統計,“志”字在《莊子》中一共出現22次(不含得志、養志等合成詞)。總的來看, “志”在《莊子注》中的用法和含義包含以下幾種情形:第一,虛指。籠統的志性、心志。例如:“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天地》)、“無拘而志”(《秋水》)、“志乎期費者”(《庚桑楚》)。第二,實指。明確的志向、情志。如:“賢人尚志”《刻意》 、“寥已吾志”(《知北游》)、“徹志之勃”(《庚桑楚》)。第三,通假字,通“誌”。記載,記下。如:“齊諧者志怪者也”(《逍遙游》)、“弟子志之”(《山木》)等。 可以發現,除通假字外,《莊子注》中“志”都是精神層面的價值觀念與取向。
(三)“得志”:功利的取舍之間
《莊子·繕性》云:“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莊子注》解“軒冕”為高官厚祿,郭象認為這些不過是臨時寄托的東西,既是身之外物,便不必為其得失而恣意放縱。與儒家相比,《莊子注》也承認“志”的意向性,但認為“得志”的本質在于出自本然,保持真性,而不是對于外物的瘋狂追逐。這體現出其對主體的價值取向有了更高層面的內在性和專一性的要求。《莊子注》否定“志”的功利價值,指向得是生命的圓滿與生存的自由,代表著個體獨立自由的意志。
二、“心齋”:用志不分,聽之以氣
闡釋“心齋”的意蘊及其在《莊子》中的具體意義指向,需從“心”與“齋”兩字說起。
(一)“心”之釋
《老莊詞典》中有“心”的三類解釋:一是心臟,如“比干剖心”(《莊子·盜跖》),這與《說文解字》解“心”為“在身之中”意義相同;二是心胸,如“中身當心”(《莊子·達生》);三是作為一種思維器官。古人認為心是思想、情感、意志的發出者,但《莊子》中卻要“無聽之以心”(《莊子·人間世》),成玄英疏“心有知覺,猶起攀援”,只有使得心寂,方能淡泊忘懷,進入道的境界。
(二)“齋”之釋
《說文解字》解“齋”為:“齋,戒潔也”。《莊子》則由孔子與顏回的對話引出:“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于聽,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
郭象認為,“一志”即是“去異端而任獨也”。成玄英表示,“異端”的根由在于心只能感受事物的表象,易為外物所迷惑。因此,“齋”并非普通意義上的吃齋念佛,而是要去除由心而生的知覺,泯除由心而起的疑慮與欲念,使得內心潔凈。
(三)“氣凝”而“志一”
在中國古代哲學理念中,氣是空明且能化生萬物的,《莊子》所講的“聽之以氣”的“氣”,可謂“某種心理狀態的比擬說法”。“聽之以氣”僅是修養過程,能夠通過養“氣”來保持空靈明覺的心,才能應待宇宙萬物,與大道相應和。因此,“一志”,是“心齋”的前提,通過“氣”的培養與凝聚,又反過來使得心志虛靜專一,從而達到“心齋”的目的。
三、“心齋一志”以成圣
《莊子注》中“心齋”所要感悟的“道”,是對老子“道”的自然化,是將“道”突破了時空的界限,作為“精神生命之極詣”。而《莊子·繕性》中卻寫道:“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喪言隱,方督是非。儒家認為“志”能夠統領主體的身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心志的展開本質來說是目的為了濟世。但當主體所存在的時空都無道法可言時,個人的理想與志愿也就無法得以實現。莊子借孔子之口來釋“心齋”,想要倡導的是主體面臨“不顯志”之時應對之法——或曰亂世存活保全之法。天下有“道”只是莊子設想中的一種社會理想狀態,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已經無道可循。“世與道交相喪也”,對于莊子而言,在理想與現實的反差面前,剩下的也只有無可奈何的追懷與感嘆了。
《莊子》外篇有一章名為《刻意》,陸德明釋文中解“刻”為“削也”;“意”為“志也”。按《莊子注》之解,刻勵意志只是“人道也”,仍未達到如“托生與民并行而不知其所之”(《莊子·天地》)一般“圣王之道”的境界。通過對《莊子注》中“志”范疇的研究,可以發現,在精神領域凝氣專一,虛靜待物,自然無為,恰是“心齋”活動的審美過程;處于“玄冥之境”的“道”自然是郭象筆下的審美對象;能夠“去離塵埃而返冥極”的圣人之德則是至高審美標準;不囿于名利,不刻意追尋目的,專心一志的“純白者”才是郭象理想中的審美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