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tài)監(jiān)測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在狼瘡性腎炎患者治療全過程中的臨床價值
張 銘, 李文哲, 李瑩瑩, 范明華, 邢廣群
(1.青島大學附屬醫(yī)院 腎病科,山東 青島 266555;2.日照市人民醫(yī)院 腎內(nèi)科,山東 日照 276800)
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種可累及全身多個系統(tǒng)的慢性彌漫性結(jié)締組織病,腎臟是其最常累及的器官[1]。無論SLE的活動期還是緩解期,感染均是導(dǎo)致SLE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3],在臨床工作中早期識別易感狀態(tài)、早期應(yīng)用敏感的抗生素就顯得尤為重要。有研究表明CD4+T淋巴細胞可作為監(jiān)測SLE活動的指標[4-6],但CD4+T淋巴細胞是否可預(yù)測狼瘡性腎炎(lupus nephritis, LN)患者的感染風險及不同臨床階段CD4+T淋巴細胞變化的意義尚不可知。本文從LN患者初診時、誘導(dǎo)治療后和維持治療期3個時間節(jié)點來探討CD4+T淋巴細胞在不同治療節(jié)點不同的臨床價值,為疾病的早期預(yù)防和臨床干預(yù)提供依據(jù)。
1 資料與方法
1.1病例選擇 回顧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青島大學附屬醫(yī)院腎病科收治的初診LN并于初診時、誘導(dǎo)治療后均檢測過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LN患者共38例,其中20例于維持治療期再次完善了第3次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檢測。所有納入的LN患者均符合1997年美國風濕病學院制定的SLE分類和診斷標準,以SLEDAI評分作為評價SLE活動性指標[7],其中SLEDAI評分<5分為疾病穩(wěn)定,5~9分為輕度活動,10~14分為中度活動,≥15分為重度活動。以出院診斷為SLE、LN為納入標準,以出院診斷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腎移植狀態(tài)、妊娠狀態(tài)、合并其他結(jié)締組織病、腎臟疾病、血液系統(tǒng)疾病和惡性腫瘤、既往曾長期應(yīng)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的患者為排除標準。
1.2方法 收集所有患者初診時、誘導(dǎo)治療后和維持治療期的臨床資料,如性別、發(fā)病年齡、隨訪時間、臨床表現(xiàn)、感染部位等基本資料,血清肌酐(SCr)、血清白蛋白(ALB)、紅細胞沉降率(ESR)、C-反應(yīng)蛋白(CRP)、降鈣素原(PCT)、血白細胞計數(shù)、血淋巴細胞計數(shù)及比例、血紅蛋白、血小板計數(shù)、尿紅細胞計數(shù)、尿白細胞計數(shù)、尿管型計數(shù)、24小時尿蛋白定量、補體C3、補體C4、ds-DNA、病原學檢查等實驗室檢查,并通過閱讀病歷和實驗室檢查計算每例患者各時期的SLEDAI評分。運用CKD-EPI公式計算每例患者各時期的估計腎小球濾過率(eGFR)。
1.3感染診斷標準 參照2009年美國衛(wèi)生及公共服務(wù)部、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國家癌癥研究所共同頒布的常見不良反應(yīng)事件評價標準(CTCAE)中感染和傳染性疾病部分來定義感染的發(fā)生,依據(jù)臨床癥狀、體征、實驗室檢查、治療、預(yù)后綜合評價感染的嚴重程度,包括:1級:癥狀輕微,無需抗生素治療;2級:局部治療,需使用抗生素;3級:需靜脈應(yīng)用抗生素、抗病毒或抗真菌藥物或需手術(shù)治療;4級:危及生命,需緊急治療;5級:死亡。僅收錄2級以上的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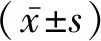
2 結(jié) 果
2.1一般資料 38例LN患者,其中女性31例,男性7例;死亡2例;平均發(fā)病年齡(36.89±17.92)歲;初診時eGFR低于60[ml/(min·1.73 m2)]共有22例,初診時平均eGFR 47.63±31.56[ml/(min·1.73 m2)];初診時平均SLEDAI評分(16.34±4.33)分,重度活動者24例。8例患者完善腎臟穿刺活檢,其中LN-Ⅳ型4例,LN-Ⅴ型2例,LN-Ⅲ+Ⅴ型1例,LN-Ⅱ型1例。
2.2LN患者初診時與誘導(dǎo)治療后臨床指標比較 LN患者初診時外周血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eGFR、ALB、血小板計數(shù)、補體C3和C4均低于誘導(dǎo)治療后,初診時SLEDAI評分、SCr和感染率均顯著高于誘導(dǎo)治療后(P<0.05),見表1。初診時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與SLEDAI評分呈負相關(guān),見圖1。
圖1 SLE患者初診時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與SLEDAI評分的相關(guān)性分析
2.3LN患者維持治療期與誘導(dǎo)治療后臨床資料的比較 在以上38例LN患者中,有20例患者在維持治療期完成了第3次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檢測。LN患者維持治療期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血淋巴細胞計數(shù)、SLEDAI評分低于誘導(dǎo)治療后,維持治療期感染率、補體C3、C4、ALB、CRP高于誘導(dǎo)治療后(P<0.05)。見表2。

表1 LN患者初診時與誘導(dǎo)治療后臨床資料的比較(n=38)

表2 LN患者誘導(dǎo)治療后和維持治療期臨床資料的比較(n=20)
2.4LN患者維持治療期感染事件的發(fā)生及特征 以20例LN患者維持治療期是否發(fā)生感染繪制Kaplan-Meier生存曲線,見圖2。當監(jiān)測時程(誘導(dǎo)治療后至維持治療期的時間)分別為第3、6、12、18個月時感染發(fā)生的例數(shù)和感染率分別為3(15.6%)、9(56.2%)、10(63.5%)、12(81.7%)。其中感染部位以肺部感染最常見(13人次,54.2%),其次是尿路感染(5人次,20.8%)和皮膚感染(5人次,20.8%,其中帶狀皰疹3人次,單純皰疹1人次,蜂窩織炎1人次)。
2.5維持治療階段SLE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進一步根據(jù)LN患者維持治療期是否發(fā)生感染將維持治療期的LN患者分為感染組和非感染組,兩組年齡、ALB、eGFR均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感染組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卻低于非感染組(P<0.05)。感染組激素及其他免疫抑制劑的累積量及監(jiān)測時程均高于非感染組,但差異無明顯統(tǒng)計學意義。見表3。

表3 兩組維持治療階段的臨床資料比較
注:CTX:環(huán)磷酰胺;MMF:嗎替麥考酚酯;FK-506:他克莫司
2.5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預(yù)測LN患者維持治療期感染發(fā)生的效能 以維持治療期LN患者是否發(fā)生感染為狀態(tài)變量,分別以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血淋巴細胞計數(shù)、CRP為檢驗變量繪制ROC曲線,AUC分別為0.833、0.815和0.774,3者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見表4、圖3。

表4 不同臨床指標在LN患者維持治療期預(yù)測感染的ROC曲線分析
圖3 LN維持治療期患者血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淋巴細胞計數(shù)和CRP水平在預(yù)測感染的曲線下面積
3 討 論
SLE是一種累及全身多系統(tǒng)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大量自身抗體的產(chǎn)生是SLE的主要特征。盡管目前對SLE發(fā)病機制、病原學檢查和抗生素的應(yīng)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感染,包括機會性感染仍是導(dǎo)致SLE患者死亡或治療失敗的主要原因[8]。大劑量糖皮質(zhì)激素和免疫抑制劑尤其是環(huán)磷酰胺的應(yīng)用,是導(dǎo)致SLE患者感染的重要危險因素[2, 9]。所以,在臨床工作中,早期識別感染的發(fā)生、早期應(yīng)用敏感抗生素、及時減少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的用量就顯得尤為重要。
SLE的發(fā)病和疾病的進展依賴于CD4+T淋巴細胞[10]。Horwitz等[11]證實經(jīng)CD4+T淋巴細胞特異性抗體處理的小鼠可避免SLE的發(fā)生;HIV感染可降低SLE的活動性[12];SLE患者體內(nèi)CD4+T淋巴細胞的活性增強[13],運用二甲雙胍和2-脫氧-D-葡萄糖抑制CD4+T淋巴細胞的代謝可使SLE的特異性標志物轉(zhuǎn)陰[14]。近年來,更多的研究發(fā)現(xiàn),CD4+T淋巴細胞的變化可能與疾病的活動性相關(guān)[4-6]。本研究中,LN患者初診時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下降,并且與SLEDAI評分呈負相關(guān),與以上研究結(jié)果相一致。推測SLE初診時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下降可能與SLE活動時CD4+T淋巴細胞異常凋亡及針對CD4+T淋巴細胞自身抗體的生成有關(guān),是免疫異常過度激活和免疫失衡的結(jié)果;同時,CD4+T淋巴細胞由外周血向腎小管間質(zhì)的遷移也是導(dǎo)致SLE活動期外周血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下降的原因之一[15-16],但具體機制尚不明確。還有文獻報道SLE患者疾病活動時CD4+T淋巴細胞的減低還可能是SLE患者預(yù)后不良的因素,并與多臟器受累相關(guān)[17]。綜上,LN患者初診時下降的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恰恰是SLE活動的表現(xiàn)。此時不能因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下降而放棄積極應(yīng)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經(jīng)過積極激素和免疫抑制劑的誘導(dǎo)治療后,感染率反而隨之下降。
本研究中,LN患者維持治療期再次出現(xiàn)的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下降,卻與疾病活動無關(guān)。CD4+T淋巴細胞作為T淋巴細胞中的一個亞群,在機體抵御感染過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18],可作為監(jiān)測機體免疫功能的指標。長期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的應(yīng)用,直接或間接抑制機體T、B淋巴細胞[19],導(dǎo)致機體細胞免疫及體液免疫受損。有研究證實,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降低是原發(fā)性腎病綜合征重癥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20-21];在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其感染的發(fā)生率與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的累積劑量相關(guān)[9, 22-23]。本研究中,LN患者在維持治療期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再次下降,評估此時并無疾病活動,感染率卻明顯升高,達70%(14/20)。我們進一步將維持治療期的LN患者分為感染組及非感染組,發(fā)現(xiàn)感染組患者CD4+T淋巴細胞顯著低于非感染組,感染組患者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總量、監(jiān)測時程高于非感染組,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同時,ROC曲線分析發(fā)現(xiàn)CD4+T淋巴細胞可作為預(yù)測LN患者維持治療期感染發(fā)生的指標之一,并且其預(yù)測價值高于血淋巴細胞和CRP,其預(yù)測維持治療期感染發(fā)生的臨界值為276 cell/μl。在本研究中有半數(shù)以上的LN患者在誘導(dǎo)治療后的6個月內(nèi)發(fā)生感染,提示我們在臨床工作中,尤其是在LN患者的誘導(dǎo)治療后的6個月內(nèi),對于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下降的患者,要格外警惕感染的發(fā)生。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雖然本中心診治的SLE患者較多,但符合納入及排除標準的研究人群卻較少;本研究納入的多為重癥LN患者,存在一定的入院率偏倚。這可能會對結(jié)果造成一定影響,后期仍需大樣本臨床研究進一步證實。
綜上所述,LN患者治療全過程中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變化規(guī)律如下:LN初診時,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下降,考慮與SLE的活動,免疫紊亂、免疫失衡有關(guān);經(jīng)誘導(dǎo)治療后,免疫紊亂被糾正,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升高;維持治療期的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下降與免疫抑制有關(guān)。當CD4+T淋巴細胞低于276cell/μl時,尤其是在誘導(dǎo)治療后的半年內(nèi),我們需格外警惕感染的發(fā)生。通過監(jiān)測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了解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在LN治療過程中動態(tài)變化的意義,識別疾病活動及易感狀態(tài),在疾病活動時不要因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的下降而懼怕應(yīng)用免疫抑制治療,而應(yīng)積極合理地應(yīng)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劑,調(diào)節(jié)失衡的自身免疫;在維持治療期,通過監(jiān)測CD4+T淋巴細胞計數(shù),早期識別易感狀態(tài),適當減少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的應(yīng)用,在控制疾病的同時降低感染的發(fā)生率,提高腎臟及患者的遠期生存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