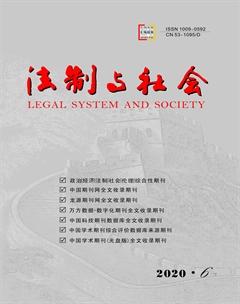試析網絡直播涉黃的定罪問題
關鍵詞 網絡直播 涉黃 黃播 互聯網犯罪
作者簡介:劉冰,廣東國智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研究方向:刑事辯護案件、民刑交叉案件、民商事案件。
中圖分類號:D92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6.261
一、引言
為凈化網絡環境,營造健康、綠色的網絡氛圍,近幾年全國掃黃打非辦開展一系列凈網專項行動,針對電信詐騙及網絡涉黃的嚴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嚴厲打擊。筆者有幸代理了凈網專項行動中的一起網絡直播涉黃案件,而從這起案件中也可以看到,網絡直播涉黃,也就是黃播,可能涉及了幾個罪名:傳播淫穢物品罪、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組織淫穢表演罪。本案的案例如何進行定性?是否是這三個罪名中的一個?除了要研究各罪名的犯罪構成之外,還應當從案件本身入手。
二、案情簡介
2016年,被告A與同案犯合謀以經營網絡直播平臺B的方式牟利。由被告A負責安排運營場所、開發直播APP和組建運營團隊,并與同案犯合謀以“打擦邊球”的方式運營直播平臺B。
2016年X月X日,該網絡直播平臺B,測試后上線進行試運營。觀眾及使用用戶均可以注冊會員制的方式免費進行直播或者是觀看直播,而平臺B的牟利方式是通過觀眾支付給主播的打賞費用參與分成來獲得利益的。平臺B上線后,才幾天時間,用戶及會員就呈現井噴式的增長。期間,被告A聯系了主播中介帶主播來進行大尺度表演。而被告A等人明知該平臺上有大量淫穢表演,仍通過一系列的技術操作,如隱藏房間、選擇性封號等方式,以此來逃避網管監督,另一方面又繼續放任主播在直播平臺B上進行淫穢表演。
該直播平臺運營十天即案發。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本案情節特別嚴重,認定被告A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并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
一審判決后,被告A在上訴期內提出上訴委托筆者擔任其二審辯護人。經辯護,二審法院采納二審辯護人意見,改變本案的定性,認為應定性為組織淫穢表演罪,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的定罪和量刑部分,改為在十年以下量刑。
三、涉及罪名分析
通過對案情的分析,可以鎖定直播涉黃可能觸犯的罪名為: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傳播淫穢物品罪 、組織淫穢表演罪 等三個罪名。
我國刑法規定,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下稱A罪)的最高刑為無期徒刑;傳播淫穢物品罪(下稱B罪)是個輕罪,其最高刑僅為二年有期徒刑;組織淫穢表演罪(下稱C罪)的最高刑為十年有期徒刑。因此,從量刑輕重來說,A罪最重,C罪次之,C罪最輕。但從本案一審判決來看,一審本案定性為A罪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是幾個罪名中量刑最重的罪名。
結合本案案情來看,本案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述一致承認,開發并使用“擦邊球”方式運營該APP直播的目的就是為了牟利,因此,本案是以牟利為目的的,不可能認定為A罪。那么一審認定為A罪的定性是否正確?是否可能構成B罪呢?筆者認為,本案應當定性為B罪組織淫穢表演罪。
四、代理思路
1.從犯罪構成來說,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除了要求要以牟利為目的外,還需要具備傳播行為、淫穢物品,且傳播行為和淫穢物品二者必須具有關聯性,而本案中,二者呈現割裂的狀態。因此本案不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首先,本案中的淫穢物品,指的是經鑒定,存儲于服務器的淫穢視頻。而該服務器并不屬于被告A及同案犯所有,也不非被告A及同案犯所能控制。該服務器為第三方所有。服務器內的視頻是直播時產生,并同步存儲于服務器中。無論是觀眾還是直播者、被告A及同案犯等人均不能復制、回播、下載。那么,就需要弄清楚觀眾觀看的是什么?是直播者的表演?還是直播者表演形成的視頻?
網絡直播具有即時性,觀看行為和表演行為同步發生,表演結束即觀看結束。公訴人認為線下淫穢表演搬到線上,這個傳播行為已經完成。也就是說表演完成即傳播完成。換言之,傳播的是表演,表演并非物品。有直播表演才會產生數據, 進而有存儲發生。如認定為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那么傳播的淫穢物品應當是存儲于服務器的視頻,也就是前述的淫穢視頻。但關鍵是,視頻存儲于服務器之后,觀眾已無法重復觀看或下載、復制,也就是說不具有傳播的可能性。因此,傳播行為和淫穢物品二者割裂,不具有關聯性。
其次,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最基本的條件必須具有淫穢物品。而定位為物品,就必須要有載體,包括有形載體和無形載體。互聯網本身已不同于傳統的雜志、書籍、VCD光盤、錄音帶等有形載體。互聯網本身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但是,雖然無形,但其所傳播的淫穢信息仍需要有視頻文件、音頻文件等電子文件形式作為必須的載體。而網絡直播,傳播的淫穢內容實質上并沒有載體,而是表演行為本身,表演是一種行為,不是物品。不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2.筆者通過檢索案例,也發現各地確實存在兩種判決,一種認定為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另一種認定位組織淫穢表演罪。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主辦的《刑事審判參考》也發布了指導案例認為,雖然是網絡的媒體形式的淫穢表演,其視頻是面對面式,這也是組織淫穢表演的形式。不能因為該方式不是傳統的場地+人員表演的方式,就認為不是組織淫穢表演。時代是發展的,應當從本質上進行認定。
最終二審法院采納了筆者的觀點,判決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被告A犯組織淫穢表演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五、案例評析
本案中,既有牟利的目的性,有傳播行為,同時也形似具備淫穢物品,看似應以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定罪量刑。但筆者仔細研究網絡直播的特性及各要素之間的關聯性后,發現,形似各要素具備,實則各要素之間并沒有關聯關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審據以定罪的淫穢物品是存儲于服務器的視頻,但該批視頻存儲于服務器之后,觀眾已無法重復觀看或下載、復制,也即該批視頻不具有傳播的可能性。因此,傳播行為和淫穢物品二者割裂,導致不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
被告A以牟利為目的,開發并運營直播APP,該平臺的運營費用均由被告A等人提供,可見本案實際上是存在組織行為的。且,主播的淫穢表演和觀眾的觀看同步進行,表演即是在傳播,但傳播的是其淫穢表演,是種行為,并非物品,更非淫穢物品。因此本案應當定性為組織淫穢表演罪。
六、結語和建議
本案直播涉黃案是當年全國掃黃打非辦開展“凈網”專項行動中,首批刑事立案偵查的案件,受到全國上下的廣泛關注。
本案中的被告A本是80后創業者中的佼佼者,他們創建的科技公司作為互聯網行業成功創業的新秀,在案發之前已在互聯網行業取得了一席之地,卻因缺少對法律的敬畏,輕視黃播所帶來的惡劣的社會影響,忽視作為創業者所肩負的社會責任,最后鋃鐺入獄。該直播一共運營了十天,一審判決判處被告A有期徒刑十一年,相當于直播每運營一天,被告A需要付出一年人身自由的代價。在此也想以此案例警醒創業者,無論哪個行業,都應當恪守職業道德、遵守執業紀律,學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
再回到案件本身,一審法院認定本案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且情節特別嚴重,所依據的法律法規是2004年9月最高院和最高檢出具的司法解釋,但該司法解釋至今近十五年。201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了司法解釋二,但是,2010年距今又是近10年。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無論是上述2004年的司法解釋,還是2010年的司法解釋二,其具體規定都沒有跟上互聯網涉黃犯罪的手段更新。因考慮到法律規定的滯后性,在轟動全國的深圳快播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批復,明確了在追究刑事責任時,不應單純考慮淫穢電子信息的數量,還應充分考慮“傳播范圍、違法所得、行為人一貫表現以及淫穢電子信息、傳播對象是否涉及未成年人等情節”。但因為缺乏具體標準,實踐中各法院對此自由裁量的尺度不一,甚至偏為保守。希望最高院能盡快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明確具體量刑標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希望天下無黃。
注釋:
《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傳播淫穢的書刊、影片、音像、圖片或者其他淫穢物品,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規定:“組織進行淫穢表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