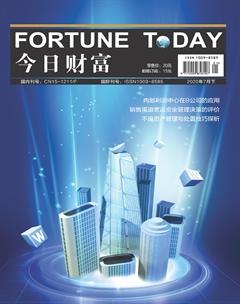影子銀行的監管
范俊斌
影子銀行是金融機構規避監管的行為,并不對應于某類機構或產品。影子銀行遵循金融市場的資金供求規律。對影子銀行的監管應以行為監管為核心,厘清金融主體的行為邊界,承認各類金融機構的平等市場地位,降低交易成本,維護金融市場的信息公開透明,提高市場效率。
一、引言
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已經從2008年初的40萬億元,增長到2019年末的200萬億元,年均增長15.76%,超出同期GDP年均增長率(12.54%)逾3個百分點。充裕的流動性促進了經濟快速增長,卻也蘊含著極大的金融風險。近十幾年來,圍繞防范金融風險、合理控制流動性的爭論很多,其中關于影子銀行的監管是個焦點問題。
二、影子銀行是逃避監管的金融行為
很多觀點認為,券商、信托、基金、P2P等非銀金融機構就是影子銀行,買入返售、委外投資、信托及資管計劃等金融產品也屬于影子銀行。它們逃避監管、攪亂宏觀調控秩序、導致流動性泛濫、加劇經濟危機。隨著監管政策力度加碼,影子銀行的范圍在不斷擴大,自2019年起融資租賃、保理、小貸公司等也被統一納入銀保監會監管范疇,經營杠桿比率被要求不斷壓低,業界把這些類信貸機構也視作影子銀行。金融從業者們的普遍感覺是,“合規性業務”越來越少了,各種“通道”都被卡住了,影子銀行將要消亡了。
筆者認為,影子銀行應該是金融市場必要而有益的補充,而不應成為市場主力,影子銀行應當被限定在“依法規范經營”的范圍內。影子銀行歷史悠久,從未沒落,將來也不會消亡。為說明這一觀點,首先要澄清影子銀行的概念。
爆發于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影響深遠,美聯儲總結次貸危機的原由,提出了“影子銀行”的概念:除接受監管的存款機構外,充當儲蓄轉投資中介的金融機構。根據美聯儲的統計,2007年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資產達20萬億美元,而同期美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僅10萬億美元!在美國金融市場上,影子銀行已不再是“銀行的影子”,他們成為了真正的市場主力!
事實上,券商、基金等各類金融機構,以及資產證券化、信托計劃等金融產品,都已存在、發展了百年之久,商業銀行的歷史則更久遠。一部金融機構的演化史,寫滿了資本為規避監管而不斷創新的故事。在競爭激烈的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如果不規避既定的政策體系和監管邊界,何來創新?沒有持續的創新,就無法獲取超額利潤,企業又如何生存發展?歷經波折的金融機構都早已將規避監管的基因融入血液,差別僅僅在于誰的創新能力更強。因此,影子銀行就是個“新瓶裝舊酒”的概念,它既不是某類金融機構、也不對應于特定的金融產品,它是存在于各類金融機構中的“規避監管的行為”。
三、影子銀行遵循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影子銀行遵循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供求理論。金融市場上,當傳統的金融手段無法實現資金的供求平衡時,影子銀行就應運而生、大行其道。
美國次貸危機前,資金供給端的特征是流動性極度充裕;而在需求端的大量居民因信用等級低而無法通過商業銀行渠道獲得住房貸款,資金供需兩端不能建立平衡。此時次級抵押貸款公司出現了,通過“金融創新”把普通居民的住房貸款打包成證券化產品,出售給投資銀行;投行們繼續加杠桿,把證券化產品包裝成金融衍生品出售給對沖基金、保險公司,資金供需就這樣實現平衡。
2008年之后的中國金融市場,流動性快速膨脹,疊加居民理財的巨大投資需求,急于找到出口;而受政策管控的行業和中小微企業卻得不到資金支持,迫切需要打通融資渠道,資金供需兩端不能建立平衡。此時影子銀行出現,信托公司承接低信用評級或受限行業的融資需求,將企業資產或項目打包成信托產品放到商業銀行代銷,與理財資金對接,資金供需重新達到平衡。中國式的影子銀行的特色是,商業銀行手握流動性、充當資金游戲主角,各方在商業銀行的主導下,扮演不同角色,流動性在杠桿疊加后仍然回流到商業銀行。
上述分析表明,影子銀行的概念不同于某類金融機構或產品,它們只是一種規避監管的金融行為,此種行為在銀行有之、在非銀金融機構亦有之。事實上,商業銀行作為中國金融市場的絕對主力,正是通過非銀行機構渠道,嫁接銀行理財及類信貸產品,提供規避監管的金融服務,使得資金流向投資回報率更高的地方,從而創造出了天量的流動性。
四、影子銀行體系蘊含著風險與失控,應實施有效的行為監管
影子銀行解決資金供需矛盾,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是金融市場的必要補充。但影子銀行的特性是規避監管以獲取高收益,自身蘊含著風險與失控,任由發展必然會加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因此對影子銀行實施有效監管是十分必要的。筆者認為,對影子銀行的監管要從制度監管向行為監管轉變。
很長一段時期,對影子銀行實施監管還主要是針對相關機構及金融產品的政策監管。自2010年以來,監管政策不斷加強,影子銀行的運作模式也不斷迭代,初始版本是:由信托公司包裝信托產品,銀行代銷理財。此時監管層認為該類信托夾層融資投向政策限制行業,屬于影子銀行,需要整頓。于是影子銀行模式升級為2.0版:“信托產品+券商資管計劃+銀行理財”;監管再次喊停后,模式繼續升級:“信托+資管+基金+銀行理財”;繼續被叫停,然后版本再升級:“信托+資管+基金+金融資產交易所+銀行理財”;…… 政策不斷加碼,試圖堵住漏洞,卻最終陷入了監管越嚴格、流動性越泛濫的怪圈。自2009年至2016年的八年間,國內M2的實際增速基本都在15%左右。
可見,以特定金融機構或產品為靶向的影子銀行監管之路走不通。既然規避監管的行為存在于各類金融機構中,那么應對之策就應遵循行為監管的政策邏輯,涵蓋所有金融機構的規避監管行為,而不應僅僅指向非銀金融機構或其開發出某類產品。
行為監管的政策目標應當是結果導向的,就是要看金融行為導致的結果是否符合政策調控預期。逐利是資本的天性,監管層如果站在道德評判者的角度,動輒給機構或產品貼標簽,是不能制定出有效政策的。監管政策應當讓市場參與者充分了解行為邊界,使其在劃定的區間內進行理性選擇和交易。管控資本流動性好比治水,堵不如疏,推動影子銀行朝著政策預期目標去做好金融服務,才是上策。
行為監管的政策舉措不是盯著看金融機構是否充當了通道。通道只是中性的金融媒介,無所謂好壞。資金供求雙方是直接交易還是選擇通道,應交由市場主體去自行判斷。監管者的職責是提高市場信息的公開透明度,金融市場的信息越是公開透明,就越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
五、行為監管政策轉變期的新問題
自2017年以來,決策層確立了金融監管政策向行為監管轉變的路徑,對各類金融機構實施統一監管,開展金融亂象專項治理,取得了明顯的調控效果,流動性泛濫的勢頭得到遏制。自2017年至2019年,中國M2的增速已降至8%左右。
行為監管轉變時期的一些新問題需引起關注:
一是不同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趨同。作為金融市場的核心主體商業銀行,一方面由于利差不斷收窄,盈利能力承壓;另一方面由于經濟增速持續下行,壞賬率居高不下,這些因素迫使銀行風險偏好轉向追求安全,投向集中于央企、上市公司和政府平臺公司等風險相對較低的領域。非銀機構本來是通過承擔較高風險獲取利潤的,但其流動性的主要來源由商業銀行掌握,所以被動地與銀行資金投向保持一致。由于金融市場的風險偏好趨同,原本服務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機構及融資模式全面萎縮,而圍繞央企、平臺、地產和上市公司的融資業務大幅增長。
二是央企已成為脫離金融監管范圍的“新興影子銀行”。近十幾年來,在流動性充裕和金融機構風險偏好趨同的背景下,央企吸納了天量的資金規模。據統計自2015年以來,央企每年的發債規模都在4萬億以上,而總融資余額至少幾十萬億,這個規模已超過央企的實際資金需求,央企成為資金的供給端。聚集在央企產業鏈上的眾多小規模廠商,受金融機構風險偏好趨同的影響,大多面臨政策受歧視、稅費負擔重、經營風險高等問題,融資困難。中小廠商成為資金的需求端。資金供需矛盾突出。按本文邏輯,影子銀行該上場了。但在這個故事中登場的影子銀行卻是央企自身。
央企居于產業鏈的核心地位,掌握上下游廠商的重要經營信息,擁有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優勢。這使得央企可通過向上下游公司輸出資金來獲取超額利潤,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對上下游公司的控制力。央企在這個自我加強的循環中,成為新興的影子銀行。如果不能破除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趨同觀念,現有的全部金融監管政策對于非金融機構的央企來說都是無效的。
六、對影子銀行監管的政策建議
一是要回歸監管政策的初心本源,繼續堅持以行為監管為政策核心,完善制度邊界。當前世界經濟正處于深刻變革的時代,次貸危機影響還未消散,新的全球經濟危機又處在爆發前夜。近十幾年來充裕的流動性促進了社會消費總量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然而深層次矛盾被表面的繁華掩蓋了,天量流動性推高了資產價格(主要是房地產估值),社會消費總量多被固化在虛高的資產估值上,生產效率也主要集中在地產投資領域,一旦金融市場開始不景氣,疊加的債務就如雪崩一般爆發。影子銀行監管的政策初衷就是要抓住金融市場這個牛鼻子,對泛濫的流動性實施管控。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這根弦,到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
要緊盯政策效果,以較為完善的制度邊界為各類金融機構劃定行為界限;承認各類金融機構的差異化風險偏好,推動影子銀行圍繞“完善基礎設施、提升科技創新”等政策預期目標去提供差異化金融服務;要求各類金融機構嚴格會計核算,補充資本和風險撥備,提升償付能力。
二是充分利用5G基礎設施推廣和互聯網科技應用,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加強信息披露,提升金融市場的信息公開透明度,努力降低各項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
三是承認各類金融機構的平等市場地位,統一稅率降低稅負、減少歧視性準入政策。加強社會法制體系建設,補齊金融機構的法律制度短板,改善金融主體的法制環境。(作者單位:天津城投創展租賃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