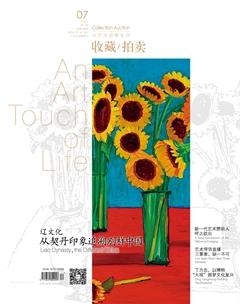撥開迷霧,還原歷史上的契丹
馮翊



髡發左衽的鑌鐵之民
契丹人起源于中國東北的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自古過著游牧生活。驍勇善戰毫無疑問是其民族的一大特性。契丹本意“鑌鐵”,即為很堅硬的鐵。這個鐵血一般的民族曾趁著唐王朝的衰落而迅速崛起,創建了顯赫一時的草原帝國。遼全盛時,疆域東至日本海、黑龍江口,北至外興安嶺、貝加爾湖一帶,西到阿爾泰山,南到山西北部雁門關、河北中部霸縣(今霸州市)一帶與北宋接壤,疆域面積為宋朝的兩倍之多,并能維持相對長久的統治,足見其強大。
現代考古發掘為人們揭開了契丹族形象的神秘面紗,從現存遼代壁畫可窺見一二。壁畫中的契丹人給人最直觀的印象是迎面而來的草原氣息,身材魁梧的男子,或彎弓持劍、或牽馬弄鷹,彪悍的形象躍然而出。作為馬背上的民族,契丹人對馬有著難以言說的鐘愛,他們不僅騎馬馳騁大漠與草原,也同樣熱衷于唐代流行的馬球,追求激烈而驚險的競技快感;他們還給愛駒打造奢華而精美的馬具,盡顯華美與威嚴。那份昂揚自信,將雄渾與豪邁演繹得淋漓盡致。
在形象與服飾上,《契丹國志· 兵馬制度》中這樣記載:“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萬余人,并髡發左衽,竊為契丹之飾。”“髡發左衽”是古人對契丹人總體形象的高度概括,這是馬背上民族的又一鮮明特征。髡發是指將頭頂上的頭發剃掉,保留額頭或兩鬢的頭發。契丹人的髡發是全民族的,男子與兒童髡發的樣式最多,常見的一種是只在額頭上方留一小撮頭發,其余全部剃掉。不少研究認為,髡發可以讓游牧民族避免在乘馬馳逐,披散的頭發容易遮擋視線,故而將其剃去或結辮。
而契丹人左衽的穿衣習慣,與傳統的漢服交領右衽相反,同樣為了便利。因為衣襟左掩能夠較少地影響拉弓射箭的右臂的活動范圍,又能更多地保護右臂不受到傷害,并且方便左手從懷中取放物品,可以騰出右手使用武器。為了在軍事上發揮最大優勢,契丹人以靈活而務實的生活方式應對,鑌鐵之民絕非浪得虛名。
愛美,奢華而時尚地享樂
契丹人不僅善戰,也是一個愛美、同時懂得享樂的民族。近年的考古發掘極大地豐富甚至顛覆了以往人們對遼文化的認知。契丹貴族崇尚奢華,他們打造各種精致的金銀首飾,也廣泛使用珍珠、琥珀、玉佩作為自己的頭飾、項鏈等,以此彰顯自己尊貴的身份。他們甚至死后也不忘打扮自己。
1985年發現于內蒙古的陳國公主墓出土大量奢華無比的隨葬品,各種銀絲網衣、銀鎏金冠、金花銀靴、珍珠琥珀頭飾、琥珀瓔珞以及玉佩等,達3000件之多,讓人嘆為觀止。其中,作為契丹族特有喪葬習俗用來覆面的公主金面具,也被認為契丹人要死后遮丑;另一說是遼朝信奉佛教,時尚女子都愛往臉上涂一層黃色的金粉,美其名曰佛裝。不管是何種說法,契丹人愛美之心,可見一番。
契丹人不僅愛美、追逐時尚,還喜歡波斯、粟特等文明傳來的各種奇珍。可見遼文化不光兼顧中原文化,同時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通過草原絲綢之路與世界接軌。早在上千年,契丹人就使用上了玻璃器。這些晶瑩剔透的美物受到遼朝貴族的追捧。當時,中原還沒有燒制玻璃器的技術,契丹人使用玻璃器都來自中亞和西亞。契丹人他們不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還對外發揮出了極強的文化輻射,讓當時的東歐國家不識中國,只聞契丹,認為中國就叫契丹。
并行不悖的二元特性
善戰又愛美,既能馳騁疆場,又能創造燦爛的物質文明,遼文化這種“雙重人格”與其統治疆域密切相關。遼朝國土橫跨東北高山密林、漠北草原以及華北平原,涵蓋游牧與農耕兩種文明,為此,遼朝統治者創造性地建立起南北兩院制度:南院用儒家的方式來治理漢人,治理的地方主要在華北地區的幽云十六州;北院則以草原文明方式來治理契丹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
因此,遼文化也就表現出明顯的二元特征。一方面,契丹人在與中原漢人的廣泛接觸中,不斷接受其先進文明,如中原傳統的國家治理模式、倫理觀念乃至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習俗;另一方面,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貴族在接受漢文化的同時,不斷融入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如通過創立“春水秋山,冬夏捺缽”的“四時捺缽”制度,刻意保持自己的尚武、善戰的游牧民族特性,避免像南北朝時期鮮卑族那樣的全面漢化。
所以,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文化與契丹傳統游牧文化在遼朝并行不悖。教育上,契丹人一邊熟讀著中原的儒家經典,另一邊又根據契丹語而創造出契丹文字;精神上,契丹人既皈依佛家的普度眾生,又執著地保留著草原原始的圖騰崇拜、薩滿信仰;藝術上,唐宋發達的制瓷業為遼朝瓷器提供了充裕的營養,他們創造出雞冠壺、遼三彩等極具時代特色名品,還有遼朝繪畫、金銀器、玉器、銅鏡等方面均在中國藝術上史上獨樹一幟……
所謂盛極必衰,契丹人也不例外。草原就如同一個巨大的舞臺,游牧民族就是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的表演者。公元12世紀,又一游牧民族金人在東北興起,輝煌一時的遼朝在金人的鐵蹄下很快覆滅,契丹人隨之四散,一部分西遷建立西遼,后融入當地民族,大部分留在中原,并逐漸與金人、漢人通婚,從明代起,便不再見于史書記載。與其說契丹人消失了,倒不如說,他們以及他們所創造的文明早已融入我們的文化血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