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小支流折射時代大河
張瓊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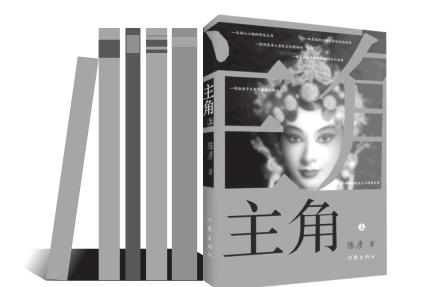
2019年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揭曉,陳彥憑借小說《主角》榮獲該獎。與之前的作品《裝臺》一樣,陳彥選取了自己最為熟悉的戲劇舞臺生活作為小說題材,講述了40年間,一個放羊女娃如何成為一代秦腔名伶的故事。小說中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構筑了一副嬉笑怒罵的世態眾生相。通過人物40年的起廢沉浮,又折射出秦腔在歷史變遷中的興衰際遇。“主角”二字,不單指向女主人公憶秦娥,也指秦腔這門傳統藝術,更指裹挾著混沌和清醒滾滾而來的歷史潮流。
拉雜人生交織下的個人奮斗史
小說主要圍繞憶秦娥長達40年的人生經歷展開敘述。起初她只是一個農村的放羊丫頭,在舅舅安排下進了劇團,開始了一波三折的求學過程。在經歷了舅舅入獄、淪為燒火丫頭、險被強暴等一系列事件后,憶秦娥恰逢老戲解禁,劇團政治生態改組,團里藝名為“存忠、存孝、存仁、存義”的四位老藝人活躍起來,他們看重憶秦娥的努力與天分,不惜傾囊相授,憶秦娥的演技因此大大提高,并以一折《打焦贊》扭轉了局面,順利進入“省秦”劇團。其間憶秦娥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又因懷孕生子和舞臺事故遭遇事業低谷,但她憑借一股不服輸的“癡勁”,獲得了“秦腔皇后”的殊榮。憶秦娥的成長離不開劇團前輩們的幫助,老戲解放這一關鍵時間節點也助推了她的成功。可見“主角”并非靠一己之力可以造就,除了要在背后默默承受各種流言和苦楚,還需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緣際會。
故此這本小說并非完全聚焦于“主角”憶秦娥,也有大量文字圍繞著幾十號人物的生活展開。
陳彥依靠他敏銳的觀察力和長期浸淫在劇團生活的機會,將戲團演員的集體生活、日常習慣等觀眾無法接觸到而又極富真實性的細節在文本中呈現。同時,他也深諳劇團當中人際關系的微妙:同劇團的女演員胡彩香和米蘭為角色而爭風吃醋;劇團黃主任倒行逆施、獨霸專斷,攪得劇團永無安寧;就連劇團伙房這一方寸之地,都繚繞著機心算計……陳彥曾說:
我在這個大劇院生活了幾十年,心里充盈著無盡的故事,行走著數不勝數的鮮活人物,就想把他們寫出來。我覺得他們的故事,是一定能打動人的。
我相信在他塑造人物時,不曾對某一人物寄予特定的愛憎,而只是幾近虔誠地將個人經驗訴諸筆端,這種貼近現實的手法使一個個飽滿鮮活的人物粉墨登場,拼湊成一副拉雜的社會眾生相。陳彥將自己長期以來對幽深復雜的人生體悟融會于這些世相之中:憶秦娥常被人稱為“癡女子”,但恰恰是癡傻不爭的她常被機緣眷顧;楚嘉禾汲汲營營,在事業和生活中都想壓憶秦娥一頭,但處處敗下陣來;配角周玉枝參透其中的奧秘,放下忿忿執念,過好了自己的人生。陳彥在此處傳達的邏輯頗耐人尋味,“爭”與“不爭”,不僅見諸戲劇行業,也是一套適用于人生的處世哲學。
在克盡闕職中守正古老藝術
《主角》刻畫了一批兢兢業業的秦腔藝人,肯定了他們對于傳統文化的守正態度。
我們可以從劇團敲鼓人胡三元身上照見秦腔藝人對藝術的癡迷:他愛惜自己的敲鼓工具,每日將鼓槌打磨得锃光瓦亮;敲鼓人表演時需隱匿在臺后,胡三元并不因此對表演有所懈怠,還在臺后時刻關注觀眾的表情;他因沉溺敲鼓而身陷囹圄,也不忘趁機對著一切可敲打的東西過過手癮。胡三元對那些將鼓敲成“一鍋粥”的人溜須拍馬的行為不屑一顧,堅持以技藝見高低,為人處世上難免有些“不得哥們兒”,再加上沉浸于敲鼓,經常做出些“癡事”。這一人物反映出傳統藝人對于自身從事行當“不瘋魔,不成活”的價值追求,閃現出傳統藝人世世繼承、代代流傳的一脈正氣和風骨。
陳彥刻意在小說前半段弱化了“忠、孝、仁、義”四位老藝人的存在,隨著秦腔老戲解放,四位老藝人才開始在小說中大放異彩。他們具有伯樂般敏銳的觀察力,看重了憶秦娥的吃苦精神和被掩埋的天賦,以戲園老一套“私相授受”的培養方式指導她唱戲;“當練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經沒棍的時候,棍就算被你徹底拿住了”,多年的表演經歷賦予他們一套自己的經驗感悟,并堅持以嚴格標準和挑剔眼光對待藝術;茍存忠因表演“連珠火”而命喪舞臺,彌留之際,他將吹火的秘訣傳授給憶秦娥。秦腔老戲得以綿延,離不開傳統老藝人們嚴謹的守正態度與絲毫不吝的傾囊相授。
秦腔藝術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沉淀,自有一分厚重與底蘊。但是對待藝術不能僅是一板一眼的繼承,在守正中尋求新變,方是秦腔發展的出路。于是,作者通過“秦八娃”這一角色昭示秦腔發展的方向。作為一位秦腔編劇,他可以為了寫作耗盡生命的全部能量,甘居演員身后默默貢獻自己的才華和靈光;他有一雙善于發掘“美”的眼睛,在“不愛紅裝愛武裝”剛剛過去的時代,不憚宣揚追求演員的“色藝俱佳”;他一面堅守著秦腔應保持的傳統表演形式,一面在敏銳的歷史眼光觀照下,賦予劇本前衛的時代精神與內涵。
秦腔老戲,需要有人“迷”,有人“守”,還需要有人賦予其“新”。《主角》中刻畫了形形色色的秦腔藝人,在秦腔的起廢沉浮中,照見了他們對于傳統藝術相同的堅守與忠誠。
秦腔藝術折射時代的開合沉浮
陳彥將戲劇喻為時代的鏡子,在寫作《主角》時,還抱有一定的野心:“力圖想把演戲與圍繞著演戲而生長出來的世俗生活,以及所牽動的社會神經,來一個混沌的裹挾與牽引。”通過這本小說,讀者能從秦腔的興衰沉浮中照見中國40年間的風云變幻。
憶秦娥初入劇團時,胡彩香和米蘭正為劇目《向陽紅》中的赤腳醫生一角爭風吃醋,我們可以推測到當時正處于“文革”時期。革命樣板戲風靡全國,以“三突出”“人物形象高大全”為特點的樣板戲幾乎傾軋了老戲原來的全部地位。在眾聲壓抑的時代,秦腔藝術的守成者,如堅持業務至上的胡三元,因在毛主席去世的日子里敲鼓被定為“白專分子”遭到關押;再如“忠、孝、仁、義”四位老戲藝人被剝奪唱戲權利而淪為劇團的伙管、門房。混沌的時代不僅使秦腔無法以正常形式得到發展,也狠狠拷問著那些文化堅守者們的靈魂。
隨著“四人幫”的粉碎,中國的政治、文化氛圍變得相對寬松。1978年,在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傳統老戲從政治先行的背景下解放出來。憶秦娥借此時機將老戲帶到了貧瘠荒蕪的鄉下、熱鬧繁華的縣城與省城、首都的大劇場,甚至帶上了中南海的舞臺,讓不同階層與年齡的人都接觸到老戲,將他們的審美趣味從過去的單一古板的樣板戲中解放出來,使其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藝術魅力。
到了八九十年代,隨著中國經濟改革走向深入,“資本至上”的拜物教觀點也在一些人心中悄然興起,秦腔成了劇團人口中“要飯賣唱”的手段。小說展示了人們面對這一問題時不同的抉擇:有人堅定地維護民族文化,如憶秦娥、胡三元、秦八娃等;有人甘愿被資本浪潮裹挾,如楚嘉禾、米蘭、龔麗麗等。另外,流行音樂和現代舞曲狂轟濫炸著人們的視聽觀感,觀眾偏向于這種新穎獵奇甚至帶有一點情色意味的舞臺表演形式,秦腔淪為一門“老得掉牙”的藝術,面臨兩種道路:要么做出變革屈意迎合市場的喜好,要么只能任生存空間日漸萎縮。
作為上層建筑,秦腔受社會經濟基礎變化的制約和影響。中國40年風云變遷有如狂風過境、摧枯拉朽,秦腔像被狂風吹動的風車,時而停擺,時而越轉越快。秦腔的未來如何無法被預測,但只要風在,便永不靜止。
小說中的秦腔似乎成為了一位“潛在的主角”,它的興盛衰亡不僅關系著每一個角色的命運,還折射出中國近40年的時代變化,從而使小說呈現強烈的真實性和文史紀的厚重感。《主角》不僅是一時代塵世男女的人事悲歡記,還是一本有關傳統藝術的秦腔談藝錄,更是一部可供借鑒的中國當代社會發展史。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