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牽風記》:向小人物問自然人性
余鍵欣 陜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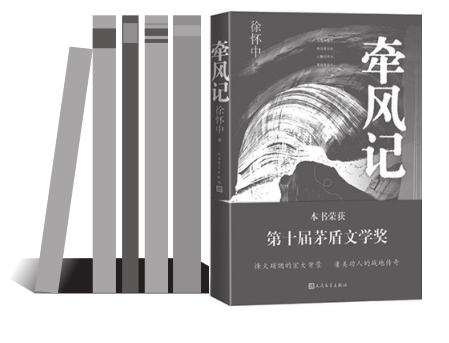
《牽風記》是徐懷忠先生醞釀半個多世紀而寫成的一本戰爭悲劇小說。他返璞歸真、剝繭抽絲,于戰火硝煙中揭示了自然人性,賦予了戰爭小說新的高度與廣度。因此,不同于傳統的戰爭小說,《牽風記》既不是完全的現實主義,也不是完全的浪漫主義,它帶著神啟與玄幻,講述著一個不乏真實也不失浪漫的故事。
然而,“牽風”的浪漫卻是以死為終的:無論是冰清玉潔的汪可渝,至剛至誠的曹水兒,還是文武雙全的齊競,都終究悲情死去。作者以小見大,拋棄了傳統戰爭小說對戰況的濃墨重彩,以三個小人物間美與丑的強烈對照,撞擊出了人性的火花,又以死的悲劇,將藝術推到了頂峰,喚醒了塵封的自然人性,也喚醒了美,織成了一番恢弘的生命氣象。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汪可渝
汪可渝從出場至生命結束都帶著熠熠閃光的女神的特質。抱著古琴而來的她,似乎比這古琴更為古老而純樸。在部隊中,她不諳世事,也不從世俗,逢人便是一句“傻”得令人尷尬的“你好”,即使無一人回應也始終如一。在帶領慰問團趕赴前線的途中,汪可渝堅持選擇繞遠道而行,原因僅僅是不愿從幾具敵人的尸體上方軋過。她似一陣遠古吹來的清風,任人性的丑惡如何蔓延,到她這便瞬間化為空洞,激不起任何的回應與影響。
除此,徐懷忠先生筆下,汪可渝三次“行為藝術”般的裸體更以一種特別的浪漫,淋漓盡致地高歌了純粹的自然天性。野戰軍結束整訓后,汪可渝脫光了被雨水浸透的衣服,一絲不掛地安睡在門洞里。第二天睡過頭的她在被沉迷于人體藝術的齊競拍下后,不但沒有因羞愧而大發雷霆,反倒不以為意地回以齊競一聲再熟悉不過的“你好”。或許她不諳藝術,但卻安于天然。第二次是在北返渡河中,為了保證婦女們的安全,她身先士卒,脫光了身上的衣服,泰然自若地站在船頭,于是,一個、兩個……一百多個婦女都脫光了衣服,白花花地一片,圍坐在船上。她們由一開始的羞澀、拘謹,慢慢地變得大方,自如。她們談論起了乳房之美,談論起了原始記憶……這場景,仿佛一下回到了遠古時期,生命沒有了《十字街頭》里那所謂的壓倒式的“習俗”的約束,人人都遵循著自然,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最后一次“裸體”是臨死前的汪可渝。預感到死亡的她開始清洗身體內外,從粒米不進,大量地飲用山泉水,再到臨死前脫光衣服,卸掉夾板,用泉水將整個身體擦拭干凈,連指甲縫都不放過。她力圖將身體里每一寸無關自然的物質剔除,留下最純凈也最純粹的自己。幾月之后,在戰馬“灘棗”的努力下,汪可渝的不腐之尸被直立地放置在一棵千年銀杏樹樹洞里。她一條腿略作彎曲,取的是欲邁步前行的姿態。她順著無限生命的銀杏,向著無限自然的時空繼續遠行。如此,死不再是簡單的生命的消逝,死更像是自然的深化與延續。這般奇詭的想象,似乎有些難以理解,但越是反復咀嚼,越能領悟到女神汪可渝身上源源不斷的神圣而至上的自然與美。它們超越了戰爭,也超越了生命。
孤獨之魂,凈化之美——曹水兒
通訊員騎兵曹水兒是徐懷忠先生筆下一位典型的圓形人物,他虛榮而好色,在行軍路上留下了許多風流韻事。盡管如此,他所堅守的真與美又是多數人自愧弗如的。放浪形骸的他,在面對美麗動人的少女汪可渝時,卻偏偏始終保持了那份尊重與珍愛。他避開了所有可以與之接觸的機會,像一位紳士一般保護著她,愛惜著她。在和齊競一起初次見到汪可渝的裸體時,反倒是曹水兒成了提醒齊競不要靠近的人。可見,他對美保持著一種天然的敬意與向往。此外,他并不在意他人的目光,只是在人群里追尋著美,也踐行著真,直至面對俗世的槍口。這讓我想起了安托萬·德·圣—埃克蘇佩里《小王子》中的一段話:
“人都在什么地方?”小王子終于又開了腔,“在沙漠上,還真有點孤獨……”
“在人群中也一樣孤獨。”蛇說。
曹水兒便是那個年代里孤獨的靈魂,粗鄙之下竟是真與美。其實,真假美丑,若是浮于皮相,恐怕只得個霧里看花的果。唯有掙脫人類自我鑄造的堅牢,回歸天然,回歸生命,一切方能“撥云見日”。
比起汪可渝之死,曹水兒的死更讓人痛心。好色的弱點終究使他自食惡果。一場被人精心策劃的桃色風波將他推向了風口浪尖。然而,當齊競告訴他公審大會上不得喧鬧等事宜時,他卻用輕松的口吻回答:“首長放心,我肯定配合就是啦。”于曹水兒而言,生死,就像是孩提時不假思索的承諾,那般干脆;性命,也只是一個輕飄飄的,無關痛癢的位置。槍聲響了,一個排槍急射過來,第二個,第三個……其實,一顆子彈便可以了結的事,作者竟安排得如此驚心動魄。也許正是這般玄幻而富有浪漫的死,方能讓人于心底原諒他的一切,也銘記他的一切——污穢已然被抹去,但美與真卻永遠銘刻在心。
美的假面,靈魂的自贖——齊競
美丑交撞最為激烈的便是齊競了。作為一名留學歸來的解放軍將領,在藝術與能力上,齊競是當之無愧的美的代表。然而,在他真誠美好的外表下,掩藏的卻是一副虛偽的丑面。齊競醉心于人體藝術,面對少女汪可渝自然行狀下的裸體時,他不但不回避,反倒大步流星,并取出相機趁機拍了起來。如此行為,權當是對自然藝術的陶醉與尊敬。然而,當汪可渝被虜后回歸部隊時,他最關心的竟是汪可渝是否還是處子之身,就像汪可渝所說:“實際上你內心想的是,從八里畈交換回來的這個汪可渝,要么是一個完好的女人,要么是一具女尸。”前后行為強烈的對比,使他藝術的假面被撕得粉碎。此外,因為拍照事件,汪可渝不得不被調離九旅,無辜而又充滿抱負的青年才女當然不甘就此離開。而此時,一向大義凜然的齊競竟選擇了逃避,反倒是曹水兒設法將她留了下來。于齊競而言,曹水兒更像是一面明鏡,低調而不動聲色地照出了齊競不自知的假面,又如一江春水,時刻在齊競的內心激蕩,一點點腐蝕著他的虛偽的真誠與自然。
齊競之死,雖已是蹣跚之年,但在遠遠望見汪可渝站立的尸體的那一刻,他已全然崩潰。初春的陽光透過金黃的銀杏樹葉,稀稀疏疏地灑落在汪可渝天然的肉體上,生命雖已停止幾月之久,但汪可渝骨子里透出的生命氣象卻像她彈奏的空弦音那般向遠處無限延申。此刻,真與假、美與丑在他的血液里瘋狂激蕩。懊悔與羞愧,惶恐與心虛,使他無法上前,他明白,他只能和鷹鷲、爬蟲一樣在汪可渝尸體外繞行。戰爭最終在艱難的炮火中勝利了,而齊競的心卻狠狠地受挫了。他將用一生來懺悔,懺悔所為,也懺悔靈魂。
《牽風記》與其說是戰爭小說,卻更像一部書寫人性、構建美好的抒情長詩。它以直寫讓我們看到了美,又以對比震撼了我們的靈魂。如果說汪可渝是至境的美,那么曹水兒是摻著雜質的美,而齊競則是虛偽自欺的美。他們在對比中仙化、凈化,又在對比中燦爛殆盡,共同構建了自然的人性美。
歷史總是藏在微不足道的細枝末節里,無須刻意潑墨。戰爭已去,人性永恒,自然、真誠與美終將遠遠超越一切丑惡,高懸在人性的頂端。
(作者簡介:余鍵欣,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17級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陜慶,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講師,清華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