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物兄》:不迎合讀者的儒學世界
鄧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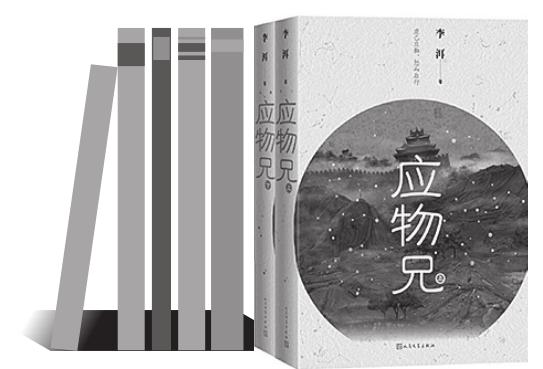
在2019年茅盾文學獎的五部作品中,《應物兄》的風格最為特殊。它承繼了世情小說的傳統,卻不迎合讀者口味。這部備忘錄兼沉思錄式的作品,是中生代知識分子對兩個基本問題的回答:怎樣做人、如何做事。李洱將載道的技術打磨得極精細,建構了一個“看不見”的儒學世界。他沒有冬烘地說教,而是創造了一場自由的拼圖游戲,等待讀者拼湊出自己的闡述。
這本書的故事主線是程濟世、應物等學者籌建太和儒學研究院的始末,而故事卻不是通過連貫情節推進的,看似雞毛蒜皮的人際關系、嘰嘰喳喳的對話才是編織起的敘事網絡。應對敘事網絡的改變,語言風格也有一些調整,要讓商政學界背景迥異的角色溝通,只能用淺白平實的口語。這本書語言生活化,甚至初讀時還會感覺文字未加雕琢,作者有意用形式上的“俗”包裹艱澀的“道”。若想進入《應物兄》的世界,就需調動智性細品人物對話。中國小說傳統,向來偏愛感情濃郁、情節曲折的作品,而幾乎沒有靜默沉思。情感與理智并無高下,但對于在漢語文學世界中成長起來讀者來說,閱讀此書時,要摒去自己預設的情感立場并非易事。
“觚不觚,觚哉!觚哉!”是書中最沉痛的喟嘆。李洱說:“對這個時代的寫作者來說,沒有常識。”對于抱著舊常識的有識之士來說,窗外事常令他們不解。舊秩序舊道德的斷裂,我們正身處時代的縫隙,因此“道”也正隨之變動。恰如程濟世在七十二講堂所說的那樣:
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人,不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人,也不是儒家意義上的傳統中國人。孔子此時站在你面前,你也認不出他。傳統一直在變化,每個變化都是一次斷裂,都是一次暫時的終結。傳統的變化、斷裂,如同詩歌的換韻……每個中國人,都處于這種斷裂和連續的歷史韻律之中。
我們身處萬古江河干涸的河床里,正因為身處時間的縫隙,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精神惶惶,急于尋找道與儒學世界,而二者皆因斷裂無跡可尋,進一步加劇了人物情緒的焦灼。這種尋覓無果也是李洱有意為之。一方面,“道”在中國哲學體系中是變動的,因此它必然不能直接被說出;另一方面是寫作技術的考慮,作者刻意將“道”隱去,隱言他對舊式書齋凋敝的哀嘆。小說中的幾代學人形象中,最老一輩學者邁入生命尾聲,恰是“一代人正在撤離現場”。李洱對于老一輩學者,比如雙林院士、蕓娘、程濟世和何為先生學術世界的敘述流暢明麗,全然不同于描寫當下世界混亂繁雜的筆調。但形而上的崇高書齋,最終敵不過現代秩序的侵襲,程家大院在最后一曲灰蒙蒙世界真迷茫的挽歌中畫上句號。中生代學人有過玫瑰色時光,李洱對八九十年代應物、象愚和喬珊珊大學生活的描寫相當可愛,但如今他們的學術世界與媒體、商政界糾葛,早已不再有過去獨立自主的地位。鸚鵡和驢的人格,是中生代學人面對公共空間無力感的隱喻,分別代表學舌與技窮。在朗月廣播臺言不由衷的應物,借用抽簽決定辯論立場的比喻,說出了中生代學者的尷尬境遇。
儒學世界也非無跡可尋,恰因為“道”之形而上,造就了它應物化形的靈活。《應物兄》的一物一言中皆有道跡。在日常飲食中,道巧妙地附身顯形,“仁德丸子”,這道清淡的濟州菜,是對儒學世界終極問題的回答。仁德丸子的“仁”與“德”是儒家道德哲學的核心,而這本書中的仁德丸子正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代言,這道菜在程濟世的言說中被反復提及,不同于他偏執的濟哥蟈蟈,仁德丸子是日常和精致、實用和審美的統一。將看不見的儒學世界放在仁德丸子中,恰恰是讓儒學世界顯形的最聰明辦法。
這本書中,敘事的視角常有變化,但讀者在這些連綿不絕的聲音背后,也能隱約感受到那個始終存在的儒學世界。小說人物的立場背景不同,且都隨著文本變化著。《應物兄》的生活多元復雜,在生命難以抉擇的時刻,所有人都會對“道”產生懷疑。一些角色看似無恥,但剛要咬牙切齒,下一秒的情節,就要使讀者同情他,而再過一會兒甚至要為他哭、為他笑了。前省長梁招塵在位時做過不少荒謬之事,被雙規后,他想在慈恩寺出家,卻在一個陰雨綿綿的冬天,被寺廟的一紙告示打發回家。路人指認出從廟中走出的前省長,梁招塵說:“我不是他,他不是我。”爾后衰老的身影消失雨中。這條典型的“儒—釋”路徑能夠勾連起的文化回憶數不勝數,因此我們不再單向度地品評梁的行為。另外,偷兒也是一個符號性的角色,他先后擁有三重身份,且這三重身份斷裂了。從清華大學畢業生,到小偷,再到中層公務員,他的社會身份不停異動。偷兒在書中50多歲,有心的讀者回溯歷史便可將偷兒的經歷猜個大概。書中有一段偷兒和程濟世的對話:
那天的談話,就是從偷盜開始的。程先生說:“魯國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答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這話是什么意思?”……偷兒說,他也是這么想的。如果有錢人不貪圖財利,將財富搜刮一空,那么即使獎勵偷竊,也不會有人偷盜。偷兒不愧是清華大學出來的。
雖然對于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來說,儒學世界是始終飄渺著的無形物,但對應物兄來說,儒學世界卻是確定的、始終能在現實世界找到形狀的,黃河轉彎處的內心獨白,正是形而上在他心中形成的確定性。九曲一章,李洱鋪開大段排比,不避詞藻幼稚堆砌的嫌疑,用力書寫應物兄眼見黃河的激動獨白:
這是黃河,它從莽莽昆侖走來,從斑斕的《山海經》神話中走來,它穿過《詩經》的十五國風,向大海奔去……這是黃河,它比所有的時間都悠久,比所有的空間都寥闊。
當儒學世界進入公共空間,常以蒼白老朽的表象示人,而應物卻用語言修行自己,在說話與沉默間,敞開自己,以創造鮮活當下的儒學世界。他曾這樣回答陸空谷:
每一個對時代做出思考的人,都會與孔子相遇……孔子把自我身心的修行,看成是一個不會終結的過程。它敞開著。孔子反對怪力亂神,他不相信奇跡,不依賴神靈。這說明他是一個有尊嚴的人,同時他又很謙卑。他的道德理想是在一個日常的、變動的社會中徐徐展開的,所以孔子是一個做實事的人,辦學,教書。他誰都教,有教無類。他不是一個凌虛蹈空的人。所以,我首先是對孔子感興趣。我沒有辦法不感興趣。你對他不也挺感興趣的嗎?
儒學世界是我們腳下的路與心中的道德律令,但我們必須承認,并不存在完美的思想體系。對儒學的反思從五四開始就沒有停歇,“打倒孔家店”的矯枉過正聲仍在回響,而新儒學界也時有令人大跌眼鏡的言論。但不確定性不應該帶來恐慌,“你給我一個思想,我給你一個思想,我們每個人就有了兩個思想”。李洱記錄的思想,加上讀者的思想,就擁有了一江活活思源。太和春暖,對于尚沒有答案的問題,我選擇保持樂觀。《應物兄》隨時在更新,永遠未完成。身處當下,李洱不愿做預言明天的神棍,可小說需要結局,而要終結一段思考,只能讓應物在車禍中死亡。應物的觀察被掐斷,留下一部八十萬字的小說。
現在是午后,一切都在幽微的光線中變動,在這顆尚未成型的晶體中,應物兄,或者該叫他李洱兄,抬抬他狡黠的皺紋,大概要對我們說:“它的不確定性,就是它的確定性。”
(作者系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17級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