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的楊林柯
本刊記者_高洪云 供圖_楊林柯

楊林柯,祖籍陜西扶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農村教育培訓中心特聘教授,中華教育改進社社員,陜西省經濟發展“十年十人”教育影響力致敬人物,《教師月刊》“年度教師”,《當代教育家》《教師博覽》專欄作者,入選《中國教育報》2014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為陜西師范大學附中資深語文教師
“一語成讖”
2017年11月12日,周日,湖南省沅江市某中學,高三年級結束了一天的考試。按這所封閉式管理學校的規定,學生當天下午放假。但在高三1502班,班主任鮑某臨時布置了作業:觀看一個16分鐘的勵志視頻,寫不少于500字的觀后感。16歲的尖子生羅某想出校,班主任堅持先完成作業,遂發生爭吵。羅某掏出彈簧刀,連捅26刀刺殺了老師。
也就在案發前,西安,楊林柯剛在陜西師范大學參加完一輪研究生論文答辯。
結束后,老師們閑聊。談到拒絕其中一名學生通過答辯,一位副教授不由對楊林柯等參評老師感嘆:“你們演紅臉,我演白臉。”參評老師開玩笑:“嚴師出高徒啊!”楊林柯則半開玩笑:“嚴師也可能出暴徒!”
沒想到一語成讖,兩小時后應驗在了千里之外的湖南。
一連幾天,楊林柯感到震驚、惶恐,甚至還有一絲恥辱,五味雜陳。
近年來,校園欺凌、師生沖突、青少年自殺、殺人等事件屢見報端。很多人甚至已麻木于分析原因,但每當悲劇發生,受沖擊最大的,除了當事家庭,還是普通的教師群體。

要致富,賣教輔,已成為書店行業心照不宣的口頭禪。據說,十萬成本開店,可年賺二十萬
但看完幾篇血案的評論文章,楊林柯依然被留言嚇了一大跳:很多人一面倒地指責學生。
本能地,他感到憤怒:老師怎么能不檢討自身呢?隨后連寫兩篇文章——《教師為什么會如此受傷》《師說:在救孩子之前請先救出自己》。
對這起互害式悲劇,楊林柯認為,不能僅僅指責學生,或把矛頭指向制度,盡管死者為大,但仍要討論遇害老師的責任。
在他看來,教育無論如何改革,都一定有個不可逾越的底線:那就是師生之間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好的教育離不開愛與自由,鮑老師的嚴管,聲稱通知家長談話,及“不愿寫就轉班”等“不當言行”,是否也是激怒愛徒的導火索?
從教多年,楊林柯不知見過多少被應試教育生態扭曲的心靈。不論是對別人的暴力,還是對自己的暴力,早在暴力之前,就已埋下種子。
如果說,自殺和殺人的悲劇還只是極端現象,他看得更多的,還是日常教學和生活里的“茫然和脆弱”。
他一位朋友的孩子,中考是西安未央區第十,因成績問題,高中三年分了三次班,高一在實驗班,高二被轉入普通班。有一次,班主任以成績退步為由,勒令他當著全班同學面念檢討。后又因“早戀”問題,約談時雙方惡語相向,老師打了學生一巴掌。從此,學生日益厭學,高考前一個月,每天躲家里睡覺。
雖然這位學生最終以超強的應試能力升入了985高校,但到了大學卻一蹶不振。楊林柯說,如果不是后來老師和家長的極力疏導,這個學生還不知后果會如何(按:該生目前正申請去國外留學,四個月復習,雅思考試7分,學習能力很強)。
超級學校模式、嚴酷的分班制、教學的粗暴,師生的委屈乃至戾氣,最終導向的,早已不是應試和素質之爭、教育公平之爭,而是教育常識的丟失、生命教育的失落。彌漫社會各個年齡段的抑郁癥、大學生“空心病”、精致的利己主義,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精神疾病問題。
在新書《與教育拔河》中,楊林柯依然反復質問著:教育除了為GDP增加數字、選拔人才和承擔職業分流器的作用之外,還應該為孩子的生命增加些什么呢?
教育爭論早已超出教育之外。正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劉云杉教授指出,“既有底層的平等訴求,也有中間階層經營、投資的策略,還有隱秘的財富階層對繼承人的傳承和庇護。教育最終變成了一種賭博,成為各種力量的博弈。”(參見界面新聞《專訪北大教育學院劉云杉:今天的教育已經變成了賭場》,2019年7月)
而所有教育之外的焦慮和壓力,層層傳遞,最終落在學生身上。
兩個楊林柯
今天的楊林柯,被很多人視為“異類”。而對他自己,卻是一段非常漫長的“自我啟蒙”。
三十年前,年輕的楊林柯,可謂與世浮沉。1988年自陜西師范大學畢業后,楊林柯教了四年初中,最大的愛好是下棋。
九十年代轉教高中,時代仿佛一下子變了,“下海潮”彌漫整個社會,他也開始跟著打麻將。為了賺錢,還編了不少如今被他視為“爛書”的教輔及文化普及讀物。
他清楚記得,第一本書是1990年11月出版的《天方夜譚新編》,伴著隔壁的麻將聲,他每天晚上下班后堅持寫3000字,約半年寫完,印了45000本。彼時他當班主任,月薪才幾十塊。扣稅后,這部書稿掙了3800元。三四沓10元的“大票子”到手,他竟懷疑是不是真的。
教輔市場悄然崛起,楊林柯發現,這種“垃圾書”竟比文化讀物還賺錢。他用了一個月的暑假,剪刀、糨糊加一支筆,整理出一本復習資料,凈賺7500元。書稿累積,僅1996年就出了6本教輔及文化普及書。有一人編輯,也有合編,掙了近2萬。他還因此被批評不專心教學。
三十歲的楊林柯,沒有過“而立”的想法,更沒想過所謂“不惑”。
現在回頭看,楊林柯覺得,他如此自然地參與了這樣一個“合謀”的過程。早在1999年國家提出“教育產業化”之前,實際整個基礎教育、社會文化教育已開始“產業化”。約略統計,那些“亂七八糟”的教輔書以及服務兒童的名著改編,九十年代的楊林柯至少出版了20本。
這樣的“市場化”,最終反應在學校,就是應試教育的殘酷競爭。差別化的分班制、教師“精細化管理”、教學的題海戰術,接踵而至。一所一所的高考名校,你方唱罷我登場。
雖然編了那么多教輔,教學上,楊林柯卻一直排斥題海戰術。2004年到2008年,他連續帶了五屆高三,歪打正著壓中高考題的經驗,更強化了他這種意識。
2004年,高三6個班,最后一次模擬考試,楊林柯參與的命題任務是現代文閱讀和作文。現代文選了孫犁的《老家》,作文是根據材料改編的話題作文“換一種思維”。結果當年高考,18分的現代文閱讀材料恰好就是《老家》,作文是“哭婆婆和笑婆婆”。那屆學生下了考場,眉飛色舞。
一瞬間,他成為香餑餑,高一和高三都開始搶他。
2007年,高考作文材料是歌手叢飛助學。日常作文訓練中,楊林柯曾讓學生以《發現陽光》《學會感恩》為題練過筆。2008年命模擬題時,一些語文老師覺得汶川地震太敏感,肯定不會考。楊林柯反對,語文課怎能不讓學生關心這事關生命的大災難?他圍繞地震出了66分的考題,再次猜中高考作文。
楊林柯說,之所以歪打正著,是因為他發現了世界廣泛存在的“悖論”:你越想達到什么目的,反而越不能達到。他從來沒刻意猜過題,也不覺得有什么自豪。即使從命題者角度,高考作文也一定是跟時代大勢息息相關的。為什么是“換一種思維”?為什么是“感恩”?為什么必須是汶川大地震?這些都是每年發生的無數社會變革或問題的一部分。

高考結束后的撕書節,是中國教育極化的一個縮影

熱播劇《小歡喜》從三個高考家庭的故事展開,其反映的升學壓力、親子關系等引起無數家長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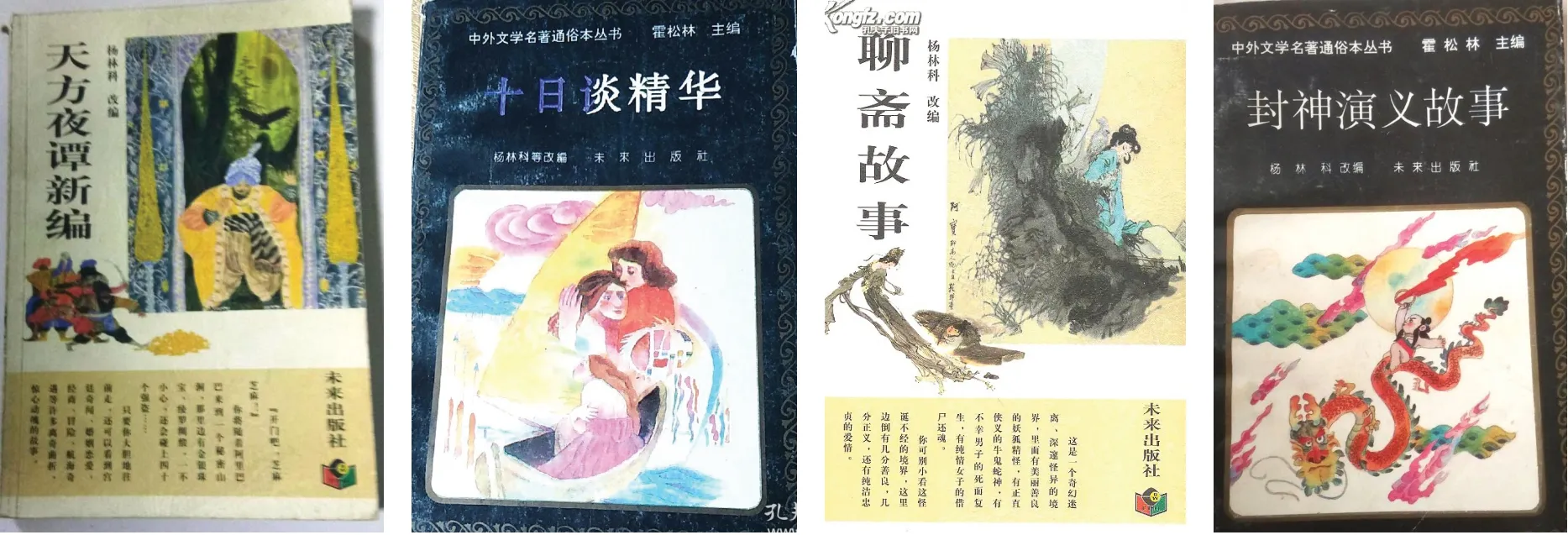
目前在孔夫子舊書網上,還能搜索到九十年代由楊林科(原名)改編的文化普及類書籍
“因此,我的邏輯是,教師得先思考教育,從全學科出發,在這個大前提下,再思考自己的科目和課堂。語文教育,只要按照教育教學規律學習,不要那么功利、短視,一定不會差。”楊林柯對記者說。
2005年,他評完職稱——高級教師,41歲。這是一種榮譽和利益,有人說“教師高級就自由”,但楊林柯卻迷茫了:找不到自己,對群體認定充滿懷疑,甚至有種當做“行貨”被處理的感覺。連續帶高三,他發現,學生比他還迷茫。除了考試和分數,什么都不關心,“像樹一樣長空了”。
也就在那幾年,為了緩解精神危機,他開始重新讀書。雖然在80年代的大學校園讀書熱潮里,他也跟風讀了不少書。如李澤厚《美的歷程》、薩特《存在與虛無》、柏楊《丑陋的中國人》、張賢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但那都是“胡亂讀書”“誰不讀似乎就精神落后了一樣”。
41歲,他才開始意識到,讀書是一個生命向內開拓的過程,是對生命的重建。
三十多年的人生,從沒書讀,到盲目閱讀,再到生命的回歸。楊林柯深感,學好語文關鍵是多讀書,開拓視野,具備獨立思考能力,這是語文之“道”。至于字詞、課文背誦、做題技巧等,僅僅是“術”。
一個想法產生了。孩子們沒時間讀書,那我自己能否多讀點,把自己變成資源?
一個系統的閱讀過程開始了。古今中外,從哲學到歷史,從周國平到王小波,從諸子百家到“圣經”,從魯迅、胡適到康德、哈耶克……發狂式地讀書。邊讀邊寫筆記,幾年下來,竟然寫完了十幾本,摞起來一尺高;邊讀邊和學生分享,沒想到課堂也開始改變,學生讀這些“私貨”比讀教材還專心,進而主動閱讀。
“在國家新課程實施以前,我其實已進行了四五年自覺改變,只是沒有上升到理論高度。”楊林柯回憶道。
那幾年,寒暑假除了讀書,就是旅游,并結交了一些追求公民教育的同仁。盡管無法說明具體是被哪本書或哪個人“點燃”了,但經歷幾年痛苦求索,他覺得逐漸“豁然開朗”,找到了教育的價值,也找到了人生意義。
理想主義者的實踐
楊林柯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想把他的理想,藏在“每一堂課”“每一次教育行為”“每一個教育細節”之中。
很多學生還記得一場大雪后,這位關中彪形大漢,浪漫到把課開在操場上,“天地就是我們的教室,自然就是我們學習的內容,快樂和成長就是我們真實的體驗”。
他的課堂不拘一格,放過電影、民歌、紀錄片、學術講座……甚至搞過“百家講壇”,讓學生連講七八場;講課時天南地北、旁征博引,國際國內大事信手拈來;大量薦書、分享文章,盡可能有趣、有料,來消解學生對應試的疲憊。老師總覺得時間不夠,學生也覺得一節課太短。
像《藍色星球》《地球脈動》之類紀錄片,貌似跟考試無關,但其中有天地之大美、敬畏生命、環保教育等因素。“盡管當時放映這個片子,是為了寫作文《發現××之美》。”楊林柯笑道。
即使復習考試,也要有趣、有價值。他原創命制的訓練題被學生放到學校貼吧上,被認為是“最牛高考訓練題”。他甚至把自己寫的文章《玄想陶淵明》選段編成閱讀題,過了許久才被人發現……
在本次采訪中,本刊記者也采訪了楊老師的部分學生和家長,看了很多學生寫他的回憶文章。談到楊林柯,許多學生用了“先生”一詞,覺得楊林柯給他們埋下了“一顆種子”。
目前在西北大學念大二的王豫川,憶及高中語文課堂,還滔滔不絕,對老樹《一席》講座中那句“眼前兩碗米飯,心中一粒飛鴻”印象深刻。厭惡背誦的他,以遇見楊林柯為幸事。好幾次,他語文考過全班第一。
他曾跟一位文科實驗班的同學聊天,發現同樣一堂《水滸傳》選文課,兩班授課風格迥異。對方老師開講前就羅列問題,按閱讀題那樣上課,楊老師則串講課文,討論某段為何這樣寫,品味關鍵句子,還展示其他章節、播放電視劇片段,并作點評和討論。

閱讀,既讓楊林柯逐漸開拓自我,也成為與學生溝通的橋梁
作業方面,楊林柯通常分必做題和選做題,必做一般是記背類型的,不搞人人過關式抽查。對作文和讀書筆記,他則批閱得一絲不茍。甚至有個別學生會寫四五十頁,要花費一兩個小時去批改。讀書筆記每兩周上交一次,但有些學生會堅持天天寫,并要求楊林柯第二天把本子還回,再接著寫。
對于讀書筆記,他給學生選擇的自由,可長可短,可完整也可零散,但一定要寫能夠觸發自己感悟的東西,不是為完成作業。他越是放得開,學生反而越自覺。偶有學生不交,第二次補交上來還會自覺寫清理由,表示歉意。楊林柯常對學生說:“如果你對自己都不負責,還可能指望你對家庭和社會負責嗎?”
他的課堂上,有學生會做其他科目作業,大家都不怕他。學生背后叫他“老楊”“柯總”“楊大大”“林柯君”,他聽到也毫不介意。他認為,直呼老師姓名也是長大的標志,不一定是不尊重老師。
楊林柯不忍心學生海量刷題,逆題海戰術大潮,班級成績卻很不錯。錢理群稱贊他“兼顧了人文與工具兩個方面”。
在反復的閱讀和課堂討論中,他的教育理念也開始成型,“震撼心靈、開啟智慧、健全人格”。大部分學生喜歡楊林柯的授課方式,沒過多抽查,更沒懲罰,重視思考,有合作互動,不怕犯錯。家長則分成很多派,有支持,有反對,多數不表態。

楊林柯與學生合影
弱化考試和刷題,不光家長不答應,個別學生也有意見。楊林柯每接一屆新生,課后總有學生追問:“老師,作業是什么?”這讓他憮然。楊林柯擔憂,很多學生的學習習慣,在初中就被搞壞了。他甚至聽過,有語文老師要求學生背誦所有課文注釋,有位高二的學生此前竟然沒讀過一本課外書。
更復雜的是,課堂上的討論,尤其對社會議題的探討,令家長覺得孩子開始“不聽話”了。有家長很氣憤,孩子竟然跟他講“平等”,兩代人的“價值觀沖突”突然被抬到前臺。
曾有幾個學生把他拉進家長群,希望老師能扭轉家長的應試觀念。他在群內發了二十多個貼子,家長們只是清一色地點贊,沒人說話。他甚至還組織過一次家長呼吁學校廢止分班制度,也無疾而終。
楊林柯覺得尷尬,只好退了群。他還記得學生們責怪他,“快被父母逼得活不下去了”。
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和一個想要扭轉應試教育弊端的老師,就這樣,最終觸到了那個中國教育最復雜的“雷區”。
無物之陣
2018年高考復習,楊林柯講過關于“語言”的作文話題,出現在了江蘇省的高考試卷上。這次不是“歪打正著”,而是“陰差陽錯”了。這種微妙的錯位,仿佛也成了對他處境的尷尬隱喻。
2012年,“萬言信”事件發生后半年,本刊記者曾對楊老師做過一次深度專訪(參見2012年11月號)。那段時期,突然走到輿論的漩渦里,楊林柯焦慮、彷徨,似乎就像魯迅說的,走入了“無物之陣”。
盡管拋出了尖銳的問題,得到了廣泛的討論,但總感覺是打在了“外套”上。一陣熱鬧之后,煙消云散。
2012年到2020年,國家整體的教育改革不斷向前推進。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把“立德樹人”明確為教育的根本任務。2017年開始試點新高考改革。尤其是語文,多少已開始落實楊林柯當年竭力倡導的“大語文教育”,以至于光明日報《教育家》雜志在2017年12月還邀約他主持了一期“大語文歸來”專刊。
2019年《關于新時代推進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導意見》,更明確提出高中在“2022年前全面實施新課程、使用新教材”“有序推進選課走班”,進行全面改革。
但是,隨之而來暴露的問題和爭論更多。“南京家長已瘋”“深圳家長已瘋”的帖子彌漫網絡。“一塊屏幕改變命運”,在改革和科技的雙重催化下,應試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甚或“素質”也成了“應試”。
“我把人家娃教醒了,卻成了我的罪狀。”這個一度令人迷惑的問題,他現在回想反而開始變得平和了。
“萬言信”事件后,楊林柯又因先后兩次家長“舉報”,一次被領導約談,最近一次被停課。他的內心也不斷地沖突,甚至有種想“逃離”的感覺。
“教醒”,是他一直堅持的語文教學原則:要讓學生學會獨立思考。如果說2012年之前,是楊林柯走向自我覺醒的過程,2012年之后,則是一個“不斷尋求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公約數”的過程。
總結起來,對楊林柯課堂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弱化了考試訓練,一是課堂的價值觀引導。即使比較認可他的家長,也對他較有傾向性的價值觀持保留態度。
記者跟一位畢業于陜師大的家長聊了兩個小時。她的兒子從小學時就愛看書,僅《明朝那些事兒》全集就看了四遍。高二進了楊林柯的班,回家就跟父母分享課堂話題。父親很認可,母親則跟父子辯論。
這位母親每年出國六七次,她跟記者談起國外見聞:新加坡的公屋面積很小,底層非常辛苦;迪拜的王公貴族生活宛在天堂;俄羅斯的男人愛打女人……這些實際的經驗不斷刷新她曾經的書本知識,打破了“外國月亮更圓”的迷思。兒子去美國游學幾次后,最終放棄了赴美留學。
二十年前去香港地區,她驚嘆不已,但近年再去,地鐵等基礎設施十幾年未變,底層百姓住房仍無好轉。“二十年間,我們的住房條件有多大改善?國家發展這么快,人口這么多,要允許一點點地改善。”她對記者說。
盡管與楊林柯有許多觀點不同,但她還是對他的教育教學理念表示贊同。觀點不同,可以討論。她最反對的,是高考極端應試化。她的孩子吃了不少虧,曾長期厭學,個中辛酸難以贅述。
對家長的這些意見,“萬言信”事件后,楊林柯讀了大量教育類書籍,也開始反思課堂,轉變教學方式,節制自己的價值判斷,讓學生自由辯論。
有很多人說,楊林柯,你其實更適合教大學。楊林柯也不諱言,他的目標,是真的想把高三做成大學預科班。他經常幫助畢業班學生填志愿:最關鍵是選擇喜歡的專業,不用太看重學校排名,反而要研究該專業是否是學校強項,包括學校的藏書量和院士數量等等。
即使復習和考試緊張,他的每堂課依然堅持“課前三分鐘”分享,不限話題,由課代表負責組織。這背后,他有很多精細的考量。長遠意義上,是鍛煉膽識、談吐等終身必備的能力。短期意義,即使為了考試,這樣既能擴展知識面,又可積累作文素材;同時,每個學生自覺變成學習資源,鼓勵大家不要盲目競爭,學會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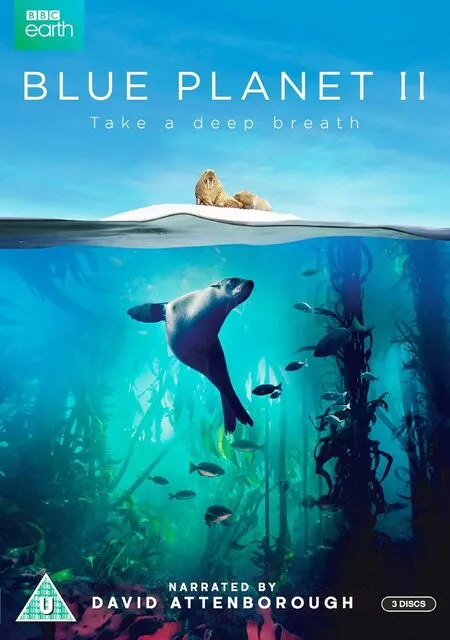
《藍色星球》海報。楊林柯在課堂放映的紀錄片,既消解學生的壓力,又有助于學生寫作
他發現,越是長期堅持,這樣的課堂反而對老師挑戰越大。學生講完,他要即興點評,這又倒逼他不斷學習,教學相長。
楊林柯至今記得,有位女生課前分享了對秦朝亡國的思考,指出《史記?陳涉世家》“失期,法皆斬”不確,按出土秦律材料,遇雨失期會受罰,不至于殺頭;又指出秦始皇“坑儒”是“坑術士”,并非專指儒家;秦代非常重視教育,六國的能工巧匠到咸陽,工資很高……漢代之后,對秦代的描述多少都帶著夸張和宣傳……這一點也讓楊林柯對歷史傳統有了新的思考。
關于價值觀引導的問題,在很多學生看來也不以為然。
趙永歡博士告訴記者,當年他的同學中,有很多人不認同楊林柯的觀點,多年后仍舊不認同。他的一位好友,高中時喜歡傳統文化,目前在中國科技大學讀博士,仍然堅信傳統文化。
“一個班五六十人,來自不同家庭,除了家長,讀書、上網等獲取信息的渠道實在太多了。擔心楊老師的課堂把學生帶偏,那是低估了學生的自覺思考能力。況且,他只是提供一種思考而已,而課堂是七嘴八舌的。”趙永歡說道。
王豫川眼里的楊林柯,并不固執,但認為老師有文科生的通病——反科學,有時也容易走入誤區。比如轉基因問題,楊林柯一度非常贊賞崔永元。為說服老師,王豫川找了不少資料,揭示反轉基因理論的漏洞。

梁文星、錢理群和楊林柯

榮膺《中國教育報》2014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
對爭議很大的宗教問題,王豫川也不同意老師的觀點,但表示理解。在他看來,絕不可因信仰去歧視或貶低某個人。“宗教對人的影響是非常復雜的。我不愛辯論,辯論的人,常抱著改變對方的意圖,若不能敞開心扉,摒棄成見,討論就無意義。”王豫川說道。
這種課堂自由辯論的教學方式,王豫川進入大學后感觸更深。
王豫川初中時就愛看書,楊林柯的課堂,保護了他的興趣,更擴大了他的知識儲備。進大學,他發覺自己反而成了“少數派”,愛讀書的人越來越少。有的人只看專業,有的沉迷網絡和游戲……
他還記得有次宿舍聊天,說到《英雄聯盟》國際比賽“天不生the shy,上單萬古如長夜”。有室友突然發問,“你們知道這句話出自哪里嗎?”不等大家回答,他非常認真地說:“最早見于《雪中悍刀行》中劍神之口,‘天不生我李淳罡,劍道萬古如長夜’。”王豫川默然。師—生
如今,在媒體公眾形象上,楊林柯儼然就是一個反應試、反傳統的“戰士”。但對很多學生,他倒更像是陶淵明和莊子。
目前在杭州讀博士的趙永歡,來自農村,高中時身體不好,高二遇見楊林柯,他很感念在激烈競爭的應試環境下,還有楊林柯這樣的老師,關注像他這樣的“弱勢群體”。此后十余年,每逢路過西安,他都要找老師敘舊。
多年以后,他才慢慢明白老師經常在課堂上念叨的那首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在重重雷區之下,要尋找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公約數實在是困難的。但對楊林柯,也許特別簡單。這個公約數的核心還是師生關系。
師—生,教師的職責,還不止引導社會問題和某種價值觀的討論,最重要的還是給學生一種生命的覺醒、“生生不息”的力量。
他的課堂,刷題少,延伸多,注重討論,充滿愛與尊重。因此,學生有小秘密或煩惱,不愛跟父母分享,更不去學校心理咨詢室,反倒愛跟他傾訴。
有位男生覺得自己有同性戀傾向,來找楊林柯講自己的成長經歷;有學生談起假期旅游,半夜聽到隔壁女人的叫聲,吵得睡不著覺;有女同學把與第三任男友的分手信拍給他看;另一位男生跟女朋友偷嘗禁果后,提心吊膽,陷入絕望,頻繁找他談心……
楊林柯生于1964年,他現在用的QQ號,還是趙永歡幫他申請的;他不擅長在網絡找資源,他下載的很多電影和紀錄片,都是王豫川幫他找的……
王豫川一度著迷于“虛無主義”,曾寫了一篇作文,被楊林柯打了高分,拿到年級組印刷。楊林柯推薦的書,他最喜歡流沙河講莊子系列。有段時間他迷上王陽明,讀了《陽明心學》,還把作者熊逸“安利”給楊林柯。
高三時,他喜歡上同桌女生,對方理綜成績低迷,極度悲觀。王豫川私下求助,說自己好朋友心理壓力大,自己勸解不了,希望他再講一次有關“價值意義”的話題,楊林柯真的為此改了課。

2017年2月27日,河北衡水二中高考百日誓師大會現場
對待高中生的戀情,楊林柯很包容。他不認同“早戀”一說。在他看來,愛的教育自然包括談戀愛的教育,這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而這恰是當下基礎教育最缺乏的。而反觀當下熱烈的PUA爭論,北大女生被自殺事件,我們仍然需要嚴厲地向教育追責。
楊林柯猜中了王豫川的小心思,只是叮囑戀愛的責任,別影響學習。就這樣,那位同桌成了王豫川現在的女朋友。
許多學生,直到大學,遇到困難仍然會找楊林柯談心。目前正在陜師大文學院就讀的大二學生趙夢雨璇,曾患厭食癥五年,不敢對別人說。她覺得,在與楊老師的不斷交流中,慢慢重建起了心靈地圖。在一封信中,她對楊林柯表達謝意:
周國平有篇文章《守望的角度》,提出了“守望者”,作者將他們比為守林人、守燈塔人。他說:“與都市人相比,守林人的生活未免冷清;與弄潮兒相比,守燈塔人的工作未免平凡。”他說——守望者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并不直接投身于時代的潮流,往往與一切潮流保持著距離。但他們也不是旁觀者,相反對于潮流的來路和去向始終懷著深深的關切。他們關心精神價值甚于關心物質價值。無論個體還是人類,物質再繁榮,生活再舒適,如果精神流于平庸,靈魂變得空虛,絕無幸福可言。
楊老師,在我眼里,您就是一位守望者。守望者最重要的東西,哪怕大家都認為微不足道,也總會有一些人在最迷茫的時候抬頭,仰望星空,被照亮腳下的路。我想說謝謝您。
守望者,看到這個詞,楊林柯百感交集。寫了那么多尖刻批評的文章,楊林柯突然覺得放松下來,這大概是一個人心底最柔軟的部分。
2019年,楊林柯重讀了一遍《蘇東坡傳》,又讀了錢理群的《歲月滄桑》,再看郭小川、趙樹理、艾青的生命經歷;暑假,他和同學一家自駕出游21天,從云貴高原到青藏高原,親自走過那些九曲的盤山路和蜿蜒的河流,他對某些歷史的曲折也變得釋然,“同情之理解”使他對自己和未來依然充滿期待。
采訪快結束時,他笑著對記者說:“我是一個‘犧牲品’,希望其他同仁汲取我的經驗和教訓。”
犧牲,是個太復雜太抽象的詞語。在這里,對于他的很多觀點和做法,筆者仍然想說一句老生常談:僅代表受訪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刊立場。
但是,透過楊林柯,橫亙在新時代教師面前的兩大問題仍然亟需討論:何謂教育常識,何謂教師自覺?在應試和素質激烈沖突的困境下,又如何找到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的“最大公約數”?進而言之,又如何找到各階層教育的最大公約數?
這或許才是整個教育變革走向良性循環的“星星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