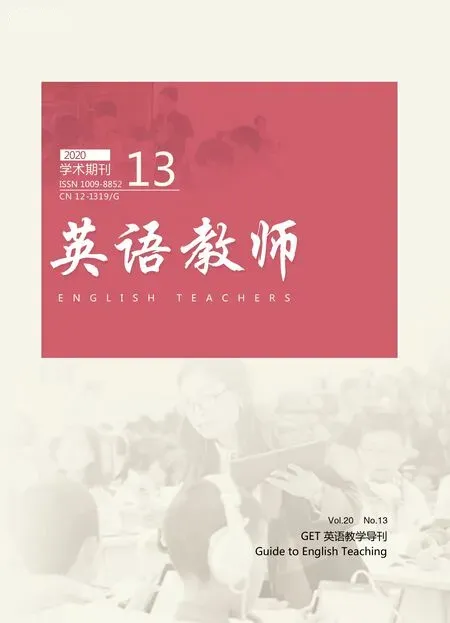中國網絡文學英譯現狀及翻譯方法
吳廣珠
引言
近年來,中國網絡小說及其改編的影視劇憑借獨特的藝術魅力,令大批海外受眾主動進行譯介和傳播(彭紅艷、胡安江 2019:114);2018年1月廣東省作家協會創辦了《網絡文學評論》雙月刊,同時《花千骨》《尋龍訣》《瑯琊榜》等網絡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引爆網絡文學。近年來,我國的網絡文學開始在海外流行,比較著名的有“武俠世界”和“地心引力故事”等,網絡點擊率很高:到2016年上半年,“武俠世界”和“地心引力故事”的點擊率分別達到5億次和2.5億次(吉云飛 2016:112)。保守估計,“武俠世界”的日訪問量為30萬次,而且北美讀者占三分之一(吉云飛 2016:112),甚至與美國好萊塢電影、日本動漫及韓國電視劇成為“世界四大文化奇觀”(王才英、侯國金 2018:41),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中國網絡文學具有新鮮的中國文化元素——玄幻仙俠小說加上一些民間網絡翻譯平臺的推動傳播。雖然目前對網絡文學的認識還存在很多爭議,網絡文學甚至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無法與主流文學相比,但其也有傳播優勢:語言通俗易懂,外國讀者不需要掌握太多中國文化背景便能輕松閱讀,而且網站往往支持雙語閱讀,能夠引起外國讀者的興趣,使他們潛移默化地了解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
翻譯文學的本質在于傳播文化(林玲 2018:94),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網絡文學在海外的輸出和傳播,有必要進一步了解中國網絡文學在海外的英譯現狀,分析譯者所使用的翻譯方法和策略。
一、中國網絡文學英譯現狀
將“中國”“網絡文學”與“翻譯”作為關鍵詞,通過知網搜索2000—2019年網絡文學的翻譯研究文獻,截至2019年11月16日,獲得的數據見表1:

表1:2000—2019年知網網絡文學翻譯研究文獻統計表
從表1可以看出,近20年來,知網上收錄的網絡文學翻譯研究論文共有博士論文1篇、碩士論文18篇、期刊論文41篇;然而,2000—2014年僅有4篇,但2015—2019年高達56篇,是前15年的14倍,尤其是2018年、2019年相關論文44篇,占20年間論文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最早論及網絡文學翻譯的論文是陳遼(2002:63)的《“全球化”下的中國文學》,提出21世紀一要著重發展網絡文學的翻譯文學;二要著重發展以業余作者為創作骨干的群體文學;三要著重發展翻譯文學等;2007年豐云的博士論文《論華人新移民作家的飛散寫作》探討新移民作家利用在海外的優勢開辟了漢語網絡文學;2013年金暉的《中文網絡流行語英譯探究》探討了中國網絡文學流行語的翻譯方法;吉云飛(2016:112,115)的《“征服北美,走向世界”:老外為什么愛看中國網絡小說?》一文認為:自2015年初,中國網絡小說開始在北美流行,并以北美為中心向世界輻射,中國網絡翻譯文學成為中國網絡小說的“另類可能”。文章刊登后影響很大,引用次數達29,下載次數達1468,但文章只是較系統地介紹了北美“武俠世界”和“地心引力故事”等中國網絡文學翻譯網站。郭競(2017:85)的《也談中國文學翻譯出版“走出去”——以中國網絡文學歐美熱為例》一文,認真提出傳播力不強仍然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最大痛點,但是中國網絡文學歐美熱為中國文學翻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文章刊登后影響較大,引用次數達24,下載次數達1310,但文章只是從宏觀而論;席志武、付自強(2018:79)的《我國網絡文學海外傳播現狀、困境與出路》一文提出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要堅持內容為王,創作并傳播符合主旋律精神的“高峰之作”,積極參與海外傳播和競爭,增強國際話語權,變被動的“拿過去”到主動“走出去”;尹倩、曾軍(2019:171)的《中國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現狀及其問題》一文指出:中國網絡文學仍未被西方主流文學圈認可,提升網絡文學作品的翻譯質量、加強對正版網絡文學的授權和培育海外網絡文學用戶網絡付費閱讀的習慣至關重要;楊曙、尹付(2019)的《國際傳播視域下中國網絡文學“走出去”策略分析》及劉陽(2019)的《中國網絡文學對外傳播的“在地化”建構:歷史、現狀和思辨》等從宏觀上討論了中國網絡文學的翻譯。
鑒于中國網絡文學的翻譯與傳播不僅僅是理論問題,更是實踐問題,是一種自下而上、由點及面的翻譯效應,因此,對網絡文學譯者水準及譯者的翻譯方法都有必要探討。基于此,擬從實踐視角探討中國網絡文學的翻譯。文章中的例子均出自“武俠世界”和“地心引力故事”。
(一)譯者群體
一部作品在海外的成功,除了作品優秀外,翻譯也決定了其可讀性,因而譯者是僅次于作品的一個重要環節,所以譯者既應具有較強的“雙語能力”,又應具有較強的文化意識和“雙文化能力”(劉明東、何曉斕 2011:122)。網絡文學翻譯傳播的初期階段,譯者主要是一些喜愛中國文化或武俠玄幻類文學的海外華人,隨后一些翻譯平臺如Wuxia World和“起點國際”等開始興起,從而出現對中國網絡文學的批量翻譯。
這些譯者的等級劃分就如同玄幻小說中的修仙體系,大部分網絡文學譯者處于低級階段,主要根據原文,采用“直譯+注釋”和“音譯+注釋”的方法一字一句地翻譯,讓讀者看明白,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進階階段的譯者會讓讀者在讀懂情節的同時,增加故事的可讀性和生動性,并通過各種方式讓讀者感受故事人物此時此刻的情緒。而高級別的譯者甚至會修改原作者在故事情節和前后文邏輯的錯誤,并將原作者未表達完整的意思敘說清楚,但由于難度較大,所以此類高階譯者目前較少。
(二)所選譯的作品
目前幾個較出名的海外翻譯團隊大多由華裔組成,他們既熟悉英語又對中文有一定的了解,更了解國外讀者的閱讀興趣,因此這些翻譯團隊在選譯作品時一般選擇玄幻小說類網絡文學,既不是純粹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言,又不是單純西方奇幻思想的延續,而是在全球化語境下二者的雜糅(邱凌、韓婕 2017:94),情節套路與外國魔幻小說(fantasy novels)有些類似,但敘事簡單直白,隱喻等修辭手法使用較少,適合大部分國外低語境國家的讀者閱讀(谷學強、汪中瑞 2017:58)。
二、英譯方法
中國網絡玄幻小說中出現了很多讓外國讀者感到新鮮的中國文化元素,如“六道輪回”“五行三界”等(林江依、段綺茹,等 2017:32)。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很多中國元素無法在英語中找到指稱意義和蘊含意義相對應的詞匯,因此在網絡小說的跨文化傳播中,翻譯者的譯介策略可謂是決定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一環(谷學強、汪中瑞2017:58)。本研究將分析網文譯者翻譯時使用的幾種方法:
(一)直譯法
直譯法是翻譯網絡文學常用的方法。翻譯一些獨具中國特色的詞匯、俗語、成語或者在翻譯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匯時,往往采用“直譯+注釋”和“音譯+注釋”的方法,能基本保留漢語詞匯中的原文化信息。
例1:
原文:刀山火海
譯文:a mountain of blades and a sea of fire(meaning:extreme danger)
“刀山火海”在中文中形容極大的危險,采用異化的直譯方法直接在目的語讀者腦海中產生像尖刀形成的山、如火焰地獄般熊熊燃燒的海的形象,不存在難以理解的文化障礙,因而“直譯+注釋”更能體現原文的精彩。
例2:
原文:冰清玉潔
譯文:clear as ice and clean as jade(meaning:spotless;incorruptible;irreproachable)
玉和冰給人的感覺是干凈通透,且ice在英語口語中也有diamond(鉆石)的含義(陸谷孫 2007:935),所以這個成語直接用異化的方式或“直譯+注釋”的方式英譯,表示純潔無瑕,英語國家讀者也能夠明白這個中國成語的意思。
例3:
原文:一片世外桃源的樣子
譯文:appear like a pristine utopia
原文:青年的臉上卻沒有一絲血色,蒼白如紙樣。
譯文:The young man’s face was devoid of all colors,as white as snow.
此外,“五行”“三界”“六道輪回”和“有眼不識泰山”分別被譯作 the Five Elements,the Three Realms,the Six Paths of Reincarnation 和 have eyes but fail to recognize Mountain Tai。上述這些陌生化的翻譯方法可激發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的好奇心。假如譯者將“有眼不識泰山”歸化譯作entertain an angel unawares或fail to recognize an VIP and pay due respect he/she deserves,目的語讀者定然不會如閱讀“have eyes but fail to recognize Mountain Tai”一般深切感受到原語的文化。
對小說名稱的翻譯:Wuxia World平臺上翻譯小說名大多采用直譯法。由于標題字數有限,小說名的翻譯往往不加注釋,如《盤龍》《原血神座》《仙逆》《三界獨尊》《天啟之門》《生生不滅》《龍符》《莽荒紀》《天珠變》《無敵劍域》《仙魔變》《祭煉山河》《圣王》《光之子》《狩魔》和《斗破蒼穹》分別被譯成Coiling Dragon,Divine Throne of Primordial Blood,Renegade Immortal,Sovereign of the Three Realms,Gate of Revelation,Everlasting,Dragon Talisman,Desolate Era,Heavenly Jewel Change,Almighty Sword Domain,Immortal Devil Transformation,Refining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Sage Monarch,Child of Light,Demon Hunter和 Battle Through the Heavens。
“地心引力故事”網站將《巨龍的野望》《仙武同修》《美女和保鏢》《地心》《災厄紀元》和《妖的境界》分別譯成A Dragon’s Curiosity,Martial Dual Cultivation,Beauty and the Bodyguard,Earth’s Core,Era of Disaster和 Demon’s Realm。
對小說中一些武功招式和武器的直譯:“打狗棒”被譯為Dog-Beating Staff,“降龍十八掌”被譯為Eighteen Dragons-Subduing Palms。對小說人物的介紹:孟婆譯為Granny Meng,“玉皇”譯為Jade Emperor,等等。“奇經八脈”(Eight Extraordinary Meridians)、“任脈”(Conception Vessel) 和“督脈”(Governing Vessel)等經絡術語的翻譯基本采用了中醫界的通行譯法(劉毅、張佐堂 2018:102)。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采用直譯的方式而可能造成目的語讀者誤解的例子,如下:
例4:
原文:打雞血
譯文:injected with chicken blood
隨著網絡的發展,說“某人像打雞血一樣”,主要是借以諷刺此人對特定的人物或事物突然情緒亢奮的一種行為表現。然而,這樣的含義在英語中沒有,如果直譯且不加注釋,可能會引起目的語讀者的誤解。
例5:
原文:愛麗絲是個悶葫蘆。
譯文:Alice was a closed gourd who hid her thoughts.
“悶葫蘆”就是不喜歡跟人交流,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這是漢語中的一個隱喻,形象生動,富有異域色彩。為了成功地表達這個意思,譯者采用了異化的策略將這個富有異域情調的文化表達出來,同時,為了減輕目的語讀者的文化障礙,增譯了“who hid her thoughts(to herself)”,這樣一來,目的語讀者很容易明白原文的意思。
例6:
原文:腹黑
譯文:black belly
“腹黑”一詞源自日本,中文中指“外表溫柔,內心詭詐的人”,在英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而直譯的black belly也無法讓目的語讀者理解,所以必須加以注釋或意譯;類似的還有wash one’s hands in a golden basin(金盆洗手)等。
(二)音譯法
在玄幻小說中,一些中國神話傳說關于修仙的術語及專有名詞具有豐富、深厚的內涵,在英語中完全找不到對應的詞匯,如“武俠”(Wuxia)、“江湖”(Jianghu)、“武林”(Wulin)、“道”(Dao)、“氣”(Qi)、“陰”(Yin)和“陽”(Yang)等,闡釋起來較難,所以將漢字的拼音形式直接作為英譯詞匯,是譯者常用的術語翻譯方法之一(萬金 2017:31)。
對于中國傳統的計量單位,譯者也直接處理為標音詞匯(見表2)。

表2
另外,譯者在翻譯包括中國一些神獸在內的動物時也采用了音譯法,如龍生的九子:Qiuniu(囚牛)、Yazi(睚眥)、Chaofeng(嘲風)、Peng(鵬)和Pixiu(貔貅)等。
(三)意譯
在翻譯中國網絡文學時,一些譯者主張以意譯為主,直譯為輔,不是直接或僅僅使用拼音或音譯,從而對中國文化元素進行“淺化”處理(劉毅 2017:95)。由于直譯在很多情況下是歸化法翻譯,因而避免了由于過度異化而難懂,追求將中國特色詞匯自然地融入小說語篇所帶來的閱讀障礙。
例7:
原文:斗氣
譯文:Battle qi,a form of internal energy
“斗氣”(Battle qi)的“氣”采用音譯、意譯結合的方法,以意譯為主,加上a form of internal energy注釋,進一步讓目的語讀者理解中國特色詞匯的內在含義。
例8:
原文:鳳毛麟角
譯文:rare as phoenix feathers and unicorn horns(Meaning:extremely rare objects)
在中西方傳說中均存在鳳凰,但是麒麟是中國神話中特有的神獸,無論采用直譯法或音譯法,都很難讓英語讀者更直接地理解這一成語的含義,于是譯者采用了歸化的策略,將英語中既存的表達或者已有的翻譯直接拿過來(張順生 2015:92);用英語讀者更熟悉、類似麒麟的神獸獨角獸替換,這一成語要表達的稀少又珍貴的意思便能形象地傳達給目的語讀者。由于目的語中意義相同、相近的表達能夠簡潔地再現原文的魅力,故而通常是翻譯的首選。類似的翻譯還有“俠”“妖”“魔”,分別被譯作Hero,Demon,Devil,便于以英語為母語的讀者或其他以英語為二語的學習者所認知和理解;否則,文化負載詞“江湖”這樣的詞無論音譯為Jianghu,還是直譯成Rivers and Lakes,不懂漢語文化的目的語讀者都不易理解。
例9:
原文:那樣的實力,將會讓得任何勢力趨之若鶩。(選自《斗破蒼穹》)
譯文:With that kind of strength,most places would probably rush for recruitment.
此段描繪的是“大斗師往往聲名遠揚,各地都愿意聘請”,若拘泥于原文,將“趨之若鶩”直譯為go after somebody like flock of wild ducks,目的語讀者很可能不知所云,于是譯者采用了目的語受眾熟知的行文方式(張順生 2015:93),用意譯的方式將其譯作rush for recruitment,通順且完整地表達了原文要表達的含義。此外,將“被打得落花流水”譯作 be utterly beaten(陳小春 2018:40)及 someone who can be beaten so easily(陳小春 2018:42)都是典型的意譯例證。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對中國網絡文學通過英譯對外傳播得出以下啟示:
當下,中國網絡文學憑借網絡平臺的傳播力量迅速崛起,其能在海外傳播并受到海外讀者喜愛正是得益于英語中介語言(郭競 2017:85),得益于網絡翻譯;之所以較成功,主要得益于譯者采用多元的翻譯策略,注重直譯、音譯,輔以意譯。
由此可見,面對中國網絡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中國特色文化,譯者要充分考慮接受群體的閱讀習慣和審美情趣,盡量借用西方讀者熟悉的文化圖式消解文化傳播中的阻礙,用目標語讀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激發讀者興趣,傳播中國文化,保持跨文化傳播中“自我”與“他者”的平衡。
在推動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時要考慮一些務實的做法和策略,讓西方國家讀者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謝天振 2018:8)。當然,在翻譯過程中,如果過分注重“他者”,則背離了翻譯為交流文化的初心。因而,在文學外譯這一過程中,要始終保持“自我”與“他者”的平衡,達到翻譯的真正目的。
當然,中國網絡文學外譯依然任重道遠,存在諸多困難,因此,不僅需要民間譯者的努力,還需要源源不斷的專業譯者和國家的支持,從而避免中國網絡文學在對外傳播中曇花一現。因而,未來的文學英譯傳播更應利用網絡的力量,將中國網絡文學愛好者和譯者凝聚在一起,共同推動中國文化對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