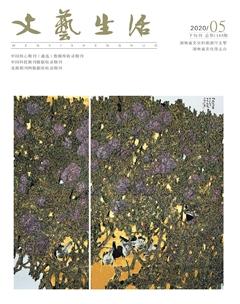淺談電影《敦刻爾克》中視聽語言的氣氛表達
摘要:電影《敦刻爾克》火爆全球的同時,其恐怖、懸疑氣氛的表達成為了其區別于其他同類型戰爭片的一大亮點。影片中并無殘暴血腥的戰爭畫面直接表達,導演諾蘭卻能以其高超的視聽語言使每一位觀眾神經緊繃、心跳不已。本文將從分析視聽語言的角度出發,淺談克里斯托弗·諾蘭是如何在《敦刻爾克》中渲染戰爭的恐怖氣氛。
關鍵詞:《敦刻爾克》;戰爭片:視聽語言
中圖分類號:J617.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 (2020)15-0106-01
一、詭譎多變的音樂表達,從聽覺喚醒觀眾的緊張神經
《敦刻爾克》之所以能制造令觀眾恐慌、緊張的沉浸式觀影體驗,其出色的配樂及音響表達是居功至偉的。為電影《敦刻爾克》配樂的漢斯·季默被譽為“好萊塢大片配樂代言人”,他也通過《敦刻爾克》獲得了奧斯卡“最佳音效剪輯”和“最佳音響效果”獎。從影片開頭,幾個幸存的英國士兵而對著漫天飛舞的勸降傳單,隨著敵人槍響,英國士兵們落荒而逃,鐘表滴答聲的音響開始回蕩在觀眾耳邊,觀眾的緊張神經迅速就被揮之不去的滴答聲激發,開始為英國士兵的命運捏一把汗。
在克里斯托弗·諾蘭的電影中,滴答聲已成為了一種特色,它是諾蘭在電影中營造恐怖氣氛的音響利器。在《敦刻爾克》中,錯落的滴答聲和緊張的心跳聲頻頻出現,它可以渲染恐怖氣氛并讓觀眾緊張,同時還隱喻了劇情中大撤退的時間緊迫,進一步加強了觀眾的恐慌感。
除去滴答聲之外,戰斗機們掠過空中時頻頻發出的尖嘯聲也在刺激著觀眾的聽覺神經。諾蘭在《敦刻爾克》中的戰斗機演繹上十分考究,無論是英國人引以為豪的噴火式戰斗機(spitfire)還是德國制造的BF-109和JU-87俯沖轟炸機都很還原史實,讓觀眾更身臨其境地感受二戰。在影片中,德軍的JU-87俯沖轟炸機可謂是英法聯軍的夢魘,其所到之處的英國士兵無不膽顫心驚。JU87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其獨有低沉的尖嘯聲,如鬼魅在風中呼號。在二戰中,納粹德國空軍大量投入的JU87不但給予地而目標毀滅性的打擊,同時它獨有的發聲裝置所發出的尖嘯聲也給地而的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在《敦刻爾克》中,諾蘭十分真實地還原了JU87的尖嘯,并且通過IMAX等技術手段,令其所表達的恐怖感倍增。
在《敦刻爾克》的配樂中,“謝潑德音調”的運用也增加了觀眾的緊迫感。“謝潑德音調”由間隔八度的若干音調復合而成,隨著音階上升,高音強度逐漸減弱,中音強度不變,而低音逐漸增強顯露出來。這種音效充滿了詭異感,音調似乎一直上升,事實上卻在原地徘徊。
《敦刻爾克》中隨著劇情發展深入不斷前進的“謝潑德音調”為影片帶來了大量緊張感,當敵機來襲、徘徊在海灘上空時,配樂的旋律似乎不斷上升,但卻始終沒有升高,這一方面可以模擬戰斗機的轟鳴聲,制造壓抑恐慌的氛圍;另一方面越來越快的配樂旋律可以充分調動觀眾的緊張感。
二、無明確主角設置,三條故事線并進從多方位體驗緊張
在影片《敦刻爾克》中,明明講述的是二戰前期至關重要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事件,諾蘭卻并沒讓希特勒或丘吉爾等政客出現,而是從陸上一星期、海上一天、空中一小時三條故事線入手,將關乎四十萬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件從每一個切身參與行動中的軍人視角串聯起來。在如此龐大的歷史背景下,諾蘭選擇了呈現每個小人物的命運。從影片開頭不慎掉隊但卻費盡心力想要回到祖國的英國士兵,到駕駛自家游艇義務反顧駛向戰爭前線的平民船長,再到擊落數架敵機保護戰友自己卻身陷敵營的英國空軍飛行員,諾蘭不選擇個人英雄主義刻畫,通過著重講述某一人物其冗長的故事來達到反戰目的,而是選擇海陸空三個陣營中并不舉足輕重的小人物來概括整個大集體的故事。不管是爭奪他人生存資源想活著回到祖國的普通士兵、被德國魚雷嚇出PTSD的返航士兵、自愿留下幫助法國人的英國將軍、還是為了四十萬人的存亡只身飛向敵營的飛行員,諾蘭通過這些角色或自私或無私的復雜人性刻畫,更深刻地向身處和平年代的觀眾展示了戰爭的殘酷與人之本性,同時小角色的設置也令觀眾更有帶入感,增強了影片沉浸式的觀感體驗。
同其他戰爭片不同,影片《敦刻爾克》中全片沒有出現敵軍人物的刻畫,只有寥寥的槍聲、敵機掠過的身影以及影片結尾處飛行員被俘時模糊的德軍身影。諾蘭把敵軍放在了影片之外,影片的恐怖氣氛卻揮之不去,如同幽靈一般縈繞在每個觀眾的心頭,這一切都要歸功于諾蘭爐火純青的視聽語言講述。
參考文獻:
[1]孫雨薇.論電影配樂的創作手法及其作用——以電影《敦刻爾克》為例[J].北方音樂,2019(09).
[2]胡珺.逼近體驗性——以回到現場為目標的《敦刻爾克》[J].影劇新作,2019 (01).
作者簡介:劉周樂(1999-),女,江西南昌人,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在讀學生,廣播電視編導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