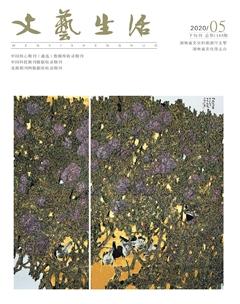飾演瓊劇《憶十八》中的梁山伯有感
葉建宏
摘要:戲曲舞臺藝術(shù)它的多元化形式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基礎(chǔ)都在于劇本之中,通過導(dǎo)演的二度創(chuàng)作調(diào)度,在舞臺上演“活”劇中人物,塑造出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給觀眾以審美享受。因此,戲曲發(fā)展數(shù)百年來,如何演“活”角色成為了一輩又一輩演員孜孜以求的目標(biāo)。本文將通過過《憶十八》的舞臺實踐,就飾演“梁山伯”這一角色談些膚淺的認(rèn)識和表演體會。
關(guān)鍵詞:瓊劇;出處與梗概;唱與演的藝術(shù)探索;內(nèi)在的藝術(shù)形式
中圖分類號:K25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 (2020)15-0121-02
一、《憶十八》的出處與梗概
“憶十八”是傳統(tǒng)戲《梁山伯與祝英臺>(以下簡稱《梁祝》)中的一個故事情節(jié),它不是從劇中節(jié)選的折子戲,而是由京劇厲家班成員朱福俠于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中期根據(jù)《梁祝》一劇編演出的新戲。說到《梁祝》,觀眾朋友們應(yīng)該是非常熟悉的,它講述這么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祝英臺女扮男裝往杭城求學(xué),路遇梁山伯結(jié)為兄弟,同窗三載,情誼深厚。祝父催女歸家,英臺行前向師母吐露真情,托媒許婚山伯,又在送別時,假托為妹作媒,囑山伯早去迎娶。山伯趕往祝家,不料祝父已將英臺許婚馬太守之子馬文才,兩人在樓臺相敘,見姻緣無望,不勝悲憤。山伯歸家病故,英臺聞耗,誓以身殉,馬家迎娶之日,英臺花轎繞道至山伯墳前祭奠,霎時風(fēng)雷大作,墳?zāi)贡眩⑴_縱身躍入,梁山伯與祝英臺化作蝴蝶,雙雙飛舞。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戲曲劇種都有搬演該劇,并且是久演不衰。而《憶十八》以十八相送為對應(yīng)點,說的便是梁山伯相送女扮男裝的學(xué)友祝英臺之后,朝思暮想,乃著意訪祝,在路上面對舊景,回憶往事,勃然動情,如癡如醉的一個橋段。海南省文化藝術(shù)學(xué)校將其移植而來,由瓊劇作曲家張拔山老師作曲,作為小生教學(xué)的劇目課內(nèi)容之一。
二、《憶十八》中唱與演的藝術(shù)探索
《憶十八》是唱做并重,屬于梁山伯的一出重頭戲,一整場表演下來將近十三分鐘,一個演員要在臺上獨自表演這么長時間,且還是一段與傳統(tǒng)《梁祝》中“思祝下鄉(xiāng)”完全不一樣的“新”戲,必將會引來廣大新老觀眾盼‘挑剔”的眼光。為了將這出戲演好,筆者除了觀看茅威濤、吳風(fēng)花等越劇范派名家的演出以外,還細(xì)細(xì)的揣摩了較有影響力的一些瓊劇名家飾演的“梁山伯”,經(jīng)過研究,我發(fā)現(xiàn),陳華老師在60年代時飾演l拘“梁山伯”給人予耿直中的悲戚之感,而吳多東老師在90年代時飾演的“梁山伯”則表現(xiàn)出了憨厚中的篤誠。
那么,新時期下的傳統(tǒng)戲曲,如何才能更好地吸引一批年輕人的關(guān)注?又該以何種形式往前人的經(jīng)典劇目中打造出自己的特色,符合當(dāng)代人的審美需求?我想起了“青春時尚”一詞。筆者希望所呈現(xiàn)出來的“梁山伯”,能夠脫離老版《梁祝》的束縛,以浪漫的風(fēng)格和人性深度開掘的視角,尤其要在突出唱功的基礎(chǔ)上,加大做功的處理,給古老的瓊劇刮來一陣春風(fēng),給瓊劇表演帶來新的挑戰(zhàn),給觀眾一個具有“初戀少年青澀與清澈”氣質(zhì)的梁山伯。
在熟悉劇情,把握人物的前提下,筆者找到了感覺:結(jié)合之前學(xué)習(xí)京劇、昆劇、越劇等劇種的表演手法,將其揉入到了瓊劇藝術(shù)表演當(dāng)中,并發(fā)揮了小生身段和表演的特長,大量的運用水袖功、扇子功、圓場、碎步等戲曲表演程式與技巧,化為戲中情境,納為己用。于是,出場時身著一襲白色褶子,手執(zhí)一柄折扇,一副溫雅如玉謙謙然的書生打扮。“祝家莊訪英臺我喜盈盈”程途內(nèi)唱之后,急切的音樂碾過舞臺,筆者撩著袍角興沖沖的飛趕上場,一個轉(zhuǎn)身亮相,喜不自禁,只為能早日見到那朝思暮想的“賢弟”。一路上,悠長的憶想,懊惱的自責(zé),甜蜜的暗笑……筆者將一切情感都交付于受眾手中這把折扇之中,為了做到以扇傳情,筆者綜合運用了抖扇、展扇、轉(zhuǎn)扇、拋扇等多種扇花技巧傳遞著山伯的情感,讓觀眾跟著表演者出城過關(guān),隨之情緒激昂,慢慢地,這類清爽陽光、朝氣蓬勃的“梁山伯”,這類渾身的細(xì)胞都散發(fā)著喜悅音符的“梁山伯”感染了在場的觀眾。
十八里路程并非通途,而是需要跋山涉水,一路上甚是艱辛,途中有表示難走的路,難淌的河,難跨的橋,戲曲動作都要將它充分體現(xiàn),在“過了一山又一山”時,筆者單抖扇快步,繼而單翻袖轉(zhuǎn)身,以示趕路,身段繁復(fù)細(xì)膩,又突出了戲曲表演程式的虛擬性。翻越了幾座山,離英臺家還遠(yuǎn)著呢,得繼續(xù)往前走,過池塘、過獨木橋、進(jìn)觀音堂。獨木橋橋面狹窄,得小心翼翼地走出搖晃且不摔倒的模樣……看不透、思不透,解不透十八相送時英臺的各種比擬,山伯在憶十八的途中終于茅塞頓開,將謎底一一破解了,原來所有的謎面暗藏著英臺真情告白,想起英臺把“弟兄?jǐn)y手在獨木橋上”說成是“多情織女會牛郎”,山伯心中一陣得意和竊喜,一個踉蹌差點摔倒,機(jī)敏地一個平轉(zhuǎn)開扇……此時的山伯是心如兔撞的,心兒已飛到英臺的身旁傾訴相思情長,想要見到英臺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了。
這時候的身段、眼神、一行一止總關(guān)情,我要求自己每一個動作都要盡善盡美,要透露著兩分書卷,承襲著三分儒雅,更兼具五分癡情,洋溢著青春與浪漫。“叫四九,奔祝莊,我心花怒放”這時心比箭長,腳下生風(fēng),從小碎步到圓場,由慢至快,我在場內(nèi)直走得襟飄衣飛,時而急促,時而輕盈,卻又不失瀟灑書生的風(fēng)流之美,這一套動作做下來分寸感極難拿捏,收一分,則木訥呆滯,放一分,則庸俗淺薄。
三、內(nèi)在的藝術(shù)形式
作為一個專業(yè)演員,要把戲唱好,將技巧運用得好,必須要做到以字生腔,以唱抒情。《憶十八》整個戲的唱腔設(shè)計基本在中低音區(qū),按照瓊劇的板腔特點,不是特別好表現(xiàn)山伯興高采烈的心情。筆者反復(fù)琢磨,總結(jié)出《憶十八》的唱腔藝術(shù)處理,第一點是要突出一個“憶”字,第二要抓住一個“喜”字,第三要強(qiáng)調(diào)一個“急”字。前半段是梁山伯思索的過程,行腔和動作比較舒緩,意在表達(dá)他一邊走一邊陷入對往事的思考,而思考的過程又是一點一點推進(jìn),下半部分,記憶的閘門漸漸打開,唱腔的節(jié)奏就稍微加快了。因此,在唱腔中,我著重在字上狠下功夫,尤其要通過咬“字”表達(dá)出梁山伯急切想見到祝英臺的心情以及三年同窗共讀的深厚情誼。第一句“祝家莊訪英臺我喜盈盈”中“訪英臺”這三個字,我先是由輕到重再細(xì)細(xì)的控制往外送,體現(xiàn)梁山伯急切又含蓄的心情。接下來“一邊走一邊想”這六句唱腔,我又要突顯一個喜,一個想,一個呆,一個忖,表現(xiàn)梁山伯一路上沿途而去的復(fù)雜心情,到了長亭之后,有環(huán)顧四周,送祝英臺歸家的情景回憶,這段唱腔的著力點在于誤會解開的心情反饋,梁山伯重走十八里相送路,觸景生情,時時憶起祝英臺花樣迭出的啞謎,對自己的木訥遲鈍懊悔不已。“她曾經(jīng)梅花透露春消息”,這個“她”是梁山伯浮現(xiàn)的祝英臺的視覺形象,在演唱的過程中,我認(rèn)為這個“她”是要唱得充滿深情的,而且音量是需要控制的,要有一種跟祝英臺交流的心情,而唱到“我卻像泥塑木雕不知其情”,這個“我”字就要有點自責(zé)意思,因此,音量要加重,這個“她”和“我”的音量對比,在語氣、語調(diào)方面就很好地渲染了山伯的心境。如此系統(tǒng)地處理下來,觀眾是可以感受得到,梁山伯這個人物的心理是非常細(xì)膩的。
四、結(jié)語
以上便是筆者對劇本的分析和對人物的看法,也是筆者在演出中遵循的依據(jù)及演出后的總結(jié)。《憶十八》盡管只是一段十三分鐘的小戲,但為了塑造好一位翩翩風(fēng)度,款款深情,俊朗氣質(zhì),儒雅做派的梁山伯,筆者花費了不少心思。現(xiàn)在回想起來,雖然當(dāng)時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感覺很有難度,但是越有難度越能從中發(fā)現(xiàn)了創(chuàng)造人物的樂趣和激情。今后,筆者會迎難而上,繼續(xù)為廣大瓊劇觀眾奉獻(xiàn)更多精彩的人物形象。(上接第120頁)發(fā)的創(chuàng)作理念。中國的戲劇往往更加追求對物質(zhì)世界的超越和對美的追求,體現(xiàn)東方哲學(xué)中特有的文化氣息,和對天人合一等思想和精神的追求。這一階段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往往與帝王的統(tǒng)治具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性,宣揚對百姓仁義禮智信等方面的教育,使其安于現(xiàn)狀,以維護(hù)帝王的地位和社會的階級,同時體現(xiàn)了對和諧美和圓滿的追求,“哀而不傷”的審美情趣滿足了當(dāng)時人們的精神需求和取向。
在意大利的歌劇文化中,往往充滿了現(xiàn)實主義、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的精神色彩,強(qiáng)調(diào)主人公的個性與自我意識的覺醒,強(qiáng)調(diào)人的行為不再受到傳統(tǒng)的封建禮數(shù)的制約,而是遵從自身內(nèi)心的真實需求和憧憬。這一時期的戲劇創(chuàng)作往往是為了取悅貴族或上層階級的人士,忽略了群眾對于戲劇文化傳播的重要意義,脫離了人民群眾和社會背景,從而被迫走向了衰弱。
在傳統(tǒng)中國戲劇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嚴(yán)格地遵守著舊社會的道德和規(guī)范,從而壓抑自己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和情感,表現(xiàn)出道德的約束下人們的個性得不到解放,無法自由的追求幸福的無奈和苦悶。而在西方的歌劇文化中,對人類個性和自由的追求的表現(xiàn)則發(fā)揮的淋漓盡致,尤其是在中世紀(jì)文藝復(fù)興時期,人們的行為雖然受到傳統(tǒng)文化習(xí)俗的約束,但不乏對新事物的追求和渴望自由的理念,這種思想推動了中世紀(jì)封建社會的瓦解。
四、結(jié)語
綜上所述,無論是中國的傳統(tǒng)戲劇還是意大利的歌劇文化,都對其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和文化思想等有著充分的體現(xiàn),反映著人們對美好社會的追求和渴望。對比中國和意大利的傳統(tǒng)戲劇,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的歷史差異和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有助于相關(guān)人員對二者歷史和文化的深刻發(fā)掘和研究。
參考文獻(xiàn):
[1]游溪,中意戰(zhàn)爭喜劇片對二戰(zhàn)歷史不同的戲劇性想象[J].河南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6 (04).
[2]肖雄,古典美與現(xiàn)代美的詮釋——觀國家大劇院版《納布科》與《游吟詩人》有感[J].人民音樂,2014(07).
[3]吳清平,童年看戲,看戲中“真”意[J].福建教育,2018 (001).
[4]宮旭,競賽類真人秀節(jié)目的攝影造型探究[J].產(chǎn)業(yè)與科技論壇,2015 (23).
[5]劉正維.風(fēng)格、個性、主題——關(guān)于戲曲音樂創(chuàng)作[J].人民音樂,2005(03).
[6]鄧蔚,論許淵沖的翻譯三美理論——以《西廂記》許譯本為例[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2013.
[7] Mila,M.,de Aranda.C.G.P.&Tamargo,C.S.El arte de Verdi.Alianza, 1992.
[8] Southwell-Sander.P.Giuseppe Verdi. EdicionesRobinbook,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