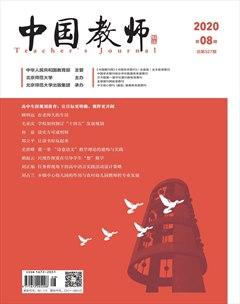魯潔先生的三次“鞠躬”
趙志毅
在先生身邊19年,離開先生也有11年了,然,先生的點滴小事記憶猶新。
凌晨暴雨一鞠躬
1992年5月,魯潔先生的首屆博士研究生龐學光畢業答辯,邀請黃濟先生、王逢賢先生、陸有銓老師擔任答辯委員會委員。我們幾個在讀博士生分頭負責接站工作,大師兄陳衛負責迎接北京師范大學的黃濟先生,我的任務是去南京火車站迎接東北師范大學的王逢賢先生,師弟張勝勇則去接1991年從山東師范大學調到上海教育學院的陸有銓老師。前一天夜里10點左右,天下小雨,我沒當回事,帶著一把抽拉式的天堂傘從南京鼓樓區寧海路122號南師大正門步行到珠江路乘31路公共汽車到南京火車站。列車預定抵達的時間是午夜1點,我買了張站臺票,進了候車室坐在長條椅子上邊讀書邊等待。窗外,雨越下越大,從長春開往南京的列車晚點,凌晨四點才進站。我冒著大雨沖上站臺,跑到臥鋪車廂門口。王逢賢先生隨著魚貫而出的人群走下車梯。我與先生打過招呼,一手接過旅行袋,一手給高大魁梧的王先生打著傘,走出了火車站。20世紀90年代初的南京已經有出租車了,但是車少人多,根本排不上隊,王先生提議去乘公交,我也只好主隨客便,一同來到31路公交始發站,乘坐頭班車到珠江路,再步行約三公里到南京師大專家樓。一路上雨驟風狂,我仗著自己年輕,也出于對王先生的敬仰之情,盡量把傘撐在他的頭上,王先生緊緊摟著我的肩頭,生怕我被雨淋著了。我們在雨地里高一腳低一腳地走著聊著,那種父子般的感覺真是終生難忘。一把小小的雨傘,根本遮不住我們兩個虎背熊腰的北方大漢,我跟先生渾身都濕透了。走到南山專家樓已經是黎明時分了,我們走進接待大廳,發現魯先生已經在大廳里等候了!我不知道她是坐等了一夜,還是凌晨從劍閣路的家里趕來。見到王先生,魯老師畢恭畢敬地行了一個90度的鞠躬禮,說了一句:“王老師,辛苦了!”這一幕讓我感到震顫。王先生握了握魯老師的手,動情地說:“魯老師,好學生都讓你招來了。”我被二位先生的言行感動得熱淚盈眶,淚水、汗水與雨水交織在了一起。從此,那一幕便深深烙在我的腦海里,經常會浮現出來,尤其是在下雨的時候。
回禮孩子再鞠躬
可能所有的教師都有一種發自肺腑的孩子情結,先生特別喜歡小孩兒。1993年夏季,我博士研究生畢業,留在南京師范大學教科所工作。在魯老師的積極斡旋下,1994年春,愛人從甘肅財經學院調到南師大任教,住房問題也圓滿解決。我的女兒也在先生的過問下,順利地進入了南京實驗幼兒園,后來進入南京瑯琊路小學學習。
女兒四歲時第一次隨母親來南京,我們去拜訪先生,女兒對爸爸的老師全然沒有陌生感,站在門口,朝先生鞠了一躬,奶聲奶氣地喊了聲:“魯奶奶好!”先生優雅地點頭彎腰還了一個鞠躬禮,說道:“小朋友好!請進來吧。”我們走進客廳,先生俯下身來問:“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苗苗。”“是不是爸爸媽媽希望你成為一個優秀的好苗子啊?”女兒搖搖頭說:“不是的,因為我媽媽是苗族,我的名字是姥姥和姥爺給起的,意思就是苗家的孩子。”先生聽聞樂不可支。
所里經常會組織活動以活躍大家的生活,先生總是叮囑我們盡量把孩子家人都一起帶去。孩子們在魯奶奶面前都很開心。女兒一年級時有一次隨我去參加活動。先生問她:“苗苗,你喜歡不喜歡新學校?”女兒回答:“喜歡呀!我們瑯小可好啦!小朋友最喜歡李(敬光)校長了。”“為什么?”“李校長經常來我們一年級教室幫值日生給小朋友盛飯,還跟我們講愛惜糧食的故事,還教我們背誦‘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先生又問:“你喜歡學習嗎?”女兒遲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說:“學習,嗯……喜歡的,但是我不喜歡考試。”先生有點詫異:“為什么?”女兒回答:“因為我每次考完試回到家,爸爸總是不高興,嫌我成績考得不高,所以我就不喜歡考試了。”“這次期中你考了多少分?”“語文(考了)95(分),數學(考了)96(分)。”“考得挺好的呀!”“可是爸爸還嫌我考得不好。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反正我就是不喜歡考試。”我站在一邊忍不住插話:“先生,她們班一半人雙百,95分就是(排名)倒數了。”魯老師笑著對女兒說:“苗苗,你已經很努力了,你回去問問爸爸,在魯奶奶這里考過95分沒有啊?”女兒抬眼望著我,我有點窘迫,轉過頭去,不知說什么好。平素里先生對我們要求比較嚴,所做作業先生都是逐字逐句地批改,而給的等級一般都是B-或B,最多也就是B+,如果換成百分數,也就是80多分。先生的這番話不僅僅是替女兒解圍,也是先生教育觀的一種體現,蘊含著對我們這些弟子的殷切期望。如今,苗苗已經成為一家文化公司的總裁。我們父女倆每每說起魯奶奶,她還是會不無調侃地問我:“爸爸,你從來都沒有正面回答過我,你到底在魯奶奶面前考過95分沒有啊?”一如當年先生的口吻。
秋游時光又“鞠躬”
先生是一個熱愛生活且喜歡大自然的人。教育科學研究所朱小蔓所長和我這個副所長在做工作計劃時,一年三次外出郊游是所里工作的必備項目,并且,先生明確交代,務必要邀請在讀的博士生參加,一個都不能少。1994年秋游時發生的一件小事讓我永生難忘。
在那個被秋風吹黃了樹葉的季節,所里組織大家去蘇州東山旅游。山林公園里游人如織,有的駐足拍照,有的打鬧嬉笑。自由活動的時候,先生在一處花壇旁停了下來,慈愛地看著一個滿頭卷發的小女孩。蹲在一旁的小女孩的媽媽剝開了一塊大白兔奶糖,咬了一小塊喂給了正在蹣跚學步的孩子。可愛的小家伙開心地掉頭朝不遠處的爸爸走去,孩子的媽媽站了起來準備跟過去,那張糖紙像一片樹葉飄落到地上,她全然沒有察覺。先生輕輕地叫住了年輕的媽媽:“同志,你的東西掉了。”對方詫異地回望了先生一眼,又朝著四周打量了一下,下意識地摸了摸隨身挎著的包包。先生走了過去,彎下腰撿起了糖紙—那個彎腰的動作像極了鞠躬的姿勢—順勢拉起那位年輕媽媽的手將糖紙塞給了她,說了一句:“喏,還你。”我和站在一旁的王堅紅老師目睹了這一幕,只見那位女士愣了一下,眼淚流了下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樣的淚水?慚愧,尷尬,內疚,抑或是某種程度的自責?先生的這一舉動令在場的人深受感動,既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先生作為德育人的品格,又讓我領略到先生“送人糖紙,教人環保”的教育藝術。
〔作者系臺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體育學院)院長〕
責任編輯: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