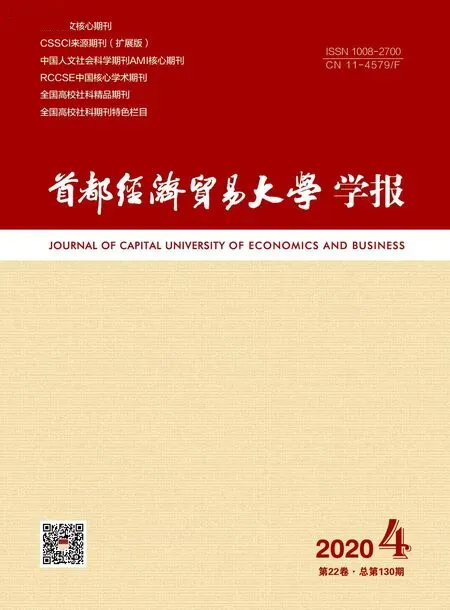“盲目的愛”還是“由愛生恨”?
——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意愿間的調節效應
高 英,袁少鋒
(遼寧大學 a.新華國際商學院;b.商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一、問題提出
城市認同刻畫了個體對某個城市的歸屬感和熱愛程度[1]。對于城市認同,已有研究通常隱含一個假定:培育個體對某個城市的高度認同,是個體融入城市、城市留住個體(尤其是人才)的關鍵[2]。然而,高度的城市認同,在留住人才方面,一定是發揮積極促進作用嗎?本研究基于公平理論的“問責”和“反事實思考”理論觀點[3],建構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之間的邏輯關系,然后考察城市認同在其間的調節效應,基于此回答上述問題。
根據公平理論,在職場,當員工感知到不公平對待時,會先分析其原因,然后進行后續的行為選擇。例如,張三在A城市X公司工作,其每月收入比在B城市Y公司相同崗位的李四要少很多;或者張三感知到在X公司,決定晉升、培訓機會、獎勵等結果分配的制度不合理、不公平。如果張三認為在A城市,即使換一家公司,收入也不會有明顯提高,決定晉升等結果分配的制度也不會有明顯改善,那么張三會選擇離開A城市,去B城市謀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對待。
以上舉例描述了員工的職場不公平感知對其城市逃離的影響。如果某個城市的員工在目前的公司,感知到收入和程序方面的不公平,在進行城市問責(這個城市的企業收入水平、對待員工的方式都差不多),和反事實思考(去別的城市工作會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對待)[3]之后,會形成對目前所在城市的不滿,進而想逃離目前工作的城市,去其他城市尋求更好的發展(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對待)。上述描述,正是刻畫了當前國內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員工,尤其是知識型員工的職業決策過程。知識型員工指的是具有較高學歷(如大專以上學歷),利用知識來進行價值創造的工作者(如程序員、設計師、管理者)[4]。比如,根據第五、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東北近十年來累計流出人口數量超過100萬,其中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生產線骨干力量等知識型員工占了絕大多數[5]。
接下來重點探討,在知識型員工的職場不公平感知、城市不滿與城市逃離意愿之間,城市認同發揮什么樣的調節作用。參考服務營銷領域關于“顧客-企業”關系質量(指顧客對企業的信任和忠誠程度)、在企業服務失敗與顧客報復欲望之間調節作用的研究,城市認同在“不公平感知-城市不滿-城市逃離”之間的調節作用可能存在兩種對立的解釋:“盲目的愛”和“由愛生恨”。前一種解釋是,相比低城市認同的人,高城市認同的個體對感知到的職場不公平更可能表現出包容、諒解或寬恕,進而體驗到相對低的城市不滿和逃離意愿。后一種解釋是,高城市認同意味著個體對城市有強烈的歸屬感和喜愛程度;根據互惠原則,如“我對你好、你也應該好好對我”[6],高城市認同的個體會對該城市有更高的期望;當感知到職場不公平時,相比低城市認同的人,他們更可能進行城市問責和反事實思考,進而引發更強的城市不滿和逃離意愿。
究竟哪一種解釋更符合實際,需要實證檢驗。如果“由愛生恨”的解釋成立,那就意味著高城市認同并不總是有助于城市留人。研究在理論上有助于揭示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知、城市不滿與城市逃離之間的調節效應;實踐上,研究結論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知識型員工吸引與保留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啟示。
二、理論背景與研究假設
(一)職場不公平、城市不滿與城市逃離
根據公平理論,在不公平對待感知與不滿意形成之間,問責和反事實思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7]。
問責涉及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7]:(1)有負面狀態或事件發生,讓個體感知到了損害,個體認為應該有主體對此負責。比如,知識型員工感知到在當前企業所獲得的報酬較低,或者從程序/制度上沒有得到公平對待,覺得自己的付出與回報不對等,認為企業應該對此負責;(2)負面狀態或事件的施加方,本可以采取行動或措施讓個體免除負面狀態或遭遇。比如,知識型員工認為企業本可以給予他們更合理的報酬、制定并實施更公平的程序與制度;(3)個體遭受的負面狀態或事件,被認為違反了特定的規范或倫理道德標準。比如,某企業給知識型員工的報酬相對低,會被認為違反“按勞分配”原則;企業的程序或制度讓知識型員工感知不公平,會被認為違反“尊重人才”、“優勝劣汰”等規范。
當知識型員工覺得其所獲得的報酬相對低,或者感知企業的程序或制度等方面不公平時,會將責任歸為企業一方。但是,如果個體認為“這個城市的企業都這樣”(即在一個特定的城市沒有明顯的不公平感知),而“其他城市的企業不是這樣”,那么個體就會將不公平遭遇的責任歸結到特定的城市上來。例如,在東北地區工作的知識型員工,經常將感知到的不公平歸因為城市[8-9]。
當遭遇負面狀態或事件之后,個體還會進行反事實思考[10],即事情現在是什么樣,如果不按當前的路徑發展,本應該會出現什么不一樣的結果。當知識型員工感知到職場不公平時,個體會思考:企業本應該可以給予其多少報酬,本應該如何制定制度或程序使他們感覺更好。當個體認為某個城市不同企業之間的報酬、制度等相似時,個體還會基于不同城市的比較進行反事實思考,比如個體會認為:如果換在其他城市的相同崗位,本可以掙得更多,得到更好地對待。
公平理論進一步指出,當個體感知到不公平對待時,進行問責或反事實思考后,會先尋求恢復公平的策略,如改變投入或努力程度、調整態度與認知[11]。當恢復公平的策略缺乏時,個體就會作出報復或逃離等關系破壞型的行為反應[12]。比如,面對職場不公平,知識型員工將責任歸到城市后,會先尋求恢復公平的策略。然而,個體相對于城市而言顯然是“弱勢一方”,缺乏獲取恢復公平的策略[12],也難以對城市實施報復,因此個體會作出“逃離”反應。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1:職場不公平感越強,知識型員工的城市逃離意愿越高。
另外,當遭遇職場不公平對待,在個體進行問責和反事實思考后,會激發個體的情緒反應(如不滿、生氣)和后續行為(如離職)[13];而問責和反事實思考,反過來還會強化個體對負面狀態或事件的不公平感知[3],從而進一步激發個體的負面情緒(如不滿意),并進一步影響個體的行為。比如,當某個城市的知識型員工,在感知到職場不公平后,如果將責任歸因為城市,認為是城市的問題導致分配、程序等不公平;或者將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基于不同城市之間的比較進行反事實思考,認為本可以在其它城市掙得更多、得到更合理對待,那么這種不公平感知就會增強,就會進一步激發其對所在城市的不滿意,進而產生逃離行為。因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H2:知識型員工職場不公平感越強,城市不滿程度會越高,由此城市逃離意愿會越高。
(二)城市認同的調節作用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個體的自我概念不僅包括個體身份,還包括社會身份[1]。個體身份由個體獨有的特質構成,社會身份則由群體標簽或會員身份等構成,如性別、種族、地域、宗教信仰、俱樂部身份等。如果個體認同某類群體標簽,就會對該群體形成強烈的歸屬感。城市認同屬于社會身份建構的范疇,反映個體對某個城市的歸屬感和喜愛程度。個體作為常駐城市的一員,通過與所在城市的日常互動,會形成對這座城市的歸屬感或自豪感。這種基于“個體-城市”關聯所建立的社會身份,可提高個體對所在城市的歸屬感和喜愛程度,即提升個體的城市認同。。
在職場不公平感、城市不滿與城市逃離之間,個體的城市認同會發揮調節作用。關于具體的調節方向,存在兩種對立的解釋:“盲目的愛”和“由愛生恨”[14]。
“盲目的愛”指當個體遭遇職場不公平對待時,在其對某個城市進行問責,或基于不同城市的比較進行反事實思考后,如果個體有強烈的城市認同,那么個體更能采取包容態度、諒解或寬恕,從而產生較低的城市不滿和逃離意愿。與之對應,邵建平和李芳紅(2012)基于甘肅地區“核心人才”的調查研究揭示,低“地域認同”是核心人才流失(離開甘肅)的主要原因[15]。由此,提出假設H3a:
假設H3a:相比低城市認同的個體,職場不公平感對高城市認同知識型員工的城市不滿的正向影響效應越弱,進而對其城市逃離的影響也越弱。
“由愛生恨”指當個體遭遇不公平對待時,在對所在城市進行問責、基于不同城市的比較進行反事實思考之后,如果個體有高的城市認同,則會感知到更高的失望和不滿意,并導致更高的城市逃離意愿。因為高城市認同,意味著個體和城市之間有強烈的歸屬和情感依附關系。根據互惠原則[16],如果個體對另一主體有強烈的歸屬或情感依附,則認為對方也應該給予積極回應。由此可知,高城市認同的個體會對所在城市有更高的期望,而當實際的遭遇與個體期望不符時,個體就會更加地不滿意。事實上,兩個主體之間的關系越“親密”,“愛”和“恨”就會變得越強烈,即所謂的“愛之深、恨之切”。據此,高城市認同的個體,在感知到職場不公平后,會產生更高的城市不滿,由此導致更高的城市逃離意愿。據此,提出假設H3b:
假設H3b:相比低城市認同的個體,職場不公平感對高城市認同知識型員工的城市不滿的正向影響效應越強,進而進一步提升其城市逃離意愿。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樣本
鑒于東北地區知識型員工的職場不公平感[8-9]和城市逃離問題均較為突出[5],本研究以東北地區的知識型員工為樣本,檢驗上述研究假設。
問卷收集方式是,在某知名問卷網絡平臺設計好問卷(生成相應調查問卷鏈接),然后依托遼寧某綜合性高校的MBA學員資源開展問卷收集。首先從2016、2017和2018三屆MBA學員中找到配合意愿較強的58位學員,然后通過微信平臺讓他們幫忙填寫,給予每位填寫者6元“微信紅包”作為激勵。之后,再請求這58位MBA學員依托微信平臺等渠道,在他們的同事、朋友中發放并回收調查問卷;并給出對被試和收集的具體要求:(1)目前在東北地區的企業工作;(2)具有大專以上的學歷;(3)幫助收集7份。同樣給予每位被委托的MBA學員42元(6元×7份)“微信紅包”,讓他們轉發給每位問卷填寫者。最后總計獲得調查問卷453份,篩除“目前工作所在的省份”不在東北、填寫時間少于90秒(經測試,90秒內無法有效完成)的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430份。樣本特征見表1。

表1 樣本描述性統計特征
(二) 變量測量
1.城市逃離意愿。根據特里普等(Tripp et al.,2007)[12]、克羅斯利(Crossley, 2009)[17]以及格雷戈等(Grégoire et al. , 2009)[14]的研究, 設計3個題項測量被試的城市逃離意愿: 我再也不想跟我目前所在城市的任何企業(單位) 打交道; 我經常想離開現在的城市, 去其它城市發展; 如果條件許可, 我再也不想來我目前所在的這個城市工作。被試在5點量表上作答,1=“非常不贊同”,5=“非常贊同”。
2.職場不公平感。基于斯維尼和麥克法林(Sweeney & McFarlin, 1993)[18]、魯普和潘澤諾(Rupp & Cropanzano, 2002)[19]、比爾斯(Bies, 2005)[20]等的研究,并參考馬超等(2014)[21]基于中國情境下的實證研究,設計12個題項測量職場不公平感。代表性題項為:與單位內相同工作和職務的同事相比,我所獲得的薪酬(工資、獎金、提成等)待遇是合理的;單位分配制度的制定過程是公開、公平的。被試同樣在5點量表上作答。鑒于題項的內容描述都為“正向描述”,因而如果被試在上述題項上的得分均值越低,表示其職場不公平感知越強。后續數據分析時,為了便于理解,將被試在該變量上的均值進行反向計分處理,即“職場不公平感知”=6-“職場公平感知”。
3.城市不滿。參考格雷戈和費舍爾(Grégoire & Fisher, 2008)[22]關于個體對企業不滿的測量,設計3個題項測量被試對城市的不滿意程度:(1)我目前所在的城市讓我感到不滿意(如城市服務方面);(2)我目前所在的城市讓我感到不滿足(如物質報酬方面);(3)我目前所在的城市讓我感到不開心。
4.城市認同。參考梅爾和艾什福斯(Mael & Ashforth, 1992)[23]關于組織認同的研究,設計城市認同的量表,具體是將描述對象“組織名稱”更換為“城市”。共包含5個題項,代表性題項如:當別人批評我所在城市時,我感覺這也是對我個人的批評。
5.控制變量。鑒于在職場不公平遭遇、城市不滿與逃離意愿之間,個體的自尊水平(個體對自我價值和重要性的總體評價[24])和消極情緒體驗可能產生影響,因此將這兩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自尊的測量,從羅森博格(Rosenberg,1965)[25]的自尊量表中選取4個正向題項和1個反向題項。如:我做事可以和大多數人做的一樣好;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反向命題)。以上潛變量同樣是讓被試在5點量表上作答。
消極情緒體驗的測量,從克勞福德和亨利(Crawford & Henry, 2004)[26]開發的PANAS量表中,選取5個消極情緒詞匯(哀傷的、煩亂的、緊張的、恐懼的、擔心的),詢問被試“在過去的一周內,您在工作與生活方面,感受到相應情緒的頻率”,被試在5點量表上作答(1表示“基本沒有”,5表示“非常多”)。
問卷中還測量了被試的性別、年齡、學歷、職位等級、工作單位性質、工作年限、所屬行業(詳見表1)等基本信息。為了保障被試填寫的認真程度,在問卷的引導語中強調“采用匿名方式填寫”、“答案沒有對錯好壞之分”;此外還參考西奧迪尼(2017)[27]的建議,問卷第一題詢問被試:“您認為自己是一位樂于助人的人嗎?”被試在“是”和“否”之間回答。西奧迪尼[27]認為這樣對被試“先入為主”的角色定位,會顯著提升被試填寫的認真程度。本研究中95.6%的被試選擇了“是”。
此外,為了在源頭上避免同源方差問題,分別將城市逃離、城市不滿和城市認同(子問卷一),職場不公平感(子問卷二),自尊、消極情緒體驗(子問卷三),控制變量(子問卷四),作為不同的子問卷,放在不同的頁面上進行測量。并在引導語強調,問卷包含四個相互獨立、不相干的子問卷。
(三)同源方差檢驗
首先使用哈爾曼單因子程序[28]進行檢驗。基于最大似然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有8個(1)職場不公平感知被分為3個子維度:“分配不公平”、“程序不公平”、“交互不公平”。鑒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城市不滿與城市逃離間的調節效應,后續分析將職場不公平感作為一個單一構念進行分析。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被提煉出來,其中第一個因子的初始方差解釋率為25.82%。參考利文斯通等(Livingstone et al., 1997)[29]的研究,認為本研究的同源方差問題并不明顯。
進一步參考哈里斯和莫斯霍爾德(Harris & Mossholder, 1996)[30]的做法,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CFA)對比檢驗8因子模型(城市逃離、城市認同、城市不滿、職場不公平感3個維度、自尊、消極情緒體驗)和單因子模型的擬合情況。基于LISREL8.7進行的CFA結果顯示,八因子模型擬合結果(χ2=1188.39,df=467,RMSEA=0.06;NFI=0.94、NNFI=0.96、CFI=0.96)明顯優于單因子模型的擬合結果(χ2=8766.02,df=495,RMSEA=0.197;NFI=0.68、NNFI=0.68、CFI=0.70)。以上分析結果意味著,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同源方差問題。
(四)信、效度檢驗
1.信度。通過克倫巴赫α信度系數和CR組合信度考查本研究涉及潛變量的信度。本研究關注的6個潛變量的α信度系數分別為:城市逃離0.81、城市認同0.84、城市不滿0.81、職場不公平感0.93、自尊0.86、消極情緒體驗0.83;組合信度分別為:0.82、0.84、0.80、0.94、0.86、0.84;均大于0.8,說明本研究涉及潛變量的測量具有很高的信度[31]。
2.內容效度。為了保證題項測量的內容效度,在問卷設計好之后,邀請5位企業員工進行試填,讓他們就問卷各題項涉及語句的易懂性、可讀性等提出看法和修改意見,之后對5位試填者的意見逐條進行檢查和修改。保障問卷涉及題項的內容效度。
3.收斂效度。通過各潛變量對應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平均方差提取量(AVE)檢驗測量的收斂效度。基于LISREL8.7的CFA結果顯示,研究涉及的6個潛變量對應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介于0.59~0.92之間,對應的p值都小于0.001;6個潛變量AVE值分別為:城市逃離0.61、城市認同0.52、城市不滿0.58、職場不公平感知0.58、自尊0.56、消極情緒0.51,均大于0.5的臨界值。以上兩方面指標分析結果表明,本研究涉及的6個潛變量均具有可接受的收斂效度。
4.區別效度。參考福內爾和拉克爾(Fornell & Larcker, 1981)[32]推薦的方法檢驗6個潛變量的區別效度。如果某潛變量AVE值的平方根小于兩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則說明兩潛變量之間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本研究6個潛變量的AVE值的平方根介于0.71~0.78;相關系數值介于0.05~0.57(詳見表2)。以上指標表明本研究涉及的潛變量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
四、實證分析與假設檢驗
本研究中6個潛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見表2。職場不公平感(r=0.34,p<0.01)同城市逃離意愿顯著正相關,這初步支持了假設H1。另外,職場不公平感還與城市不滿顯著正相關,城市不滿同城市逃離顯著正相關。調節變量(城市認同)與自變量(職場不公平感)以及因變量(城市逃離)只有較弱的相關關系。各潛變量的兩兩相關系數絕大部分小于0.5,意味著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2 潛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Pearson相關系數
(一)主效應檢驗
通過多元回歸分析,檢驗H1涉及的主效應。先根據被試“工作單位性質”生成4個虛擬變量:是否國有、是否民營、是否外資、是否機關事業單位;再根據“所屬行業”生成兩個虛擬變量:是否現代服務業、是否制造業;虛擬變量的賦值都是“1代表是、0代表否”。因為被試的工作單位性質不同、所屬行業不同,所感知的職場不公平程度可能存在差異,進而導致不同的城市滿意度和逃離意愿。需要將這些虛擬變量也放入多元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見表3。

表3 預測城市不滿和城市逃離意愿的標準化回歸分析結果
表3模型1中只考慮了控制變量對因變量城市逃離的影響,結果表明潛在干擾變量自尊(β=-0.127,p<0.01)和消極情緒體驗(β=0.237,p<0.001)對知識型員工的城市逃離意愿有顯著影響,但總體上模型的解釋能力非常有限(R2為9.5%)。模型2中加入了職場不公平感變量后,模型的解釋能力顯著提升(R2增加到17.3%)。職場不公平感(β=0.298,p<0.001)對城市逃離意愿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這支持了假設H1。意味著在控制了被試性別、年齡、學歷、自尊、消極情緒體驗等控制變量之后,知識型員工的職場不公平感越強,其城市逃離意愿越高。
(二)中介效應檢驗
采用巴龍和肯尼(Baron & Kenny, 1986)[33]的三步回歸法,檢驗“城市不滿”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意愿之間的潛在中介效應,檢驗假設H2。第一步,表3模型2表明,自變量(職場不公平感)對因變量(城市逃離意愿)存在顯著正向影響。第二步,模型4表明,自變量對中介變量(城市不滿)亦存在顯著正向影響。第三步,模型3表明,當將中介變量加入回歸模型和原自變量一起作對因變量的回歸時,中介變量城市不滿對城市逃離意愿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β=0.505,p<0.001;但自變量職場不公平感對城市逃離的回歸系數由模型2的0.298(p<0.001)降至模型3的0.134(p=0.002)。根據溫忠麟等[34]的判定標準,城市不滿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之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這支持了假設H2,即知識型員工的職場不公平感越強,越可能激發其城市不滿,并進一步提升其城市逃離意愿。
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進一步用布雷切和海耶斯(Preacher & Hayes, 2004)[35]等開發的方法檢驗城市不滿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之間的中介效應。將重抽樣次數設定為5000,運行布雷切和海耶斯(2004)[35]建議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結果表明: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之間,城市不滿的中介效應位于0.1485至0.2937之間(95%置信區間),不包含0,結果再次支持假設H2。
(三)調節效應檢驗
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并便于結果的解釋,先將自變量(職場不公平感)、調節變量(城市認同)進行標準化轉換,再生成自變量和調節變量的交乘項,做自變量、調節變量以及二者交乘項對因變量的回歸。表3模型5揭示,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不滿之間,城市認同的正向調節效應臨界顯著,交乘項“Z職場不公平× Z城市認同”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087,p=0.058。
為進一步檢驗調節效應的可靠性、并揭示具體的調節方向,還采用簡單斜線分析,檢驗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不滿之間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職場不公平感和城市認同對城市不滿的交互效應顯著,交乘項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093,p=0.041;當調節變量“城市認同”取值在均值的一個標準差以上時,職場不公平感對城市不滿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432,p<0.001;當城市認同取值在均值的一個標準差以下時,職場不公平感對城市不滿的標準化回歸系數β=0.265,p<0.001。調節效應如圖1所示。
以上結果支持“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不滿之間“由愛生恨”的調節解釋邏輯,即支持假設H3b;相比低城市認同的知識型員工,職場不公平感越強,對高城市認同個體的城市不滿的正向影響效應越強。
(四)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根據以上結果,進一步檢驗“職場不公平感-城市逃離意愿”之間,城市認同、城市不滿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是否顯著。具體參考穆勒等(Muller et al., 2005) 提出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36],進行檢驗。具體涉及如下三個方程(Y為因變量、X為自變量、Mo為調節變量、Me為中介變量):
Y=β40+β41X+β42Mo+β43XMo+ ε4
(1)
Me=β50+β51X+β52Mo+β53XMo+ ε5
(2)
Y=β60+β61X+β62Mo+β63XMo+β64Me+β65MeMo+ε6
(3)
穆勒等(2005)[36]認為,首先,方程(1)中β41顯著不等于零,β43則沒有要求一定是要顯著不等于零;其次,方程(2)和方程(3)中,需要滿足如下兩個條件中的一個(或兩個都同時滿足):(1)β53和β64都顯著;(2)β51和β65都顯著。如果以上條件滿足,則可認為有調節的中介效應(β64β53+β65β51)是顯著不等于零的。
本研究因變量Y是“城市逃離”、自變量X是“職場不公平感”、中介變量Me是“城市不滿”、調節變量Mo是“城市認同”;做方程(1)對應的回歸分析,β41=0.318,p<0.001;做方程(2)對應的回歸,β53=0.093,p=0.041;β51=0.348,p<0.001;做方程(3)對應的回歸,β64=0.501,p<0.001;β65=0.162,p<0.001。滿足穆勒等(2005)[36]提出的條件,據此可以認為,在職場不公平感與城市逃離之間,城市認同、城市不滿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β64β53+β65β51)顯著不等于零。再結合假設H2檢驗結果和圖1所示調節效應的分析結果,可以認為,相比低城市認同的知識型員工,職場不公平感越強,對高城市認同個體的城市不滿的正向影響效應越強,這會進一步驅動他們產生更高的城市逃離意愿。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第一,本文揭示了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城市不滿-城市逃離意愿”邏輯關系間“由愛生恨”的調節效應。關于城市認同的已有研究,都假定培育高的城市認同,有助于員工融入城市、留在某個城市安心工作。這一邏輯內在的假定是,城市認同會發揮“盲目的愛”的調節作用,即個體在對某個城市產生較強的歸屬與熱愛之后,更可能包容在這個城市感知到的不足(如收入水平比國內同行低)。然而,城市認同還可能發揮“由愛生恨”的調節作用,即個體在對某個城市產生較強的歸屬與熱愛之后,一旦體驗到這個城市的某種不足,更可能產生“愛之深、恨之切”的情緒與行為意向。本研究基于430個東北地區知識型員工樣本的實證檢驗,揭示了城市認同的“由愛生恨”調節效應:相比低城市認同的知識型員工,職場不公平感越強,對高城市認同知識型員工的城市不滿有更顯著的促進效應;另外,在“職場不公平感-城市逃離意愿”之間,城市認同和城市不滿發揮顯著的有調節的中介效應,即相比低城市認同的個體,職場不公平感知越強,對高城市認同的知識型員工城市不滿的促進效應越強,由此進一步提升其城市逃離意愿。這意味著,在存在職場不公平的情形下,培育高的城市認同不僅不會助力知識型員工留下,反而會驅使其逃離特定的城市。
第二,本文從微觀個體的層面,拓展了已有文獻關于知識型員工為什么逃離經濟欠發達地區(比如東北地區)的原因解釋。已有研究較多從宏觀產業經濟結構、體制機制、思想觀念、發展動能的角度[5,37,39],解釋為什么知識型員工逃離。本研究揭示,個體在職場體驗到分配或程序方面的不公平后,如果進行城市問責(即認為城市的原因造成分配或程序上的不公平)和反事實思考(即認為去別的城市可能得到更好的報酬和對待),就會提升個體的城市不滿,進而激發知識型員工的城市逃離意愿;并且個體的城市認同會強化職場不公平感對城市不滿和城市逃離的正向影響效應。
第三,本文還拓展了已有文獻關于個體逃離決策的已有認知。已有研究主要探討了“員工-組織”雇傭關系中的逃離(即離職行為),“顧客-企業”服務關系中的逃離(即顧客流失行為),以及“個體-個體”合作或親密關系中的逃離(即人際關系破裂);鮮有研究關注“個體-城市”關系中的逃離。本研究從職場不公平感知出發,探討并揭示了知識型員工個體在與城市交互關系中的逃離決策機制。
(二)管理啟示
本研究的結論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政府和企業具有管理啟示。
對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在存在職場分配或程序不公平的情形下,一味地強調培育人才的城市認同,并不是留住人才的有效策略,實際可能起到反作用。城市認同越高的知識型員工,對所在城市有更高的期待;當在該城市感知到職場不公平,并進行城市問責(認為城市的問題造成分配或程序不公平)和基于城市之間比較的反事實思考(認為去其他城市會獲得更好的收入和對待)后,更可能激發其對所在城市的“恨”,由此導致其逃離所在城市,去別的城市尋求更高報酬和更好對待。為此,希望通過城市認同的培育留住人才的城市,還需要不斷提升城市發展水平,提升員工在某個城市的總體收入水平(提升分配公平),打造重視人才、尊重人才的軟環境(提升程序公平)。一個城市想要長期有效留住人才,需要高城市認同和高職場公平的共同作用。
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城市和企業管理者而言,需要知道,除了宏觀層面的產業結構、“體制機制”或者“思想觀念”外,知識型員工在職場關于分配、以及決定分配的組織制度與程序的公平感知,是城市與企業引人、留人的關鍵。因此,除了城市層面的引人、留人激勵政策與措施外,努力提升一個城市的企業管理水平,尤其是提升企業在分配(報酬、晉升、發展機會等結果維度)或程序(決定報酬、晉升、機會等分配的制度與流程)方面的公平水平,同樣對企業與城市引人、留人至關重要。
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對于知識型員工流失問題突出的企業(如眾多東北企業),尤其需要分析企業在程序方面是否有突出的不公平問題,比如“低能之人”依靠“裙帶”、“關系”等獲得相對高的報酬或更好的對待。這樣的不公平,尤其容易引發知識型員工的職場不公平感知。一旦知識型員工,認為某個城市的企業“都是這樣”時(城市問責),就會產生城市不滿,進而激發城市逃離意愿和行為。只有創造“能者上、庸者下”,“多付出、多回報”的程序公平環境,才能促進企業和城市的引人與留人。
如果某個企業認為在結果分配、制度與程序方面,在城市(如東北城市)內的不同企業之間相對公平,但與其他城市(如東南沿海城市)相比不公平,此時,企業或政府相關部門可考慮圍繞本城市占有比較優勢的“成本因素”(比如東北城市的居民生活成本、房價等顯著低于東南沿海城市),強化知識型員工對所在城市生活工作相對低成本的認知,從而提升知識型員工的公平感知,促進其留下。
(三)研究局限與未來研究展望
本研究還存在如下局限:(1)為了有效獲取足夠數量的知識型員工樣本,本研究主要立足遼寧某綜合性高校的MBA學員以及MBA學員的工作圈展開樣本收集;雖然所獲得的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如果深入各類企業、進行更廣泛的樣本采集,可能更有助于保障研究結論的外部效度。(2)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考察了職場不公平感對知識型員工城市不滿、城市逃離的影響效應和作用機制;鑒于調查問卷方式本身是關系型設計,這一方法并不能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采用行為實驗研究方法,操縱分配、程序公平變量,然后考察其對員工城市滿意度、逃離意愿的影響,更有助于揭示其中的因果關系和作用機制。(3)鑒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城市認同在職場不公平感、城市不滿和城市逃離之間的調節效應,關于職場不公平感知干預對知識型員工城市不滿和逃離的影響缺乏探討。比如,對于分配感知不公平的員工,如果強化他們對“低城市生活成本”的認知,會不會逆轉他們的不公平感,進而減緩不公平感對城市不滿和逃離的影響效應,值得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