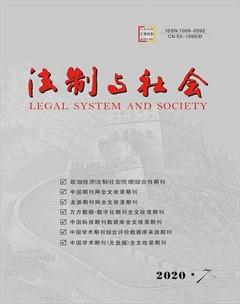有聲讀物的法律定性與著作權(quán)保護路徑
關鍵詞 有聲讀物 演繹作品 獨創(chuàng)性
作者簡介:周東來,南京理工大學知識產(chǎn)權(quán)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3.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182
隨著信息網(wǎng)絡技術(shù)、智能化科技的迅速發(fā)展,數(shù)字閱讀行業(yè)也處在一個快速發(fā)展的階段。而有聲讀物能夠很好的適應多種數(shù)字化閱讀場景,更能符合當代快節(jié)奏生活的需求,在數(shù)字閱讀行業(yè)中的發(fā)展情況尤為引人注目。在有聲讀物產(chǎn)業(yè)發(fā)展形勢大好的背景下,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案件也頻頻發(fā)生。經(jīng)過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的檢索,至2019年6月1日為止,全國有聲讀物涉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案件生效的裁判文書就達到178件。除此之外,還有大量通過訴訟外協(xié)議和解方式解決的侵權(quán)糾紛。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一來是有聲讀物產(chǎn)業(yè)自身產(chǎn)業(yè)鏈條長、授權(quán)環(huán)節(jié)多,內(nèi)容比對不易等性質(zhì),使其維權(quán)困難,易構(gòu)成侵權(quán);二來是由于有聲讀物的法律定性不明,易導致授權(quán)不清,從而導致當事人在借用法律手段保護相應權(quán)利之時存在著較大障礙。因此下面就有聲讀物的法律定性問題以及不同類型的有聲讀物如何保護的問題上進行簡單的分析。
一、有聲讀物的法律定性
想要將有聲讀物的概念準確地確定下來,無疑是困難的。從載體來講,隨著科學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有聲讀物的載體也一直在改變之中,但無論是哪一種載體,最后呈現(xiàn)的都應該是一種音頻形式,是一種錄音制品。從內(nèi)容上講,有人將有聲讀物簡單地界定為有聲書即一定要在書籍的基礎上 ,筆者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狹隘。有聲讀物可以是主要以書籍內(nèi)容為基礎的音頻也可以是原創(chuàng)性的新作品。而對于首次便以口頭方式表達出來的作品,只要達到作品所要求的獨創(chuàng)性,便可清楚地認定為口述作品進行保護。故而,在本文中,主要討論的有聲讀物指的是一類以書籍內(nèi)容為基礎的制作的錄音制品。
要探討有聲讀物的法律定性問題,最為關鍵的是看其內(nèi)容是否具有獨創(chuàng)性。
(一)有聲讀物獨創(chuàng)性認定時考慮的因素
獨創(chuàng)性是作品的實質(zhì)構(gòu)成要件,我國雖未在立法上對獨創(chuàng)性進行明確的界定,但一般認為獨創(chuàng)性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創(chuàng)作過程的獨立性,一個是創(chuàng)作結(jié)果具有一定程度的個性,即作品應當是具有某種屬于作者本人特有的東西,如語言和邏輯、選擇和編排等 。具體到有聲讀物,它的獨創(chuàng)性就一定是相較于原作品要有明顯的特征,而這種對于原作品改變的程度,在什么程度上是改編而在什么程度上應認定為復制呢?筆者認為,可以先從影響有聲讀物獨創(chuàng)性的相關因素入手。
從原書到有聲作品的轉(zhuǎn)換形式來看。現(xiàn)在市面上的有聲讀物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制作模式,一種是由人聲經(jīng)過朗讀、錄音之后形成的有聲讀物,另一種是由機器或是AI進行智能閱讀的模式制作而成的有聲讀物。前一種類型,因其將原始文字,通過朗讀者的演繹,加上后期可能會對文本進行編排和添加各種音效,所以有可能夠成演繹作品。而后一種類型往往只是單純將文字轉(zhuǎn)換為數(shù)字音頻,不存在對于原作品的任何改動和變動,因而只是對于原作品的復制。
從有聲讀物的時長來看,著作權(quán)意義上的作品雖然沒有時長的限制,但時長越短,對于其獨創(chuàng)性的認定就越困難,時長過短會導致其能夠進行個性表達的選擇空間變得狹窄,使得表達趨于相同,從而降低獨創(chuàng)性的可能 。
從在有聲讀物中添加的其他元素來看。筆者認為這些音效、音樂的添加固然是對原作品作出了一些改變,但要看其運用編排是否達到了形成新作品的程度,才能認定其獨創(chuàng)性。就比如在文字作品中添加上插畫,并不代表著就會形成新的作品,而是原作者和插畫作者就其文字作品和繪畫作品分別享有著作權(quán)。
(二)有聲讀物構(gòu)成演繹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標準
有聲讀物是否構(gòu)成演繹作品,是實務界討論得最為廣泛的一個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從復制行為與演繹行為定義的區(qū)別與有聲讀物的制作過程兩方面來確定。
首先,雖然學界對于演繹行為和復制行為的區(qū)分沒有一個準確地界定,但一般認為演繹作品應當具有以下特定:第一,演繹作品對已有作品的依賴性很大,并保留了原作品具有的獨創(chuàng)性特征;第二,演繹作品必須體現(xiàn)某種獨創(chuàng)性。演繹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體現(xiàn)在其與原作品的區(qū)別上,也體現(xiàn)在其添加的元素是否能夠體現(xiàn)出創(chuàng)造性勞動上。
其次,從制作過程來說,一般的有聲讀物是由自然人朗讀之后,進行錄制,再通過后期制作形成的。對于朗讀行為,根據(jù)前文所知演繹作品應當在保留原作品具有的獨創(chuàng)性特征且對原作品的改變體現(xiàn)了新的獨創(chuàng)性。朗讀行為是人人皆可進行的行為,即便是因語音語調(diào)差別會有所不同,但在未改變文本內(nèi)容的前提下,并未對原作進行重大改變,無非是改變了一種形式載體,其區(qū)別的實質(zhì)與紙質(zhì)書籍和電子書籍間的區(qū)別是相近似的。因而,不能認定朗讀行為便是創(chuàng)作行為。對于錄音行為,錄音行為沒有任何獨創(chuàng)性體現(xiàn)之處,應當屬于復制行為。根據(jù)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規(guī)定,錄音行為也是復制的形式之一。對于后期制作的行為,前文也已說明,要看其運用編排是否達到了形成新作品的程度。
由此可見,有聲讀物是否構(gòu)成演繹作品的標準是其內(nèi)容是否構(gòu)成了對原作品的演繹。在司法實務中,法院也因涉案有聲讀物與原文字作品在內(nèi)容和表達上沒有改變而對該有聲讀物認定為原作品以錄音制品形式存在的復制品 。
二、有聲讀物的著作權(quán)保護路徑
根據(jù)有聲讀物的法律定性不同,應當選擇不同的著作權(quán)保護路徑進行保護。
(一) 構(gòu)成演繹作品的有聲讀物
對此類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的保護,可以根據(jù)一般演繹作品的保護模式進行保護。其涉及到的權(quán)利主體,包括原作品作者,有聲讀物制作者(包括作為表演者的朗讀者)以及有聲讀物的運營平臺。為避免互相之間的侵權(quán),三者之間應當以合同進行有效的授權(quán),即有聲讀物制作者在進行改編制作時應當獲得原作品作者的授權(quán),而有聲讀物運營平臺對其進行網(wǎng)絡傳播的過程中應當獲得原作品作者和有聲讀物制作者的雙重授權(quán)。其授權(quán)的范圍主要是改編權(quán)、復制權(quán)和信息網(wǎng)絡傳播權(quán)。
(二)作為原作品復制件的有聲讀物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有聲讀物的保護主要包括錄音制品制作者權(quán)和表演者權(quán)兩方面。
根據(jù)我國《著作權(quán)法實施條例》的規(guī)定,錄音制品指的是“任何對表演的聲音或其他聲音的錄制品”,因此,將文字作品轉(zhuǎn)化成有聲讀物一般都可界定為是錄音制品。而對于錄音制品的制作者相應的享有錄音制作者權(quán),要注意的是,根據(jù)國務院頒布的《音像制品管理條例》中規(guī)定,取得了相應許可的單位或個人才能作為錄音制作者取得錄音制作者權(quán)。普通的用戶自制的有聲讀物,可能不享有錄音制作權(quán)。
朗讀是一種表演行為,因此朗讀者自然能夠獲得表演者權(quán)的保護。這也意味著那些個人制作上傳的有聲讀物可以因表演者權(quán)而受到相應的保護。
(三)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保護的具體路徑選擇
在前文中,筆者已經(jīng)說明,根據(jù)有聲讀物的性質(zhì),對其進行保護,但是在實踐中最為關鍵的還是如何構(gòu)建一個有效、便捷的保護模式,也就是一個具體的著作權(quán)保護路徑。
我國學界對于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保護的具體路徑構(gòu)建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tǒng)的合作模式,即原作品作者與有聲讀物內(nèi)容制作者相合作,原作者將作品的相關權(quán)利許可給有聲讀物制作者使用,有聲讀物制作者在制作完成后再將其上傳到合作的運營平臺上,更多的時候運營平臺和內(nèi)容制作者為同一組織,這也就減少了許可授權(quán)的困難,避免了侵權(quán)糾紛。這種傳統(tǒng)的“點對點”模式,顯然存在著效率不高等缺點,而且在網(wǎng)絡時代,是否能夠直接知道作品的原作者進行授權(quán)也是一大難題。除此之外,在原作者簽訂許可合同時,往往是會收取高額的一次性的許可費,而這個高額的許可費使得有聲讀物服務商不得不將這成本轉(zhuǎn)嫁到消費者身上。因此,若要堅持該種模式,就應當完善授權(quán)方式,平衡兩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方式 。
另一種模式是借用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對有聲讀物進行保護。根據(jù)著作權(quán)自動取得的特點,再加上信息網(wǎng)絡技術(shù)發(fā)展使得著作權(quán)侵權(quán)變得更為容易,著作權(quán)個人想要去維權(quán)顯得越發(fā)的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的地位就顯得尤為重要。雖然我國的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還存在諸多的問題和不足,但不可否認,利用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進行有聲讀物的保護依舊有著其天然的優(yōu)勢。首先,對于一個既包含著文字內(nèi)容的朗讀音頻又包含著各種背景音樂的有聲讀物來說,分別向中國文字著作權(quán)協(xié)會和中國音樂著作權(quán)進行大批量的快捷授權(quán),可以大大節(jié)約授權(quán)的時間成本;其次,隨著有聲讀物行業(yè)的不斷發(fā)展,建立一個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管理集體組織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在2014年,由多個單位共同組建的中國聽書作品反盜版聯(lián)盟便已經(jīng)成立,可以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數(shù)字化、一體化的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管理集體組織,以此來解決授權(quán)許可、利益分配、侵權(quán)救濟、防盜版的技術(shù)措施革新等等問題,以更加便捷和高效地為有聲讀物提供保護 。
三、結(jié)語
有聲讀物作為一種新的閱讀模式,滿足了多場景閱讀和適應碎片化閱讀的數(shù)字閱讀發(fā)展趨勢,行業(yè)發(fā)展前景廣闊。但在行業(yè)迅速發(fā)展的背景下,侵權(quán)糾紛也是頻頻發(fā)生,這與有聲讀物的種類繁多,無法統(tǒng)一定性有一定的關系。但通過有聲讀物的內(nèi)容是否完全“照搬”原作品,可大致將有聲讀物定性為以錄音制品形式存在的原作品的復制件以及演繹作品兩種法律性質(zhì)。而根據(jù)有聲讀物這兩種不同的法律性質(zhì),在選擇保護路徑上略有區(qū)別,從更加具體的層面講,構(gòu)建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管理組織對其進行保護和管理最為有效。
注釋:
趙俊卿.有聲讀物的發(fā)展現(xiàn)狀及其問題[J].今傳媒,2016, 24(6):40-42.
張今.著作權(quán)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4.
王坤.論作品的獨創(chuàng)性——以對作品概念的科學建構(gòu)為分析起點[J].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4(4):15-22.
張書青.“有聲讀物”涉著作權(quán)若干問題淺析[J].法律適用(司法案例),2018, 415(22):70-78.
賀言.有聲讀物中涉及的著作權(quán)問題研究[D].云南大學,2016.
冷協(xié)凡.有聲讀物著作權(quán)保護探究[D].華南理工大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