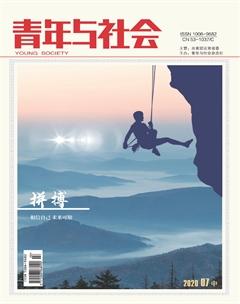莊子“渾沌”的哲學意蘊探析
摘 要:“渾沌”在《山海經》中被描述為遠古時期的一個神話生物,隨著文明的逐漸演進,其在莊子這里已經上升為了一個哲學概念,可以說“渾沌”一詞在莊子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莊子通過“渾沌之死”的寓言隱喻著其對于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哲學思考,作為對于他那個時代問題的回應,如何去更好地“應帝王”,復歸于渾沌之境,期望讓人們生活在與自然界萬物無礙的“至德之世”中,是莊子留給“人間世”的回答。莊子注意到了君王的過度有為將導致文明的異化,但其將人性僅僅理解為前文明形態下的自然之性,主觀上消解了人的目的性,顯然有其局限性。
關鍵詞:莊子;渾沌;哲學意蘊;局限性
一、“渾沌”與莊子哲學
提到“渾沌”,通常給人的印象是雜亂無章、渾渾濁濁、萬物未化的一種存在狀態,《山海經·西山經》說:“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實為帝江也。”在西方三百五十里處有個名字叫天山的地方,有一個初始的神靈,它的名字叫做“渾敦(沌)”,其形狀如黃色的卵囊一般,顏色紅得像丹火,有六只腳和四個翅膀,沒有面部形態,但是能歌善舞,如同人類一般歡呼跳躍。這個形象實在是世間罕見,樣貌奇特,前所未有。對于這樣一種初始的“渾沌”意象,后代的學者均從不同角度來解讀其精神內蘊,例如,何新把太陽看作“渾沌”的原型,蕭兵、葉舒憲則認為在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上,是人們對于“黃氣”、“黃云”、“黃精”的印象構成了“渾沌”的原型,龐樸則把“牛皮渡筏”這種涉水工具看作“渾沌”的原型,大家對于“渾沌”原型的推論雖然各有不同,但不難看出他們立足的出發點都是從“渾沌(敦)”的外在形象和色彩方面去探尋“渾沌”原型的。但他們忽略了一點,若從其“識歌舞”的角度來看,其實折射出原始先民們對于理想生活狀態和理想生活環境的向往之情。人類由大自然孕育而生,依賴著大自然,囿于當時生產力水平的低下,當人類面對外部自然環境的挑戰時,應對的能力相對較弱,因此面對大自然的優勝劣汰法則,會本能地向往一種和諧、穩定、富足、安樂的生存環境。
隨著人類文明的逐漸進步,“渾沌”的意象也在逐漸發展和變化,到了莊子這里,具象化的“渾沌”已經被轉化成了哲學化的“渾沌”,“渾沌”不單單在莊子思想中處于“核心詞匯”,乃至在道家哲學中也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莊子以其瀟灑恣肆的獨特敘事方式,賦予了“渾沌”十分豐富的內涵,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其哲學意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道”的形上意義所等同。在莊子思想深處,“渾沌”逐漸演變著,最終被抽象化,它呈現出一種蒙昧的、無序的、雜亂無章的初始狀態,其作為宇宙的核心,后世的萬物均自此開始,由此而生,“渾沌”在莊子這里已被視為“萬物之母”,其與老子所說的“道”可以說是異流而同源,因此在莊子這里,“渾沌”具有了一種本體論的意義。老子《道德經》第25章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所描述的狀態和莊子“渾沌”意象可以說是異曲而同工。美國學者吉拉道特針對于道家哲學的“渾沌”狀態做過分析,他認為老子和莊子專門把“混”來加以突出強調,將其與“道”等同,老莊把“混”視為萬物初始的根源、原則,那是類似于一種未知的神秘主義的力量,“道生萬物”描繪出一種近乎完美的、所有事物混合為一的階段。其對于“渾沌”的理解可以說是切中肯綮,在道家哲學的概念中,“渾沌”在邏輯上來說是一種先于宇宙生成階段的狀態,是一種處于完滿的、整體的、所有事物混成為一的“道”的階段,宇宙萬物的生命均從此蘊發生機,逐漸生成、生長、發展、變化,由生至死,由死重生,循環往復,以至無窮。此種狀態是一種大生命的“全包蘊”,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初始根源和至上原則,所以說“渾沌”隱喻著莊子所認同的原始秩序,此種秩序以智慧未開、是非之爭尚未展開為前提。
《莊子》中“渾沌之死”的寓言可以說是廣為人知,在內七篇的最后一篇《應帝王》中,莊子以這樣一則寓言作為其思想體系的結束語,可以說是頗有深意,憨山德清大師曾說,倏忽、渾沌這一章節的意義,不僅僅是作為《應帝王》此單篇的結束段落,在整體上來說,它其實還總結了內七篇的主旨大意。“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傳達出匆忙急切之意,“忽”則表現為快捷迅速的狀態,二者均隱喻積極有為,或快捷匆忙地從事某種活動,與之相對的則是“渾沌”。歷來注家和學者對于此寓言的解讀都各有新意,分歧之處也一直存在,從此寓言的表層意思來看:正是倏忽二帝所象征的“有為”或“智巧”,是導致中央之帝—“渾沌”被迫死亡的直接原因。若從整體上把握莊子的思想主旨,則可以總結出“渾沌”象征著天、無為、自然、無心或道這些哲學意蘊。《莊子》全書也隱隱投射出莊子及其后學對渾沌之境的無限向往和汲汲復歸,但現實終歸是現實,渾沌最終卻無法逃脫被穿鑿致死的悲慘結局,這是現實層面在莊子思想深處的映射,如何在哲學層面給予現實困惑以關懷,如何進行價值的重構,是莊子所要思考的問題,因而莊子思想的主題就以如何復歸于渾沌之境而徐徐展開。由此可見,“渾沌”在莊子思想中處于極其重要的位置。
渾沌作為“中央之帝”,其地位的尊貴性與重要性和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央”一詞很早就被人們所使用,如《詩·秦風·蒹葭》:“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就用來指代位于中間的地方,而后人們逐漸賦予其重要的、特殊的象征含義,如土之于五行、宮之于五音、黃之于五色、甘之于五味,五之于九數,都位于其所處的“中央”位置。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央位于東南西北之中,古人對于天下的空間想象即是如此,構成了以地理上的“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從政治權力的角度看,古代帝王要想頒布法令、統御四方,通常也是以“中央”的名義進行;從生物學的意義上來說,中央也可視為“生命之本”,如心臟之于人體,因為心臟位于人體之中央,中央也可看作“力量之源”,因為心臟為人的全身輸送血液,人的生命才能夠得以維持下去。因此,作為地處“中央”的“渾沌之帝”,渾沌被鑿穿而死則意味著中心的喪失,可以看出莊子所要提倡的是去地方中心主義和去人類中心主義,他要從“道”的層面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解構。當眾人都以“我”的角度去行事時,莊子卻冷眼觀之,他意識到人要從“自我”中心的視野中超脫出來,只有合“道”的視角去觀照萬物,才能真正做到“不敖倪于萬物”。此外“渾沌”還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吉拉道特就曾指出,渾沌不單單是一個名詞,還是一種方法,莊子為我們指明了一條如何看待世界的通道。莊子把“渾沌”的外在展現形式稱為“環中”,他從“環中”的角度來超越“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齊物論》)“環中”其實就是“以道觀之”的同義詞,王夫之就認為“環中”二字可以包繞住莊子的思想整體。可以說,莊子告訴了我們看待世界的一種新的方式,應從萬物的角度去觀照萬物,超越自身的狹隘,才能呈現出一個物無貴賤、萬物平等的和諧世界。
二、“渾沌”的哲學隱喻
(一)“渾沌”隱喻著“去主體性”
哲學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與哲學家所處時代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緊密相連,當哲學家給予此問題以哲學關懷進行價值重構時,那便是人文理性的回歸。先秦時期是社會最為動蕩,戰爭最為頻繁的時代,諸侯國之間不斷地兼地、攻伐,社會十分不安定,此時的中華大地上正經歷著前所未有、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莊子同老子一樣,當看到社會的亂象再結合自身的切實經歷時,作為那個時代的“先知”與高級知識分子,他們都會自主地去探尋導致“社會動亂”與“生存困境”的深層次原因,尋求一條救治之道。
《應帝王》篇的主題是探討如何運用真正的政治智慧去治理天下的,莊子對儒家所提倡的“圣人之治”提出了批判,同時提出了自己所向往的“明王之治”,當儒家以“帝道”、“王道”為政教典范大加弘揚時,莊子已經注意到這種政治形態后面所潛藏的危機,莊子正是要將“帝王”的亂為進行解構,以期能夠復歸于“渾沌之境”,期望人們都在“至德之世”和“無何有之鄉”的世界中美好地生活。正如王博教授所說:“在政治意義上,帝王只有一個;但是在生命的意義上,每個人都可以是帝王。”[]莊子生活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事實上,正是倏與忽的“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造成了渾沌之死,而莊子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正是那個可見天地之純、道術不為天下裂的渾沌之地。在天下崩壞、“渾沌”已分化的背景下,如何以合適方式去治理是莊子所思考的問題。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莊子所理想的狀態是合乎本然、合乎天性的“渾沌”之境,在理想狀態已逝的形態下,問題便表現為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回歸原初狀態。由放棄、拒絕文明形態下直接的功利性目的追求,莊子同時進一步表現出對廣義上人類意圖的消解。就政治哲學而言,“渾沌之死”意味著理想存在狀態的結束,它隱喻了偏離本然的有為而治,將導致理想存在狀態的終結,“渾沌”隱喻著莊子所認同的原始秩序,此種秩序以智慧未開、是非之爭尚未展開為前提。在莊子看來,最為理想的行為處事方式,便是超越有人為意圖的謀劃,真正地無任何目的性,完全順乎自然本性。
莊子對儒家政治觀念的批判是深刻的,他對于政治的態度是超越與疏離,他所認為的理想社會政治秩序是一種自然的秩序,是一種相生無礙般的和諧,而“渾沌”就是這種最為理想的狀態,可以說莊子抱有某種強烈的質疑精神,他批判儒家政教,反思君主過度有為對世人所造成的傷害,當德政和仁政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禮”與“樂”的治理方式受到新挑戰時,他所試圖努力的方向是消解主體,乃至消解政治,以避免過度權力與政治干預對人性的扭曲與異化。
(二)“渾沌”隱喻著包容性
通常來說事物與事物是不同的,用莊子的話來說就是“有畛”(界限),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到,毛嬙麗姬都是人們所公認的美女,但到了魚鳥那里,魚見了潛入池底,鳥見了振翅高飛,美的標準是以誰為準呢?莊子打破了事物之間的界限,他將世俗的標準消融于無形,只有超越時與空的觀念,那么事物之間的差別也就不覆存在了,這樣“以何為美”的界限自然也就被消融了。而“渾沌”恰恰具有這種包容性,客觀來說,人要想好好地生存和生活,不可能將一切界限都消除,但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超脫,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生活與生存。
“渾沌”不但可以消融事物之間的界限,將萬物融于其中,更能在此基礎上生化出各種事物,即“臭腐與神奇可互化”。這種生化方式莊子將其分為三種,一是物象間的轉化,如《逍遙游》中“北冥鯤魚”化為“南冥鵬鳥”就屬于物象間的轉化,從“鯤”到“鵬”其都是有具體的外在形象的。二是物象與意象間的轉化,在《至樂》篇中莊子說“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萬物都有某種“幾”,也就是一種自無入有、自有入無的存在狀態,事物一直處于變化的過程中。莊子指出,有種最小的微生物叫“幾”,“幾”在水中會化為繼草,在岸邊則變成青苔,……赤蟲生出馬,馬可生人,人最后又復歸于自然之中,循環往復。萬物都從自然中開始,而后又終歸于自然,生生不息。此外在《齊物論》中有一個“朝三暮四”的故事,養猴人說給每天早上給眾猴三個橡子,眾猴立馬憤怒,當養猴人改口說換成晚上給猴子四個橡子時,眾猴則立即高興了起來,橡子為實物,喜怒為意象,物象與意象間的轉化就在須臾之間。三是意象間的轉化。莊周夢蝶的故事想必更加廣為人知,莊子做夢變成了一只翩翩飛舞的蝴蝶,醒來后不知道是自己夢中變成蝴蝶了還是蝴蝶做夢變成莊周了,這種“人化蝶”與“蝶化人”的轉化即為意象之間的互相轉化。
通過以上三種“生化”方式可以看出,這種轉化之間是無界限的、無目的性的、自然的,而“渾沌之境”恰恰是“生”與“化”過程中最好的狀態,“渾沌”包蘊萬物,萬物生化于渾沌之境。
(三)“渾沌”隱喻著不確定性
《應帝王》篇說:“儵與忽時相與遇”,“儵”和“忽”均有“神速”、“敏捷”之意,可見二者屬于同類,一個“時”字道出了“儵”與“忽”見面后并沒有簡簡單單地坐著,而是“風云際會”般地互相轉變與化生,“儵”象征著風的聲音,“忽”象征著云的外形,它們“時相與遇混沌之地”,使得本來為“一”的“渾沌”被氣所秘漫,被云所充衍,被風所吹化。
《莊子》書中常選取“風”“云”這兩者來描述“道”與“渾沌”的狀態。如《逍遙游》中提到的姑射山的神人(可視為“渾沌”的化身)吸風飲露,《齊物論》中的至人駕云氣,乘日月,游乎四海之外,《大宗師》中的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共同相約“登天游霧”,《在宥》中的云將去東方游玩,經過神木枝頭恰好遇到了鴻蒙,《秋水》中說“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從這些人物形象的出行、生活方式可以看出,莊子經常把“渾沌”投射到生活中十分常見但又變幻不定、飄忽綿延的“風”“云”身上,這實際上是在隱喻“渾沌”如同自然界的風云一樣,具有“不確定性”,因為風的方向難以捉摸,云的形狀無所定形。從運動方式上看,“風”有時沒有聲音也在流動,有時凌然呼呼大作,熱風襲面可以讓人發悶,清風徐來則可撩人心脾,“云”有時輕拂掛在天上,有時颯颯變幻風采,形狀飄忽不定也無邏輯性;從情緒上看,“風”可像人一樣憂怒喜樂,徘徊宛轉,“云”可像人一樣逍遙自在或輕飄適性或狂飆飛飏;從情感上看,“風”含幽約之情,“云”具怨悱之性,始卒若環,莫得端緒,總在途中,來時無跡往則無痕;從地域上看,“風”所游之地,“云”所飄之處都是陌生之地,而異鄉人到陌生地方難免心懷忐忑不安之感。“風與云”的種種特性時時刻刻呈現出令人“不確定”的感受。
由此可見,“風與云”(渾沌)是沒有邏輯的,不被規則所束縛,“風與云”即“不確定”的代名詞,當飄忽綿延的“風與云”(渾沌)投影于廣袤大地上時,那一片陰影遮蔽的是未曾出現過的事與物,那徐徐吹拂出的是包蘊著無限可能性的勃勃生機。莊子將“渾沌”的化身比作“風與云”,來隱喻不確定性,其實有著十分深刻的用意:“渾沌”代表著“道”,代表著人類最基本的存在情境,其本身就是不確定的,同時還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如果非要去人為確定什么、規定什么,“鑿以七竅”,那么這“渾沌”即死。
三、“渾沌”的歷史限度
莊子強調治理的過程應重視人之天性,其意義首先在于肯定合理的政治生活應該合乎人性,防止政治生活和政治實踐對人性的扭曲,避免人性的異化。雖然莊子并沒有具體談到如何做到這一點,但是他提醒人們應警惕政治的異化、關注人的本然之性,自然有其深意。不過,莊子將人性僅僅理解為前文明形態下的自然之性,顯然有其局限性。人性和自由的追求是密切聯系的,在走向自由的過程中,不能將人類文明的衍化置于視野之外,真正自由與否是人區別于動物以及物理對象的分別點。康德認為對于客觀物理對象來說,其完完全全是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馬克思也認為動物只是遵循它所屬的物種限定的尺度和需要來生存,但人卻可以按照任何尺度,以人所需要的尺度和方式來進行生產和生活。動物被物種的屬性所限定,而人則可以超出這種限定,因為人與動物不同,人具有主觀能動性,人可以進行自由的創造,然后去改造自然、改造自身,儒家所謂“成己與成物”,也包含走向自由的內涵。判斷社會演進是否合乎人性,要看統治階層能否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更大的可能、能否讓人具有更加自由的權力。莊子的政治哲學一方面提醒人們應避免政治治理導向人性的異化,另一方面又由拒絕功利性追求而消解目的性,并將至德之世理解為“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這一前文明意義上的“渾沌”之境,其中顯然包含內在的歷史限度。
安樂哲教授認為,只有對于一種文化有深入的了解與思考,才會開始構想事物的本質規律,因為這種規律對于事物的變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而這種觀念的產生正來源于哲學家對于創生宇宙萬物的“初始觀念”的準確把握。可以說“渾沌”作為莊子對于世界客觀規律的變化與本質的觀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其在莊子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有具體的展現。莊子雖然表面上冷眼旁觀,但實際上是心懷熱切,他對于世界有著深入的思考,他對于人生疾苦有著瀟灑的超脫,他對文明的異化有著敏銳的洞察,因為不管是何種道德觀念亦或政治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的參與其中,久而久之這種固定模式都會走向自身的反面,失去其靈活性,逐漸趨于僵化,甚至異化。有鑒于此,莊子在開篇就反對任何模式的固定框架,要以逍遙之游來超脫世俗的框架,去尋求每個個體的自然本性與自由天性,在心靈苦旅的過程中去神游,進行生命的放歌,而“渾沌”則是莊子前往逍遙之境最基本的模型,這個基本模型永遠在氤氳著新的生機與活力。因此莊子思想才能在近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始終被人們注解、研究、討論、訴說,給后人以無窮無盡的精神支撐。
參考文獻:
[1] 袁珂.山海經校注[M].成都:巴蜀書社,1992:65-66.
[2] 王弼注.樓宇烈校釋.老子道德經注校釋(新編諸子集成)[M].北京:中華書局2008.
[3] 郭慶藩.莊子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1:309.
[4] 王博.莊子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30.
作者簡介:孟豪(1995- ),男,河北石家莊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