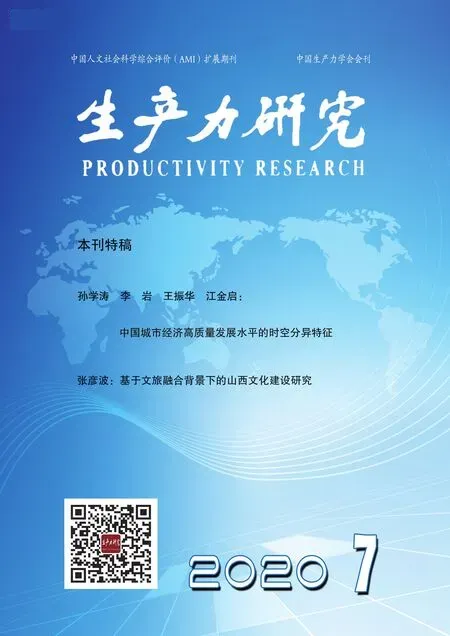長三角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測度與評價
(上海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上海 200093)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經濟增長逐步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過渡。2019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進一步指出要貫徹新發展理念并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在此背景下,本文結合新發展理念的內涵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并利用2018 年長三角地級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數據,對長三角40 個地級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證分析。
對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測度,一類研究采用全要素生產率(TFP)來衡量經濟發展質量[1],孫英杰和林春(2018)[2]等采用DEA-Malmquist 指數法對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相關測算;另一類研究通過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體系來測度經濟發展質量[3-4]。對于評價體系各指標權重的確定方法包括主觀評價法和客觀評價法,楊新洪(2017)[5]采用了專家評價法對深圳市的發展情況進行了評價;魯邦克等(2019)[6]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中國省際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了測算;黎文勇和楊上廣(2019)[7]等利用了改進的熵權法對長三角城市群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了測度。為了減少測度結果的主觀性,本文采取客觀分析法中的熵值法來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
二、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的構建
本文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在借鑒國內外相關評價指標體系[8]的基礎上,從經濟活力、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協調發展、人民生活等五個準則層構建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GDP增長速度等23 個評價指標,形成了如表1 所示的評價指標體系。
三、長三角各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證評價與分析
(一)評價對象與數據說明
本文選擇了長三角蘇浙皖40 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由于上海市的絕對大都市特性不同于地級市,因此剔除。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各省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官方統計局網站。
(二)評價方法與結果分析
根據上文確定的評價對象和評價指標體系,在搜集了2018 年各地級市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數據之后,使用熵值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五個準則層進行分項評價。然后基于分項得分再次使用熵值法進行綜合評價,評價結果如表2 所示。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表2 中的分項指標得分可以看出每個城市在經濟發展中的優勢和不足:(1)從經濟活力的層面來看,蘇州和金華的得分最高,這主要由于這兩個城市比較高的對外開放程度帶來強大的發展動力。而鎮江等經濟活力位于末位,這是因為這些城市的居民消費貢獻率較低。(2)從創新發展的角度來看,蘇州位列第一,其次是無錫、南京,這反映了城市對創新人才的吸引力直接影響城市創新發展的水平。(3)從綠色發展的角度來看,黃山、舟山和臺州位于前列,這主要基于這些城市的自然條件和優化的產業發展結構。而嘉興因為資源消耗過高導致城市綠色發展水平也較為欠缺。(4)從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舟山、寧波和杭州都有較前的排名,這主要是因為浙江省的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優越的城鄉結構。(5)從人民生活的角度來看,位列前三的均為浙江省內的城市,分別是麗水、臺州與金華,這反映了浙江作為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其省內各市的社會保障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分都比較高。
從綜合評價的結果來看,蘇州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最高,其次是寧波和杭州,這些城市的分項排名較為均衡,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而安徽省除合肥以外各市的排名均比較靠后,這反映了安徽省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與江蘇和浙江相比有較大的差距。安徽省應進一步提高省內協調發展水平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協同江浙滬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表2 長三角地級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分項及綜合評價得分
四、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議
本文結合上述實證研究結果以及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狀[9-11],提出以下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建議:第一,適度的經濟增長依然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動力;第二,只有完善科技人才的培養與激勵機制,深化科技體制的改革,才能實現科技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第三,要以新經濟包括數字經濟、平臺經濟、智能制造、現代服務業等構建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第四,各城市需繼續以開放促進貿易的高質量發展;第五,各城市需要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因城施策,完善區域政策和空間布局,推動區域的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