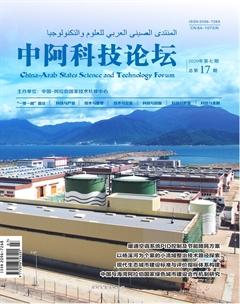“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發展模式
王恒杰 于藝
摘 要:“一帶一路”倡議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提出了新要求,特別是給應用型高等教育帶來了新機遇與新挑戰。應用型高等教育需把握新的國際大勢,全面深刻認識“一帶一路”視域下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內涵與特點,立足自身優勢,積極尋求政府、行業的參與,依托不同合作層面的不同類型項目設計多樣化、實用化的教育國際化模式,按照確定項目-打造平臺-健全機制-催生成果-產生循環效應的基本路徑,成功實現國際化轉型。
關鍵詞:“一帶一路”;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發展;模式;路徑
2013年9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并把合作內容概括為“五通”,即: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初步估算,“一帶一路”沿線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1]。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國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出席高峰論壇開幕式,并主持領導人圓桌峰會,把“一帶一路”倡議推向新的高度。“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謀求世界領導地位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一帶一路”倡議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臺。
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有力支持。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形成的新的國際合作平臺上謀求新的發展機遇,人才培養是關鍵性、基礎性的工作之一。鑒于該倡議的具體特點,與此相關的人才培養也必然具有相應的特殊性。在此背景下,基于傳統意義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探討與“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契合的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1 關于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
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一組既密切關聯又有所區別的概念。厘清其相同點與不同點,便于我們找準角度深入討論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有關問題。
1.1 高等教育國際化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國際大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把跨國界和跨文化的視點和氛圍的大學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主要功能相結合的過程,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過程,既有學校內部的變化,又有學校外部的變化;既有自上而下的變化,又有自下而上的;還有學校自身的政策導向的變化[2]。”加拿大學者簡·奈特(Jane Knight)從高校層面對高等教育國際化進行定義,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就是在教育機構的教學、研究和服務等功能中融入國際化思維和跨文化理念的過程[3]。美國教育研究者范·德·溫得(Van der Wende)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種系統化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使高等教育適應全球經濟、社會和世界勞動力市場變化的需求與挑戰。針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形式的多樣化,德國學者德克·范·達姆(Dirk Van Damme)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當前主要形式為學術合作研究、簽訂互認協議、課程國際化、學生及教師的人員流動、合作辦學或在國外設置分校、遠程教育等[4]。鐘秉林(2013)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看待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除了經濟全球化的直接推動外,政治、文化、科技發展等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動因[5]。肖鳳翔、尚宇光(2012)從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四個方面分析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基本上承襲了著名高等教育國際化專家簡·奈特(Jane Knight)的觀點[6]。李盛兵、劉冬蓮(2013)基于簡·奈特(Jane Knight)動因模式,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及人力資源五個維度為縱坐標,以國際組織、區域、國家及高等院校四個層面為橫坐標,構成了一個二維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動因理論框架[7]。李軍等人(2020)認為新形勢下發展中國家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新增長點,信息互通成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要素[8]。侯淑霞、韓鵬(2019)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是加強高等教育綜合實力的重要途徑,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動態過程[9]。
1.2 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
應用型高等教育目前并無通用的權威定義。根據研究需要,本文姑且將其界定為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基本任務的高等教育,它是應用型高等院校的集合,主要著眼于滿足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需要,是對新型的本科教育和新層次的高職教育相結合的教育模式的探索,是由部分省屬本科院校與國家級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國家大型骨干企業聯合試點培養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應用型專業人才的教育實踐。應用型高等教育重在“應用”二字,要求以體現時代精神和社會發展要求的人才觀、質量觀和教育觀為先導,以在新的高等教育形勢下構建滿足和適應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新的學科方向、專業結構、課程體系,更新教學內容、教學環節、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全面提高教學水平,培養具有較強社會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的高素質應用型人才[10]。應用型高等教育要求各專業緊密結合地方特色,注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應用型人才,從教學體系建設體現“應用”二字,其核心環節是實踐教學。
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顯然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部分,它具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般特征,同時又因其任務的特殊性而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內容、路徑與要求。“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則在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合該倡議既不同于全球化背景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內涵的諸多要素,從而具備一些新的特點。
2 “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涵解析
“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以服務“一帶一路”倡議為目的,其基本平臺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應用型高等教育,包括其研究型大學中的應用型學科專業,是此類高校及學科專業之間的跨國合作,具有如下內涵:
2.1應用性
相關高等院校及學科專業具有鮮明的應用特征,即專注于學科專業已有成果的應用性開發研究和工程技術的教學訓練,培養能夠服務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與技術合作的專門人才,包括語言文化服務、經營管理、工程技術、法律、醫療等多個學科領域,特別是與具體項目相關的領域,包括且不限于人力資源管理、項目管理、旅游管理、關務服務、路橋建設、土木工程、信息技術等。這一點與普通高校的教育國際化進程中比較集中于基礎性學科的特點具有顯著不同。
2.2國際性
上述學科專業均以“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合作項目為服務對象,以多樣化的國際合作形式實施人才培養,包括留學、聯合培養、教師及其他教學資源共享等,因此具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般性特征,或者說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3區域性
由于“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合作具有顯著的區域性特征,該框架下的國際教育合作相應地也表現出顯著的區域性,集中于東亞、南亞、中亞、西亞、北非及東歐等主要區域,并向西歐、拉美相關國家地區延伸,涵蓋漢字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東正教文化圈和拉丁文化圈。
2.4多邊性與雙邊性
“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國家近44億人口。作為新的國際合作平臺,具有突出的政治、經濟、教育、人文等多領域多邊合作的性質,亞投行的組建以及區域性的基礎設施建設均具有明顯的多邊合作的特征,因此此類項目相關的教育國際合作也相應體現出多邊性。同時,針對不同國家又有不同的具體合作內容和合作方式,表現為中國與沿線各國的雙邊合作,這種基于雙邊經濟合作項目的教育合作也多為雙邊教育合作。
2.5針對性
與西方語境下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同,“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的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具有自身特點,以服務本框架內的多領域國際合作為導向,著力解決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及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人才供給問題,因此人才培養目標更加明確,質量標準更加具體,同時也更具有行業化、專業化、項目化的特征。
3 “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條件、模式與路徑
圍繞“一帶一路”倡議討論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無法回避以下三個問題,即:達成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需要具備何種條件、以何種形式(模式)與通過何種手段(路徑)。
3.1 “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發展的條件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推進為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與社會環境,但要真正實現這一轉型,還需要非常現實、具體的條件保障,包括政策條件,行業支持、院校重視、資金和人力投入等。
3.1.1政府主導,政策鋪路
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政府間的產業合作對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具有顯著的引導作用。與政府間合作項目相配套,對應的人才培養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對常規專業人才的需求,政府間合作還會產生對某些特殊領域人才的需求。要解決這個問題,各國、各級政府都需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可以通過向教育部門下達指令并提供專項資助的形式,讓某些具備相應培養能力的高等教育機構來具體承擔人才培養任務。鑒于政府間的合作可以在國家、地方等不同層面展開,且我國大部分應用型高等院校都分布在地方,相應地滿足國際合作要求的人才培養的任務也可由不同層級的政府來主導協調。
3.1.2行業依托,需求導向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國際合作經常性呈現為相關國家間某些特定行業間的合作,如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通訊、交通,地礦資源及能源領域的勘探、開采以及不同程度的加工等,即可依托合作各方行業的力量開展相關人才的委托培養或聯合培養,以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標準、效率。應用型高等院校應充分發揮自身在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方面的優勢,積極加入行業協會,與行業組織共同擬定人才培養計劃與方案;而行業組織各成員企業則應積極順應行業發展要求,主動與高校合作,為應用型高效的國際化人才培養工作提供切實可行的人力、物力支持,具體包括辦學資金、實踐教學師資、聯合考察機會及經費、項目談判機會等。
3.1.3院校為基,質量為本
近年來,不少高等院校順應“一帶一路”倡議的需求,在原有教育國際合作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拓寬合作領域,增加合作伙伴,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截至2019年12月24日,我國高校中經教育部或地方審批開辦國際合作項目的已經達到170家(教育部審批131家,各省40家),舉辦各類教育合作項目2000余個(教育部審批1081個,各省916個);吸收外國留學生規模達到492185人,其中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留學生人數已達260600人[11]。留學生除了選擇語言文化項目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人從事其他技術型專業學習(包括學歷和非學歷)。但總體看起來,高校國際合作辦學的開展情況良莠不齊,其中不乏追求規模不顧質量者,許多留學生事實上不具備完成學業的能力——這與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國際教育合作形成鮮明的對照。因此對于應用型高等院校而言,不應簡單地擴大留學生規模,而應該科學選擇適宜項目并且嚴格選拔符合條件的學生加入項目,根據培養標準設計嚴格的培養流程以確保培養質量。練好內功,強化質量是實現國際合作轉型的重要前提。
3.1.4保證投入,重點支持
應用型高等院校應將“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化轉型發展視為學校新的發展增長點,將其納入學校發展戰略,政府也應當將其視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配套措施,是國家和地方輸出產能與技術的重要基礎環節。學校自身需認真規劃,安排專門的資金預算,政府應予以大力支持,以充足的資金保障高校完成必要的軟硬件建設,為國際化人才培養創造良好的條件。
3.2 “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發展模式
“一帶一路” 倡議框架下的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必須順應相關地區及國家間經濟、政治和文化合作的多樣性、個性化需要,“量身定制”合作模式。
3.2.1依托于單一合作項目的教育國際化模式
該模式針對具體合作項目實施過程中的崗位人才需求而設計,培養目標具有明確的崗位導向,培養規格偏重于操作技能與技術,而不過度強調知識結構的系統性,培養對象為中外雙方擬投入合作項目運營的從業人員。包括三種具體模式:
(1)短期崗位培訓模式:針對已開始運營或即將開始運營的合作項目。培訓對象為項目在崗(包括關聯崗位)或擬上崗人員,培訓內容可以包括入職培訓、崗位操作技能、與崗位工作相關的溝通技能(包括基本的合作對方的語言能力與文化認知,亦即與崗位工作相關聯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此類教育項目一般而言時間較短、較集中,課程內容相對模塊化,不涉及學歷證書,有時也可不涉及各種崗位資格證書。此類模式下,應用型高校的主要任務是接受項目方的委托提供語言文化方面的培訓,其他培訓內容則多由合作雙方的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實施。
(2)專業人才委托培養模式:一般而言針對相對長線的人才需求。培養對象為經過篩選并準備長期從事某一行業工作的人員,培養內容為系統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委托方可以是合作項目的共同管理方或其中的任一方。應用型高校作為受委托人,按照委托培養合同規定的培養目標和質量標準開展人才培養工作。此模式實際上是一種真正的跨國訂單培養模式。事實上該種模式在石油礦產勘探與開采、冶金、汽車制造、酒店管理與服務、經貿等領域已多有應用。
(3)專業人才合作培養模式:針對大型長期合作項目的基礎性人才需求。合作雙方基于長期的合作合同,利用雙方各自擁有或者各自所在國擁有的教育資源指定聯合人才培養計劃,合作開展項目長期所需的專業技術人才培養工作。該模式下參與合作培養的教育機構往往是具有深厚行業背景的高等教育機構,可涉及交通運輸、通訊、航空、船舶工程、港航管理與服務等行業領域。具體合作方式可以包括共同制定培養方案與教學大綱、學分互認分段培養(2+2,3+1,1+3等)、師資共享、課程共享以及教師的科研合作等。
3.2.2依托于國家間經濟雙邊合作的教育國際化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一直重視發展和第三世界(過去稱亞非拉,目前多為發展中國家或新型市場國家)的關系,而“一帶一路”倡議也可以理解為是我國一貫的外交政策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次完美升級。我國與沿線國家開展廣泛而又密切的雙邊或多邊經濟合作已成定勢。與之相呼應,教育合作也當然應成為這種合作的重要支柱之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一個負效應就是教育水平的不平衡。為滿足經濟合作對各類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合作勢在必行。當然,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在不同的層面進行,如通才型人才培養(政治、歷史、語言、文化、文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藝術學等)、專業型人才培養(礦產資源勘探、石油開采與儲運、冶金、化工、建筑、交通、物流、貿易等)。作為應用型高等院校,其優勢應在于積極參與各類專業性國際化專業人才培養,一方面為國家戰略提供人才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其自身發展的重要突破口。可具體采用以下兩種模式:
(1)專業人才委托培養模式:依托國家間經濟與教育合作框架,由雙方國家教育主管機構協商指定教育合作框架協議,確定特定學科專業領域的委托培養計劃,授權雙方有關院校落實具體合作項目,并予以實施。實施委托培養的專業領域一般而言是合作的一方具有明顯優勢而另一方空白或相對弱勢的專業領域。從目前的合作實踐來看,我國有關院校已經開展或可開展的此類項目包括石油勘探與開采、中醫臨床、國際經濟與貿易、關務服務等。
(2)專業人才合作培養模式:依托國家間經濟與教育合作框架,經雙方相關政府機構授權各方高等院校依據雙方市場需求,確定合作領域及人才培養項目,擬定專業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議定合作雙方各自承擔的教學任務、畢業條件、學位授予條件等,并予以具體落實。該模式要求承擔合作培養任務的院校間成立針對該項目的協調管理機構,建立定期溝通機制,選聘專門的師資隊伍,以確保項目的順利實施和培養目標的達成。
3.2.3依托于多邊經濟合作的多邊教育合作模式
相關國家政府(包括具體參與合作的各國地方政府)按照多邊經濟合作計劃和遠景規劃,判定近、中、遠期國際化應用型專業人才的需求情況與趨勢,支持各國相關高校建立多邊教育合作機制,如區域性大學聯盟,主導以滿足多邊合作需要為目標的教育合作。在此框架下,可具體采用相互間的委托培養模式、合作培養模式。伴隨著我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進程的不斷推進,逐漸形成“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間的“教育共同體”。
3.2.4國內外高校間自主人才培養合作模式
高校主動配合國家間合作的戰略要求,積極尋找教育合作的機會,選定合適的國外高校開展院校間的人才培養合作。合作院校雙方都將推進合作作為自己的日常工作內容,積極引導學生參與合作辦學項目。此類合作目前已有比較成熟的模式,包括學分互認、學生/師資交換、雙學位、提供升學途徑、開展合作研究等。此外,應用型高校在開展產學研合作時,也應刻意選擇那些已經或者擬開展跨國經營活動的企業,依托企業的人才需求設計合作辦學項目,以良好的就業預期選拔吸收優質生源參加到合作辦學項目中來,并依托企業資源開展實踐教學,以確保人才培養質量。
3.3 “一帶一路”視閾下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發展路徑
“一帶一路”倡議為應用型高等院校提供了國際化轉型發展的良好契機。抓住機會重新進行發展定位,積極投身到“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新型國際合作大潮中來,是此類高校謀求進一步特色發展的重要選擇。設計好符合自身特點和形勢要求的合作路徑,將有效推動高校建設與發展。一般而言,應用型高校的國際化發展進程離不開“確定項目、打造平臺、優化機制、培育成果、產生循環效應”這幾個主要環節:
(1)確定項目:圍繞服務“一帶一路”尋找開展教育合作的項目,基于雙向選擇的原則,在認真篩選、科學論證的前提下確定合作的具體項目,形成明確的合作合同。
(2)打造平臺:以教育合作合同為依據,建立合作各方共同參與的項目組織實施的領導機構,完成必須的人員配備,形成明確的項目實施流程和具體的合作方案(包括招生、培養方案設計、師資準備、設備設施準備、實踐教學保障等)。
(3)健全機制:在項目運營過程中根據遇到的各類問題及時開展有效溝通,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管理和溝通機制,形成常見問題分類解決的可執行預案,切實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與效果。
(4)催生成果:加強項目的過程管理,確保各階段任務的順利完成和階段目標的順利實現,在此基礎上按計劃完成合作項目的預設目標,并通過評估驗收。
(5)產生循環效應:對項目運行情況進行全面總結,不斷優化后續合作方案與合作流程,產生源源不斷的后續合作成果。
4 結語
應用型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是應用型高等教育在 “一帶一路”倡議的大背景下落實其高等教育職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把握機遇,科學規劃,充分利用新形勢下的既有發展空間并積極拓展新的發展空間,是應用型教育機構所有成員(各大院校)都不應忽視的重要課題。在新的國際化視野下,積極探索、深入研究,尋求與國家戰略同向、同步的發展模式,積極謀求主動發展,形成各自獨樹一幟、根基雄厚的辦學特色,是該類院校在心的教育競爭中賴以脫穎而出并立于不敗之地的重大戰略選擇。
參考文獻:
[1]“一帶一路”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 約占全球29%[EB/OL].http://www.chinanews.com/cj/2014/10-21/6699000.shtml,2014-10-21.
[2]劉道玉.大學教育國際化的選擇與對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7(04):6-10.
[3]Knight J. Internationalization Remodeled: Definition, Approaches, and Rationales[J].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4(01).
[4]Damme D V. Quality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J].Higher Education,2001(04).
[5]鐘秉林.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是高校內涵建設的重要任務[J].中國高等教育,2013(17):22-24.
[6]肖鳳翔,尚宇光.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實質及其經濟動因[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68-72.
[7]李盛兵,劉冬蓮.高等教育國際化動因理論的演變與新構想[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29-34.
[8]李軍,段世飛,胡科.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階段特征與挑戰[J].高教發展與評估,2020(01):81-91+116.
[9]侯淑霞,韓鵬.“雙一流”建設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研究[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9(08):46-51.
[10]汪明義.擔負時代使命,創建應用型大學[J].中國高等教育,2014(021):34-37.
[11]教育部.2018年來華留學統計[EB/OL].http://www.ict.edu.cn/news/jrgz/jydt/n20190412_57889.shtml,2019-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