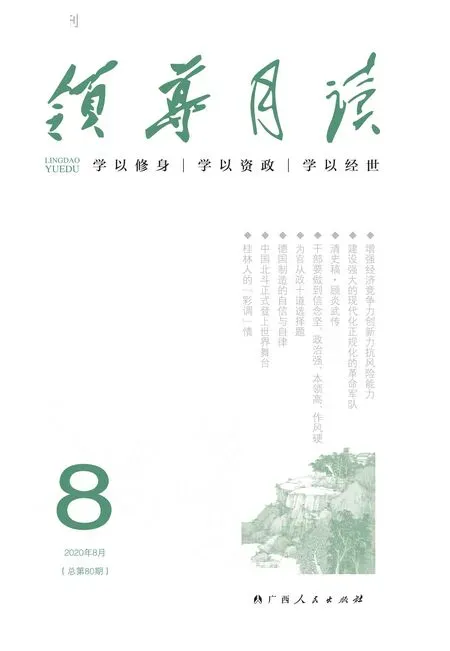“憂患”與“資治”:司馬光與他的時代
鄧小南
司馬光于1019年出生,1086年去世,正值宋真宗晚年到哲宗即位初期,這一時段基本上是北宋王朝的前中期。宋代是社會經濟、制度建設、科技文化領先于世界的時期,同時也是周邊被擠壓、內政因循求穩、面臨嚴峻挑戰的時期,戰略格局與政策應對有諸多問題。
北宋前中期的政治格局
北宋王朝建立八十年之后,長期積累的內外矛盾愈益突出,改革的呼聲逐漸高漲,范仲淹等領袖人物被推舉出來,開始推行新政。“慶歷新政”的主要綱領目標,是希望“法制有立,綱紀再振”,也就是要回到祖宗朝那樣的“理想狀態”。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編修“熙寧新法”的時候,范仲淹已經去世了。宋神宗器重的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竭誠國事,都觀察到當時綱紀隳紊、風俗弊壞等問題,但對于治國理政的路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方略,意見全然不同。
面對內外重重矛盾,王安石秉持“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堅持推動新法;司馬光卻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主張穩健緩進。針對國家財政問題,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開源重于節流;司馬光則認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朝廷所謂“理財”無異于盤剝,對家國民庶并非益事。司馬光曾經寫書信勸誡王安石,王安石則斷然拒絕了司馬光的意見。兩人自此分道揚鑣。宋神宗希望把他們都留在朝廷,但是兩個人堅決不同意共事,宋神宗最終選擇了主張變法的王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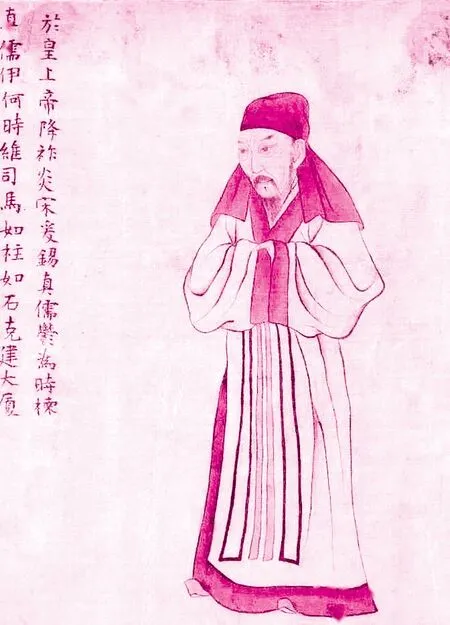
司馬光
司馬光后來到洛陽,開始專心致志地修撰《資治通鑒》,一去十五年。元豐八年(1085 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政權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里,傾向于維護“祖宗之法”的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等人被召回朝廷,政局發生了明顯的轉折。
元祐元年(1086年)閏二月,司馬光被任命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就是當時的首相,達到他仕履的巔峰。他回朝后提出的“十科薦士法”等建議,都被陸續采納,新法也先后廢罷。當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了。此時司馬光身體已經非常不好,無法上朝,但他還是手書致函另外一位宰相呂公著,對王安石給予很高的評價,希望朝廷優予追贈。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作為政治人物的磊落情懷。
士人文化與“資治”意識
宋代的士人文化與前代有高度關聯,特別是中唐以來,經過五代到宋,有延續也有變革。宋代內部的政治環境還算穩定,北宋前中期的文化氣氛也相對寬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士人群體比較活躍,社會充滿了活力。
其中的優秀者以天下為己任,這種責任感集中體現于集體性的憂患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不僅是范仲淹的高尚情操的表現,像王安石、司馬光等人,也都有由當時國家的格局背景所帶來的強烈憂患意識。
宋仁宗后期,王安石在給皇帝的奏章中指出,國家“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司馬光也說:“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統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司馬光又在《稽古錄》中說:“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資治”的意識,正是在戒惕憂患、期待治世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即便政治上失意之際,他們仍然不放棄自己的治國理念,對于學統、道統仍然有所堅持。
余 論
所謂“資治”,首先是士大夫的自覺意識;如何資治,當然關系到治理者的襟懷、見解、能力等。《邵氏聞見后錄》中記載,北宋后期有人跟劉安世說:“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劉安世回答說:“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第一。”也就是說,歷代宰相中,司馬光學術上確實很強,但是作為宰相,才干能力應該能夠統馭四海,司馬光可能算不上第一等的人才。
總體上看,司馬光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蘇軾稱贊司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我想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