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道教通史》述評(píng)
孫瑞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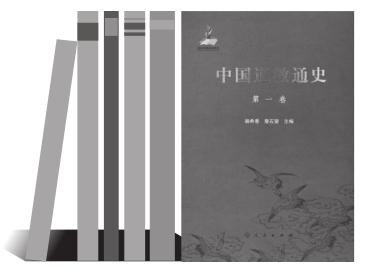
2019年12月,由四川大學(xué)文科杰出教授卿希泰先生和詹石窗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guó)道教通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該書(shū)是中國(guó)道教研究領(lǐng)域的最新成果總結(jié),是迄今為止部頭最大、內(nèi)容最全的一部道教通史。它的出版是21世紀(jì)道教研究領(lǐng)域一座嶄新的里程碑。《中國(guó)道教通史》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由卿先生主編的《中國(guó)道教史》(修訂本)基礎(chǔ)上,吸收國(guó)內(nèi)外最新研究成果,查缺補(bǔ)漏、推陳出新,歷時(shí)近10年修訂而成的一部道教通史。全書(shū)共五卷,分五冊(cè)獨(dú)立出版發(fā)行。全書(shū)卷帙浩繁,洋洋灑灑,共計(jì)344余萬(wàn)字。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卿希泰先生對(duì)中國(guó)道教史的研究始于20世紀(jì)70年代。由于受到政治運(yùn)動(dòng)的沖擊,他在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中國(guó)道教思想史綱》第一卷的撰寫(xiě),并于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他又相繼撰寫(xiě)了《中國(guó)道教思想史綱》第二卷、《續(xù)·中國(guó)道教思想史綱》,分別于1985年、199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而作為“六五”至“八五”的國(guó)家重點(diǎn)項(xiàng)目的最終成果——《中國(guó)道教史》四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別于1988年4月、1992年7月、1993年10月、1995年12月先后出版。全書(shū)約200萬(wàn)字,共十四章。在結(jié)項(xiàng)專(zhuān)家的評(píng)審意見(jiàn)中,高度評(píng)價(jià)了《中國(guó)道教史》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他們認(rèn)為:
《中國(guó)道教史》論著,不僅填補(bǔ)了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研究的空白,且在國(guó)際道教學(xué)術(shù)研究界亦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它代表了當(dāng)今我國(guó)道教學(xué)術(shù)研究所達(dá)到的水平。
由于這一版的《中國(guó)道教史》出版時(shí)間跨越7年,存在排版和裝幀風(fēng)格不一致等問(wèn)題,加之,在毫無(wú)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初次探索性地撰寫(xiě)如此大規(guī)模的道教通史,難免有遺漏或編校方面的錯(cuò)誤,所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積極協(xié)助下,1996年四卷本的《中國(guó)道教史》(修訂本)出版了。在“修訂本”第1卷“修訂版前言”中,卿希泰先生說(shuō):
本書(shū)的第一版出版發(fā)行之后,在國(guó)內(nèi)外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的高度重視,受到了各種好評(píng),產(chǎn)生了較大的社會(huì)影響,不少報(bào)刊均發(fā)表了書(shū)評(píng)并榮獲了國(guó)家及省的各項(xiàng)獎(jiǎng)勵(lì)。但是多卷本道教史的編寫(xiě),畢竟還是一項(xiàng)探索性的工作;且因這門(mén)學(xué)科內(nèi)容龐雜,涉及的知識(shí)面很廣,加之我們的水平有限,同時(shí)還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缺點(diǎn)錯(cuò)誤在所難免。……由于編寫(xiě)計(jì)劃的不斷擴(kuò)展,在全書(shū)編完以后,我們即感到有個(gè)別內(nèi)容需要前后作一些相應(yīng)的協(xié)調(diào);再加上從第一卷到最末一卷的出版過(guò)程較長(zhǎng),前后共達(dá)七年,因而各卷的裝幀和紙張的顏色質(zhì)量均不夠統(tǒng)一,還有一些排印、校對(duì)方面的問(wèn)題也需要改正。……為了精益求精,立即對(duì)本書(shū)從頭到尾進(jìn)行一次全面的修訂和補(bǔ)充,重新再版。
在卿先生主編《中國(guó)道教史》和《中國(guó)道教史》(修訂本)的過(guò)程中,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是其最根本的方法。雖然在卿先生組織編寫(xiě)《中國(guó)道教史》之時(shí),國(guó)內(nèi)已經(jīng)有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國(guó)內(nèi)尚無(wú)一部完整的道教通史可資借鑒,對(duì)國(guó)外的道教學(xué)術(shù)研究又知之甚少。如何厘清跨越2500多年的道教起源、產(chǎn)生、發(fā)展歷史,并辨別錯(cuò)綜復(fù)雜的史料,對(duì)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出公允的評(píng)價(jià),其所需耗費(fèi)的人力、學(xué)力和財(cái)力可見(jiàn)一斑。因此,明確道教的產(chǎn)生時(shí)間,發(fā)展階段的分期,史料的使用標(biāo)準(zhǔn)等對(duì)于通史的撰寫(xiě)顯得尤為迫切。在《中國(guó)道教史》(修訂本)中,卿先生將道教創(chuàng)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之前的歷史劃分為四個(gè)階段:自張陵創(chuàng)教至魏晉南北朝為止是道教的“創(chuàng)建和改造時(shí)期”;隋唐至北宋是道教的“興盛和發(fā)展時(shí)期”;南宋以后至明代中葉是道教的“宗派紛起和繼續(xù)發(fā)展的時(shí)期”;明代中葉以后至中華人共和國(guó)成立之前是道教的“逐漸衰落時(shí)期”。這種時(shí)間劃分方式,雖然一定程度上受到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的明清衰落論影響,但其跳出了按古代王朝更迭敘述道教發(fā)展歷史的方式,按照史料中所反映的道教歷史的特點(diǎn),實(shí)事求是地對(duì)道教發(fā)展的歷史階段進(jìn)行劃分,無(wú)疑是具有重要時(shí)代進(jìn)步意義的。同時(shí),由于道教歷來(lái)有“造作道書(shū)”的傳統(tǒng),如何甄別道經(jīng)的價(jià)值,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立場(chǎng),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dǎo)進(jìn)行研究,對(duì)道教歷史事件和人物作出理性地觀察和判斷在當(dāng)時(shí)顯得十分必要。
慎終如始,開(kāi)拓新局
對(duì)《中國(guó)道教史》(修訂本)的修訂工作始于2010年。在工作開(kāi)始后不久,卿先生就被確診為肺癌,并進(jìn)行了手術(shù)。在修訂工作開(kāi)展期間,他忍受著病痛的折磨,身體力行地主持工作,仔細(xì)審閱收到的每一份稿件。到了2015底,由于身體每況愈下,眼看還有大量的修訂工作有待進(jìn)行,他卻有心無(wú)力。于是,他多次召集詹石窗教授到家中,探討后續(xù)工作應(yīng)如何開(kāi)展,并將全書(shū)的后續(xù)修訂工作安排和統(tǒng)稿重任交由詹石窗教授負(fù)責(zé)。在詹石窗教授的統(tǒng)籌安排下,2019年12月,歷時(shí)將近10年的《中國(guó)道教通史》終于出版了,并榮獲“人民出版社2019年度優(yōu)秀學(xué)術(shù)著作獎(jiǎng)”。
《中國(guó)道教通史》延續(xù)了“修訂本”從道教對(duì)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道教文化的現(xiàn)代價(jià)值,以及弘揚(yáng)優(yōu)秀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角度謀篇布局的傳統(tǒng)。《中國(guó)道教史》的編撰從一開(kāi)始便肩負(fù)著發(fā)掘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價(jià)值的使命,編撰者們都懷著強(qiáng)烈的愛(ài)國(guó)主義情感。在《中國(guó)道教史》第4卷“后記”里,卿先生曾回憶說(shuō)道:
記得當(dāng)時(shí)宗教學(xué)學(xué)科規(guī)劃領(lǐng)導(dǎo)小組組長(zhǎng)任繼愈先生在全體大會(huì)上談到為什么要把這個(gè)課題列入國(guó)家重點(diǎn)科研項(xiàng)目時(shí),曾慷慨激昂地說(shuō)道:“道教本來(lái)是我國(guó)土生土長(zhǎng)的傳統(tǒng)宗教,可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是由我們國(guó)家提供材料,讓外國(guó)人去出成果,這是國(guó)家的恥辱,民族的恥辱,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我們一定要痛下決心,編寫(xiě)出自己的道教史來(lái),為國(guó)家爭(zhēng)光,為民族爭(zhēng)光。”任先生這段話對(duì)我們簡(jiǎn)直是如雷貫耳,聽(tīng)了以后非常激動(dòng),實(shí)在無(wú)法平靜下來(lái)。接著在討論會(huì)上,任先生和王明先生以及到會(huì)的全體代表,大家都一致推薦由我們研究所來(lái)承擔(dān)這個(gè)課題的編寫(xiě)任務(wù),并由我來(lái)牽頭擔(dān)任主編。我一方面感到這個(gè)任務(wù)太艱巨,恐自己水平不夠,難以擔(dān)當(dāng);另一方面,任先生的聲音又在耳邊震蕩,使我產(chǎn)生一種義不容辭的責(zé)任感,不好推卻。
而從“修訂版”的出版至《中國(guó)道教通史》的出版期間,道教研究者們對(duì)道教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入的認(rèn)識(shí)。從《中國(guó)道教史》“修訂版”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主要從了解古代政治及歷史、儒釋道三教關(guān)系、古代文學(xué)藝術(shù)思想、科技思想等角度闡述研究道教歷史的意義。而在《中國(guó)道教通史》中,首先是從道教思想來(lái)源的多元性對(duì)保存我國(guó)古代思想的重要作用的角度;其次是從政治、學(xué)術(shù)思想、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技術(shù)、倫理道德,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發(fā)展,民俗和民間信仰等與道教的密切關(guān)系的角度;再次是從道教與少數(shù)民族關(guān)系的角度,闡述了道教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這一認(rèn)識(shí)的深化是奠定在國(guó)內(nèi)外幾代學(xué)人的研究成果基礎(chǔ)上的,絕非泛泛而談。可以說(shuō),如果說(shuō)多卷本《中國(guó)道教史》的編撰是受到愛(ài)國(guó)主義情感的激發(fā),那么《中國(guó)道教通史》的出版則是建立在編撰者對(duì)道教歷史有了更加理性和清晰的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上的。
《中國(guó)道教通史》在“修訂本”的基礎(chǔ)上,對(duì)道教發(fā)展的歷史階段分期進(jìn)行了進(jìn)一步的補(bǔ)充和修訂。其主要包括五個(gè)階段:東漢至南北朝是道教的創(chuàng)建與改造期,隋唐至北宋是道教的興盛與發(fā)展期,南宋至明代中葉是道教的宗派紛爭(zhēng)與融合變革期,明代中葉至民國(guó)是道教的兩極分化期,1949年以來(lái)是道教的曲折復(fù)興期。這樣的劃分方式,體現(xiàn)了以詹石窗教授為主編的中年一代學(xué)者吸收近年以來(lái)國(guó)內(nèi)外的最新學(xué)術(shù)研究成果,對(duì)道教歷史分期有了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shí)。比如“修訂本”中,南宋至明代中葉被認(rèn)為是“宗派紛起和繼續(xù)發(fā)展時(shí)期”,而《中國(guó)道教通史》編寫(xiě)之時(shí)對(duì)“繼續(xù)發(fā)展”有了更加清晰的概括,也就是道派不斷的“融合變革”。關(guān)于明代中葉至民國(guó)時(shí)期道教的發(fā)展情況,“修訂本”認(rèn)為是“逐漸衰落”。隨著近年以來(lái)明清道教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量清明時(shí)期的道經(jīng)被發(fā)掘出來(lái)。因此《中國(guó)道教通史》作出了新的論斷,認(rèn)為雖然道教失去了統(tǒng)治者的扶植和推崇,“這一時(shí)期的道教,與前兩個(gè)時(shí)期相比較而言,總體上趨于衰微,但并不意味著道教從此一蹶不振。實(shí)際上,在某些地域,某些道派和人物的活動(dòng)依然十分活躍,道教在民間社會(huì)和少數(shù)民族地域依然具有相當(dāng)大的影響力”。同時(shí),《中國(guó)道教通史》還將新中國(guó)建立后的道教歷史發(fā)展特征概括為“曲折復(fù)興期”,對(duì)這一段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把握。
關(guān)于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道教的發(fā)展歷史,道教研究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臺(tái)港澳地區(qū)道教的發(fā)展情況,以及海外的道教學(xué)術(shù)研究情況,歷來(lái)涉及一些學(xué)術(shù)爭(zhēng)議。《中國(guó)道教通史》的編撰者們迎難而上,反復(fù)斟酌史料,實(shí)事求是地講述截止到2013年中國(guó)道教和海外道教的發(fā)展、研究歷史,站在了當(dāng)代道教歷史研究的前沿。比如陳耀庭先生撰寫(xiě)的“柳存仁的道教研究”,不僅詳細(xì)地記錄了柳存仁的生平,評(píng)判了他的功過(guò),而且還言辭懇切地告誡學(xué)人:“生活在當(dāng)今社會(huì)里,我們應(yīng)該怎樣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怎樣從事自己的事業(yè),從柳存仁的過(guò)去和后來(lái)的曲折經(jīng)歷里,明白我們今天應(yīng)該怎樣為國(guó)家、為民族、為世界,也為自己去做個(gè)堂堂正正的中國(guó)人,做個(gè)踏實(shí)嚴(yán)謹(jǐn)、奮發(fā)上進(jìn)的中國(guó)學(xué)人。”他這種以客觀而又充滿人文關(guān)懷的方式敘述歷史的方法,值得后輩學(xué)者認(rèn)真學(xué)習(xí)。
《中國(guó)道教通史》不僅為我們清晰地展開(kāi)了一幅跨越2500多年的道教起源、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的歷史畫(huà)卷,而且將道教置于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明進(jìn)程中,探討了道教對(duì)中國(guó)古代政治思想、學(xué)術(shù)思想、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技術(shù)、倫理道德觀念,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民俗和民間信仰,民族關(guān)系,以及對(duì)近當(dāng)代中國(guó)的國(guó)際交流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它的出版不僅有益于推進(jìn)當(dāng)前的道教學(xué)術(shù)研究,而且有益于弘揚(yáng)優(yōu)秀中華傳統(tǒng)文化,為解決人類(lèi)面臨的復(fù)雜問(wèn)題貢獻(xiàn)中國(guó)智慧。
(作者系哲學(xué)博士,四川大學(xué)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