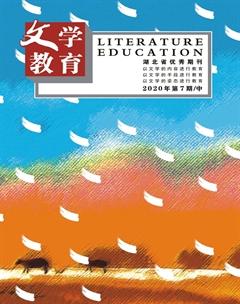論新時期《邊城》高校教學史中“人性美”經(jīng)典化歷程
內(nèi)容摘要:新時期以來,文學史對《邊城》的書寫集中在對“人性美”的評價,主要體現(xiàn)在整個湘西邊地的民風民情的正直樸素、忠厚善良的人性美書寫。這構(gòu)成了沈從文的文學理想——“人性的希臘小廟”。正因為沈從文《邊城》中“人性美”的書寫,使得沈從文一躍成為與魯迅、巴金、老舍等齊名的現(xiàn)代文學作家,在文學史中不可或缺。但是,《邊城》在現(xiàn)代文學史“人性美”經(jīng)典化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邊城》中的人物無不美好,從藝術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而言,是存在問題的。(二)近三十年來,文學史筆下的人物并沒有豐富發(fā)展,從一登上文學史舞臺,就已經(jīng)定格人物形象。(三)八十年代以來,文學史《邊城》書寫整體呈現(xiàn)的是一種較為美好的頌歌模式。筆者認為,在文學史書寫中,應當保持客觀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這對文學史發(fā)展以及作品都有裨益。此外,在高校教學上,我們應當側(cè)重《邊城》的“美育”教育作用,對學生進行審美闡發(fā),獲得大學生的“美育感知”與“美育反饋”,以此涵養(yǎng)大學生的性情、重塑民族品德,這為高校文學教學改革提供新方向。
關鍵詞:《邊城》人物形象 人性美 經(jīng)典化歷程 “美育”
《邊城》[1]寫作于1931年,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原載于1934年《國聞周報》第11卷中,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單行本。《邊城》作為重要的現(xiàn)當代小說之一,已入選中學教材與大學教材。那么,新時期以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邊城》人物形象有何發(fā)展?《邊城》在文學史中是否占據(jù)一席之地?《邊城》所反映的沈從文的文學地位又是如何變化的?由于學者論述中“翠翠”已經(jīng)闡釋得較為完整,因此,本文主要以新時期的14部文學史為主要研究對象,梳理除“翠翠”之外的《邊城》中人物形象生長脈絡,展現(xiàn)這一時期文學史學者對《邊城》的“人性美”的關注與評價以及《邊城》文學史概貌。
一.《邊城》“人性美”的形象建構(gòu)與經(jīng)典化歷程
自八十年代開始,文學史編者開始將目光轉(zhuǎn)向《邊城》中人物的淳樸、善良、美好等特性,老船夫、天保與儺送、順順、楊馬兵甚至擴展至“湘西人們”都成為文學史重點分析的人物形象,沈從文在他們身上建構(gòu)了質(zhì)樸、淳厚、善良、美好的人物形象。
老船夫是作品中僅次于翠翠的人物形象,1984年,在唐弢的筆下,老船夫以“淳樸忠厚”[2]的人物形象第一次登上文學史舞臺。1989年,郭志剛等稱贊老船工“純樸、誠實、堅忍”[3],在暴風雨之夜猝然倒掉又重修的白塔,象征著“一個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終結(jié)和對重造湘西未來的渴望”[4]。雖然此次并未提及老人與白塔的關系,但是在后文的文學史中,基本是將老船工的逝去與白塔的倒塌聯(lián)系起來,且多引用此處提出的白塔的象征意義。1991年,馮光廉等贊揚老船夫“忠于職守”、“重義輕利”、“古道熱腸”[5]。1993年,葉雪芬等書寫老船工,頌其“飽經(jīng)滄桑”“童心未泯,樂觀曠達,寬厚熱情”。葉雪芬等第一次將老船工稱作是“古老湘西的品格和道德的象征”,第一次將老船夫與白塔聯(lián)系在一起,“象征著一個原始而古老的湘西的終結(jié),而結(jié)尾白塔的重建,寄托著作者‘重造民族品格的愿望”[6]。凌宇和葉雪芬和幾乎同時注意到老船夫與白塔之間的聯(lián)系,以及他們的象征意義,所不同的是,凌宇認為“白塔的重修意味著作家對人際關系重造的理想主義期待”[7]。自此,老船夫與白塔就緊緊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論點也成為文學史家的定論,對后來的文學史書寫影響甚遠。此外,凌宇還發(fā)展了老船夫的性格特征,認為其續(xù)承了“‘信天守命的精神遺產(chǎn)”[8]。1999年,朱棟霖等延續(xù)了凌宇對老船夫和白塔的論斷,贊其“古樸厚道”[9]。2000年,程光煒發(fā)展了“白塔”坍塌的意義:“塔的倒掉由此預示了一個田園牧歌神話的必然終結(jié)”,甚至尖銳地指出“這就是現(xiàn)代神話在本質(zhì)上的虛構(gòu)的屬性”[10]。2002年,王澤龍等贊其“重義輕利,忠于職守,古道熱腸”[11]。2007年,朱棟霖等僅僅提及其“古樸厚道”,反而刪除了1999年所書寫的老船夫與白塔的象征意義。2009年,喬以鋼贊其“古道熱腸、豪爽大方”[12]。自此,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老船夫的形象就定格在“古道熱腸”、“豪爽大方”、“重義輕利”、“誠實堅忍”等美好品質(zhì)上,特別是文學史將老船夫與白塔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將其上升到民族品德的終結(jié)與重造上,不得不說是切中沈從文書寫老船夫的文學匠心了。
《邊城》中與翠翠構(gòu)成愛情關系的是天保與儺送,文學史家多喜將二者放在一起評價。在1983年,在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編寫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中,儺送和天保第一次正式登上文學史舞臺。編者贊揚兄弟二人的“性愛美”,主要體現(xiàn)在對愛情的“謙讓”、“忠誠”以及不以“家勢錢財門第等世俗觀念”作為擇婚的標準,而是以“感情”為標準選擇愛人。編者這樣評價:“以感情為重的戀愛觀,是同傳統(tǒng)的以家世利益決定男女婚配的門第觀念,形成了尖銳對立,這在客觀上是對舊婚姻關系做了否定和批判”[13]。1991年,馮光廉等頌揚天保與儺送“英武俊爽”、“知情曉義”[14]。1993年,葉雪芬等書寫他們“結(jié)實如老虎”、“不驕惰、不浮華”[15]。兩兄弟更被賦予象征意義,代表了湘西的年輕一代,他們“熱情、要強好勝、敢愛敢恨,充滿生命活力”[16]。同年,凌宇則用文化分析來探討儺送的選擇。在要碾坊還是要渡船的問題上,儺送拒絕了碾坊而選擇了渡船。碾坊,意味著“金錢物質(zhì)對婚姻的介入”,是“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表現(xiàn)形態(tài)”。渡船,則意味著“擁有生命的自主自由與婚姻的屬人本質(zhì)”[17]。凌宇實則贊頌儺送自主自由的愛情姿態(tài)。1999年,朱棟霖等贊揚天保“豁達大度”,儺送“篤情專情”[18]。2002年,王澤龍等寫他們“知情曉義,英俊倜儻”[19]。2009年,喬以鋼在葉雪芬等的基礎上發(fā)展了兩兄弟的性格,在“結(jié)實如老虎”、“不驕惰、不浮華”的基礎上,認為他們也富有“勇武雄強”的原始生命力,又浪漫癡情、忠厚重義,不乏溫柔與細膩。特別是他還發(fā)展儺送的文學史意義,從他的名字入手分析,談其身上遺留的“神性色彩”,贊其是“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順如小羊”[20]的男性美的理想化身。雖說在文學史中天保與儺送一起出現(xiàn),但是文學史家對儺送的關注更多一些,在兄弟二人皆勇武、誠樸的文學史形象之上,天保顯得更為豁達大度,儺送則彰顯其愛情的自主生命意識,以及遺留的神性色彩。
自1991年,馮光廉第一次注意到順順“慷慨好爽,敬老恤貧”[21],順順自此就登上了文學史舞臺。此后,順順的人物形象則集中在“大方灑脫、豪爽好義”[22]、“豪爽慷慨”[23]、“敬老恤貧,慷慨豪爽”[24]、“慷慨濟人、明事明理、正直和平”[25]。自此,就建構(gòu)起了順順較為清晰的文學史形象,即“慷慨豪爽”、“敬老恤貧”、“明事明理”、“正直和平”。
楊馬兵在《邊城》文學史書寫中僅僅出現(xiàn)了三次,且一般都只用簡短四字評價。1993年,葉雪芬與舒其惠第一次注意到了《邊城》中的最次要人物——楊馬兵,頌其“正直熱心”[26],1999年,朱棟霖贊其“熱誠質(zhì)樸”[27],2007年,朱棟霖在修訂版中又簡要分析了楊馬兵主動照顧翠翠的事實,贊其“品性高潔”[28]。
可見,無論是老船夫、天保與儺送、順順還是極不起眼的楊馬兵,在文學史學家的筆下都是品性純美的人物形象,沒有一絲缺點。因此,文學史編者將地方民族性格歸結(jié)為“正直、樸素、信仰簡單而執(zhí)著”[29]。1991年,馮光廉等高度贊揚《邊城》的子民,“無論老幼,不分富貧,一律都保持著忠厚善良、誠摯淳樸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特別提及“酒家屠戶,都是君子風度。往來渡客,無不樂善好施”,“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30],這句話在此第一次出現(xiàn),但在后來的文學史中被多次引用,成為定論,成為論述《邊城》不可或缺的關鍵句。朱棟霖[31](1999、2007)、王澤龍、劉克寬[32](2002)、喬以鋼(2009)[33]都不約而同地引用了這個觀點[34]。
二.文學史經(jīng)典:《邊城》的不可或缺
可見,文學史中的《邊城》書寫的所有人物無不美好,無不質(zhì)樸,無不善良。沈從文在《邊城》中書寫的人物為什么都善良、質(zhì)樸?他的用意究竟何在?這就涉及到沈從文塑造這些人物的匠心所在,三十多年來,文學史作家一直一致試圖回答這一問題。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言:“二十年來的內(nèi)戰(zhàn),使一些首當其沖的農(nóng)民,性格和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質(zhì)樸、勤儉、和平、正直的型范”[35]。《邊城》所展現(xiàn)的人性的美好,民性的淳樸,構(gòu)建的深厚豐盈的理想東方人格范式,正是成為沈從文想要改造國民性的一個重要途徑。其實,從80年代起,就有文學史作家提出作品中的“人性美”為沈從文及《邊城》平反。1987年,錢理群等人一反50年代以來的以階級定位文學史,對《邊城》作詳細分析,從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動力與思想內(nèi)核出發(fā),認為沈從文在《邊城》中“設想用農(nóng)村原始的人情美來改造社會,來恢復民族性格”,彰顯沈從文的“正義的、人道”的愛國理想和“‘重造民族品德”[36]的理想,為沈從文及《邊城》的文學地位平反。自此,《邊城》成為平反沈從文文學史地位的重要例證。劉勇直指沈從文小說創(chuàng)作的中心是“表現(xiàn)人性”,展現(xiàn)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7],作為構(gòu)筑善與美的“神廟”基地[38]。朱棟霖等也認為沈從文從“從道德視角出發(fā),為湘西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觀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來走向”[39]。這也基本成為文學史作家的共識,在《邊城》湘西邊地的“愛”與“美”被發(fā)現(xiàn)的過程中,《邊城》的地位也從文學史的邊緣地位一躍成為與《子夜》、《家》齊名的重要現(xiàn)代作品,《邊城》迎來了全面新生。
1983年,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編將沈從文與張恨水放置在一起并列專章開始,沈從文和《邊城》的地位就已經(jīng)開始在文學史中逐漸上升。但這一時期的多數(shù)文學史論述沈從文時喜將其與其他作家放置一起,如唐弢將“魯彥”與“沈從文”[40]放置同章,郭志剛等將“沈從文與李劼人”放置于同一章[41],馮光廉、劉增人將“廢名與沈從文”放置于同一節(jié)[42]。1993年,在葉雪芬、舒其惠將“沈從文的小說”單列一節(jié),這也標志著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終于第一次獨立成節(jié)。同年,凌宇將沈從文放置在“京派”小說下,獨立成節(jié)。1998年,新版《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將沈從文專章論述,這是沈從文第一次被列為專章作家進行論述,由此開始,沈從文在文學史中開始有了獨立的地位。1999年,朱棟霖的文學史書寫中,《邊城》在文學史上第一次單獨成節(jié)。這意味著《邊城》在文學史上終于占得一席之地。此后,在文學史中,沈從文基本單獨成章,而《邊城》基本單獨成節(jié)。自此,沈從文及《邊城》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經(jīng)典作家及作品。
三.結(jié)語
可見,新時期以來,隨著翠翠、老船夫、儺送等一系列人物被文學史作家不斷開掘,文學史已經(jīng)形成對這一系列《邊城》人物的共識,即“善良、淳樸、重義輕利、自信守約”等良善品質(zhì),這些人物形象的發(fā)現(xiàn)與建構(gòu)不斷驗證著沈從文書寫《邊城》的“‘重造民族品德”[43]的社會理想。因此,《邊城》與沈從文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文學經(jīng)典之一。可是,在《邊城》的“人性美”文學史經(jīng)典化歷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邊城》中的人物無不美好,從藝術塑造人物形象的角度而言,是存在問題的。其實,我們明明可以指出翠翠的膽小,老船夫過于順天應命,天保出走時的負氣沖動……他們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可是近20部文學史,卻僅有郭志剛、孫中田在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修訂版)提到《邊城》中人物的性格“缺乏一種內(nèi)在的矛盾和沖突”,呈現(xiàn)出一種“扁平”狀態(tài),但他又筆鋒一轉(zhuǎn),立刻為《邊城》開解,“但人物性格單純到極致也便成了一種凈化的美”[44]。這說明文學史作家不是沒有留意到沈從文創(chuàng)作人物的單一性,但是卻礙于沈從文的文學用意無法對其進行批判,這是問題之一。(二)近三十年來,文學史筆下的人物并沒有過多的豐富發(fā)展,從一登上文學史舞臺,就已經(jīng)定格了他們的人物形象。這期間自然有沈從文創(chuàng)造人物的匠心,文學史作家不好進行干涉與發(fā)展。但是否也值得我們反思,在分析文學史作品人物形象之時,是否需要引進更多的文學理論來深析人物形象?是否應該對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不足提出較為中肯的批判?(三)在80年代以后的《邊城》文學史書寫,呈現(xiàn)的是一種較為美好的頌歌模式。筆者認為,在文學史書寫中,還是應當保持客觀的問題意識和批判意識,這對文學史發(fā)展以及作品都有裨益。此外,《邊城》重新發(fā)現(xiàn)湘西的“人情美”與“人性美”,彰顯的“愛”與“美”,小說中的牧歌情調(diào)與桃花源式的塑造十分契合當下高校大學生的品德培養(yǎng)目標,可以此涵養(yǎng)他們的審美觀與世界觀,這對提升當代大學生的審美教育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高校文學史教學上,我們應當側(cè)重《邊城》的“美育”教育作用,對學生進行審美闡發(fā),以獲得大學生的“美育感知”與“美育反饋”,以此涵養(yǎng)大學生的性情、重塑民族品德,這也可作為開拓高校文學教學改革的新方向。以上,希冀為今后《邊城》文學史發(fā)展以及《邊城》高校教學提供一些歷史資料參考與建議。
參考文獻
1.沈從文.邊城[M].上海:上海生活書店初版,1934.
2.丁易.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
3.唐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4.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下)[M].濟南: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1983.
5.唐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簡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6.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
7.郭志剛、孫中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修訂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8.馮光廉、劉增人.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9.葉雪芬、舒其惠.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程[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1993.
10.凌宇、顏雄、羅成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
1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2.劉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M].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
13.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4.程光煒、吳曉東、孔慶東.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15.王澤龍、劉克寬.中國現(xiàn)代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6.喬以鋼主編.現(xiàn)代中國文學(1989-1949)[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
17.朱棟霖、朱曉進、吳義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2012)[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注 釋
[1]沈從文:《邊城》,上海: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版。
[2]唐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簡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87頁。
[3]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頁。
[4]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頁。
[5]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238頁。
[6]葉雪芬、舒其惠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程》,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1頁。
[7]凌宇、顏雄、羅成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28頁。
[8]凌宇、顏雄、羅成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26頁。
[9]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1頁。
[10]程光煒、吳曉東、孔慶東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頁。
[11]王澤龍、劉克寬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12]喬以鋼主編:《現(xiàn)代中國文學(198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頁。
[13]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下),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1983年5月版,第78頁。
[14]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頁。
[15]葉雪芬、舒其惠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程》,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1頁。
[16]葉雪芬、舒其惠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程》,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1頁。
[17]凌宇、顏雄、羅成琰:《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226頁。
[18]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1頁。
[19]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頁。王澤龍、劉克寬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20]喬以鋼主編:《現(xiàn)代中國文學(198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頁。
[21]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頁。
[22]葉雪芬、舒其惠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程》,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1頁。
[23]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1頁。朱棟霖、朱曉進、吳義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20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頁。
[24]王澤龍、劉克寬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25]喬以鋼主編:《現(xiàn)代中國文學(198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頁。
[26]葉雪芬、舒其惠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教程》,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1993年3月版,第151頁。
[27]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1頁。
[28]朱棟霖、朱曉進、吳義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201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頁。
[29]1983年,在山東師范大學附設自修大學編寫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編者頌揚“湘西人民的樸素政治、互助互愛的美德”。1987年,錢理群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總結(jié)地方民族性格,即“正直、樸素、信仰簡單而執(zhí)著”。1998年,錢理群《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夸贊其“正直、樸素、信仰簡單而執(zhí)著”的地方民族性格。
[30]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頁。
[31]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1頁。
[32]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頁。王澤龍、劉克寬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頁。
[33]喬以鋼主編:《現(xiàn)代中國文學(1989-1949)》,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頁。
[34]注:1999年,朱棟霖等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認為“茶峒民性的淳厚”,這里的人們“輕利重義、守信自約”,“酒家屠戶,來往渡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風”,“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2000年,程光煒等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認為小說中的人物都具有“淳樸、美好的天性”。2002年,王澤龍等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書寫“酒家屠戶,來往渡客,也都樂善好施,具有君子風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2007年,朱棟霖等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2012(上)》書寫茶峒民性的淳厚”,這里的人們無不“輕利重義、守信自約”,“酒家屠戶,來往渡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風”,“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還更可信任”。2009年,喬以鋼主編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1989-1949)》認為《邊城》彰顯“人性美的典范”。《邊城》眾人“既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人還更可信任”。
[35]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頁。
[36]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322頁。
[37]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劉洪濤,楊瑞仁編:《沈從文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頁。
[38]劉勇:《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頁。
[39]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1917-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12頁。
[40]唐弢:《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簡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頁。
[41]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1頁。
[42]馮光廉、劉增人主編:《中國新文學發(fā)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頁。
[43]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322頁。
[44]郭志剛、孫中田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07頁。
基金項目:福建省教育科學“十三五”規(guī)劃2017年度重點課題《<邊城>高校教學史(1951-2014)》(FJJKCGZ17-179)階段性成果;2018年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養(yǎng)計劃“京派散文文體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介紹:鄭麗霞,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