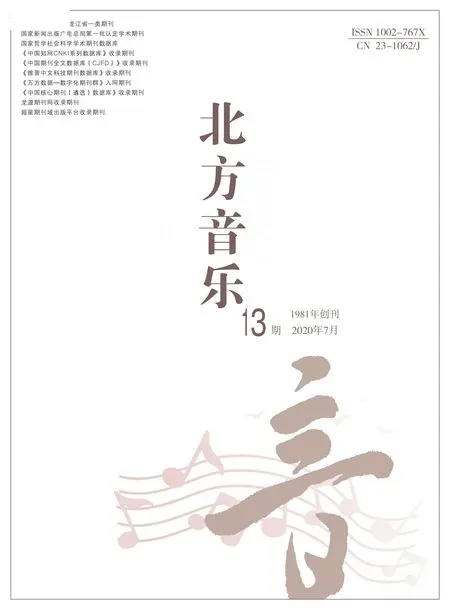談舒曼“迷娘曲”中詩與樂的結合及情感表達
方賢君
(云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藝術歌曲是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浪漫主義運動影響下產生的一種獨立聲樂體裁,由詩歌、聲樂旋律以及獨立的伴奏(鋼琴聲部)構成,側重人物內心的表達,歌詞多半用著名的詩歌,作曲技法和表現手段較復雜,且伴奏占有重要的地位。
舒曼是德奧浪漫主義音樂的代表,他有較高的文學鑒賞水平和詩人般的幻想氣質,在他的藝術歌曲創作中意境更為含蓄、細膩和深邃。他更側重內心的刻畫,擅長通過細膩的音響變化來發掘人物的內心,烘托意境。“迷娘”是歌德的著名長篇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的人物,她以少女的形象出現在小說中,雖然只有十四五歲,但卻性格極其敏感復雜,悲觀且充滿矛盾。舒曼為歌德小說中的四首相關迷娘的詩歌都進行了藝術歌曲的創作,分別是《你知道這個地方嗎?》(kennst du das Land),《只有懂得相思的人》(Nur wer die Sehensucht kennt),《讓我別說,讓我沉默》(hei? mich nicht reden),《讓我照耀》(so lass mich sheinen),這四首作品都屬于舒曼晚期作品(1849—1856),風格與1840年(舒曼歌曲年)的大量藝術歌曲的創作風格略有不同,音樂的表現戲劇沖突更強烈,寫作手法尤其在和聲以及節奏節拍的運用上更為大膽、不規則。以下本文將對其中一首迷娘曲《你知道這個地方嗎?》(kennst du das Land),從詩歌本身出發,結合音樂表現與情感表達進行其風格特征上的把握和探討。
詩與樂結合的這種創作觀,德奧藝術歌曲既是首創又具代表意義,舒曼藝術歌曲是德奧藝術歌曲的代表,具有德奧藝術歌曲的共性,同時又滲透出自己的強烈個性。
一、詩歌的內容與內涵
Kennst du das Land 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ühn,你知道嗎?那檸檬花盛開的地方
Im dunkeln Laub die Goldorangen glühn,茂密的綠葉中,橙子金黃
Ein sanfter Wind vom blauen Himmel weht,藍天上從來宜人的和風
Die Myrte still und hoch der Lorbeer steht? 桃金娘靜立,月桂梢頭高昂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你知道那個地方嗎?前往,前往
Dahin m?cht’ ich mit dir,我愿跟隨你
O mein Geliebter,ziehn.愛人啊,隨你前往
Kennst du das Haus? Auf S?len ruht sein Dach,你知道那個房子嗎?圓柱成行
Es gl?nzt der Saal,es schimmert das Gemach,萬堂輝煌,居室寬敞明亮
Und Marmorbilder stehn und sehn mich an: 大理石像凝視這我
Was hat man dir,du armes Kind,getan? 人們把你怎么了,可憐的孩子?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你知道那個房子嗎?前往,前往
Dahin m?cht’ ich mit dir,我愿意跟隨你,
O mein Beschützer,ziehn.恩人啊,隨你前往
Kennst du den Berg und seinen Wolkensteg? 你知道嗎?那云徑和山崗
Das Maultier such im Nebel seinen Weg,驢兒在霧中覓路前進
In H?hlen wohnt der Drachen alte Brut: 巖洞里有古老的龍種的行藏
Es stürzt der Fels und über ihn die Flut.危崖欲墜,瀑布奔忙
Kennst du ihn wohl? Dahin! 你可知道那座山崗?前往,前往
Dahin geht unser Weg! 我愿跟隨你,
O Vater,la? uns ziehn! 父親啊,隨你前往
從內容上來說,詩歌先從低婉沉郁的表達到充滿神秘的思索,再到滿懷憧憬與懇求,最后是催促和充滿渴望。第一段是對意大利的風光進行了描繪,“月桂樹”“桃金娘”“檸檬樹花”,陽光普照,輝煌燦爛的風光,這都是意大利特有的風光。迷娘出生于意大利,表達的是對家鄉的思念和向往之情。第二段詩歌描繪了用圓柱撐起房頂的金碧輝煌的房子,房間里還陳設著大理石雕像,這是迷娘的童年記憶,她曾經出生于意大利的一個貴族家庭,是貴族與自己妹妹的私生子,童年時被拐賣,成為雜技團的鋼絲演員,經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后被小說中的主人公威廉·邁斯特贖買,詩歌中的“愛人”“恩人”“父親”都是迷娘對男主人公威廉·邁斯特的親切稱呼,邁斯特的解救讓迷娘脫離了苦難的生活,在男主人公身邊度過了一段安穩的時光,她對邁斯特有著一種感恩、愛慕、崇拜又視為父親的復雜交錯的情感,痛苦而糾結。第三段對“群山”“迷霧”“巖石”“洞穴”的描繪,是迷娘憑借記憶對童年被拐賣時走過的深山迷路的回憶,充滿神秘的思索,詩歌中用較多次數強調的“dahin”表達一種層層遞進的迫切的渴望。歌德在小說中從迷娘對威廉·邁斯特的自述角度呈現這首詩歌,將迷娘的謎一樣的身世、對家鄉的思念、對男主人公的復雜的情感以及憂郁的人物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音樂的節奏與節拍
詩歌的節奏包括重音和時長,取決于詩歌所用語言的內在規律,在朗誦中的韻腳時長的起伏變化。節拍節奏是舒曼的音樂中最擅長運用的情感表現重要元素,這首藝術歌曲則體現了他將個人情感表達融入于音樂節拍節奏與詩歌節奏的把控程度。從聲樂聲部來看,他在詩句的語調中又加入了明顯的宣敘性,音樂節奏呈現出不規律性和樂句結構的多變性。舒曼讓聲樂旋律不僅只是對詩歌原本朗誦律動節奏的遵循,還包含了通過自身的文學鑒賞水平對詩歌的進一步理解和處理,讓詩歌的節奏在音樂旋律中做出了適當的變形,使其在不改變語言外形的前提下將詩歌置放在音樂中延展,使詩歌服從音樂。正常的旋律節奏與詩歌節奏重音的匹配服從關系不能完全表達情緒和意境,因此需要通過節拍的變形來實現,表達人們內心的矛盾緊張焦慮以及詩歌中搖擺不定的心理狀態和復雜感情。
整首歌曲舒曼采用三段體的曲式對詩歌進行陳述,且三個段落的節拍律動保持統一性,幾乎沒有太大的變化。全曲以3/8貫穿其中,這種節拍的律動給人一種旋律的緊湊感,更容易表達一種情緒的層層遞進,迫切和催促感。第一句kennst du das Land,wo die Zitronen blühn.從音樂旋律上的節奏重音邏輯來分析,kennst出現在了第一拍的后半拍,對原本詩歌節奏中的重音進行了位移,弱化了kennst的重音,而強調了Land;第二句從音樂節奏上弱化了wo,把重音放在了了“Zitronen”的第二個音節上,以及加強了dunkeln,Gold這些形容顏色的重音,從而給人一種畫面感,如一幅充滿色彩的意大利自然風光呈現在眼前。每一句只強調一個邏輯重音和所描繪的名詞,而弱化了動詞的重音,使整個詩句在音樂中更具宣敘性,也更自然流暢。在吟誦性的旋律下再配合內省的簡潔的和諧分解式織體,烘托出一種寧靜的氣氛,表達一種語言所不能表達的深邃意境。接下來的聲樂旋律延續之前的節奏律動,形成聲樂聲部的律動統一。但鋼琴聲部的節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運用了連續的三連音重復十六分音符的方式進行。這種節奏進行與上方的聲樂聲部旋律產生了節拍的失協性,出現了“二對三“”以及“四對六”的沖突感,用這樣的織體節奏來做烘托環境的描寫,并且與聲樂聲部形成對立失協,呈現出一種搖擺不定的心理狀態和多重的復雜情感,表現情緒上的焦慮、渴望與不安。每一段的開頭趨于平靜的節奏型,表現出對“Land”“Haus”“Berg”的神秘感和思索,漸漸轉換為三連音的鋼琴聲部做環境的渲染和鋪墊,將情緒推動到“dahin”的至高點上,激情彭拜,表現出急切的渴望,最后回歸對于“Geliebter”“Beschützer”“Vater”的漸漸委婉而沉郁的請求。這樣的處理方式將迷娘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呈現出來,是從單純的詩歌朗誦中不能夠做到的。
三、和聲伴奏的運用與襯托
鋼琴伴奏是德奧藝術歌曲在音樂形式上對藝術歌曲的最大貢獻,也構成了藝術歌曲的基本特點之一,其實對于“鋼琴伴奏”的這個概念,更為準確的應該稱之為“鋼琴聲部”,它與聲樂聲部是呈一體性的。在舒曼的藝術歌曲中,鋼琴是音樂表現的利器,鋼琴聲部的結構設計精致復雜,和聲運用成熟,織體音型則與詩歌意境及聲樂聲部完美貼合。

歌曲的前奏舒曼運用了分解和弦的g小調下行,展現出調性的暗淡色彩。兩個屬和弦中間用體現小調特征的三級曾三和弦,以及小下屬七和弦連接,形成了特殊進行,補充終止對第一小節的下行分解和弦進行低八度的重復,營造音樂的情緒。三個段落中的兩次間奏基本相同,延用前奏的織體,用一種簡潔的方式形成了音樂語言上和情緒上的統一。
三個段落的聲樂聲部都采用了模進的方式,音階式的上行結合純四度的跳進,鋼琴聲部以三連音和弦重復的手法,十六分音符附屬和弦的調式變音半音的進行,調性在g—?B—g—c—g中轉換,并隱藏著和弦外音作陪襯。半音和聲、和弦外音、變和弦的使用,減弱了中心調的感覺,短時間的調性游移增強了音樂的張力,弱化了某一調性的感覺,使和聲更有張力感。在伴奏的織體中雖采用了密集和厚重的十六分音符,但依然從主音中呈現出抒情的線條性。

這種和聲伴奏的運用營造出一種動蕩不安的感覺,表現情緒上的波動和忐忑。這樣的運用方式不同于古典時期輕盈透明的織體特征,伴奏提供了一種將聲樂與器樂相融合的音樂效果和構造,使詩歌的每一個細節在音樂中都有特定的表現,鋼琴營造并維持著整首歌曲的情緒基調,從而與演唱者形成一種平等的合作者關系,與聲樂旋律形成互動關系,這也是浪漫主義時期德奧藝術歌曲的重要風格特征。
四、演唱中的情感表達與音樂表現
結合這首作品源于歌德寫作的詩歌背景和表現內容以及舒曼寫作的音樂表達來看,這首歌曲的情感表達是極其細膩和復雜的,復雜的人物性格必定表現出復雜的人物情感。舒曼自身也具有內心糾結敏感的性格氣質,他借助于音樂中的人物事件,也是對自己內心世界的表達,詩歌與音樂體現了一種充滿疑慮與迷離的主觀情感的內在幻想,自我構建的唯美世界,這也是典型的浪漫主義心態。因此,我們在演唱中,要設身處地地去體會舒曼的人文世界,以他的角度去講述迷娘這個人物角色并展現性格。細膩的情感表達是至為重要的,整首詩歌透露著迷娘對意大利家鄉的渴望與憧憬、對童年生活的回憶和對男主人公威廉麥斯特的依賴與依戀,視作為“愛人”,“恩人”和“父親”的復雜情感,并且層層遞進。因此,每一段的速度和情緒又應有所變化,第一段趨于平靜和低婉的娓娓道來,第二段感情近一步升華,速度可比第一段稍快,但應在有節制的速度范圍內控制。迷娘想起來童年的憂郁,“was hat man dir,du armes Kind getan?”是充滿神秘的思索,仿佛預示著迷娘的迷一樣的身世,“armes Kind”便是自己,懇請著“愛人”可以與她一同回童年的住所,向往而滿懷憧憬。第三段是歌曲的高潮,情緒上應比前兩段更為激動,在速度上可做比前兩段更快的處理。段落開始先是對充滿迷霧的山間小路的描寫,“Maultier”在霧中看不清自己的路,就如同迷娘當初被拐賣時在山間的迷路,從情緒中應該呈現一種呆滯感,一種順從的遲鈍。這也是對后來的群山、洞穴、巖石實物的描線形成一種情緒上的強烈對比,最后三次的“dahin”則一次比一次強烈和迫切,并在滿懷憧憬中結束。三段的音樂處理在演唱的音色和情緒上都要有鮮明的對比,從而才能表現戲劇性的沖突和畫面感,所有的名詞和形容詞需要生動化,如第二段中對“Haus”的描寫,有圓柱支撐、明亮的大廳和大理石像的房子,這些事物本身就是宏偉輝煌的,所以應該運用飽滿的音色來體現音樂形象,而第三段中的“Wolkensteg”“Nebel”“Maultier”的描繪,是神秘朦朧地,因此,在音色的運用上也應該更為縹緲和暗淡的音色。此外在語言上,演唱中更是要突出語言的清晰性,掌握詩歌中的韻律及字的邏輯重音。歌唱本身就是語言的藝術,是帶著音樂的朗誦,所以,只有在充分理解歌詞的含義、清楚的咬字發音基礎上,才能更準確地表達音樂和詩歌的內涵,傳遞正確的情感和情緒,使聽眾產生感情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