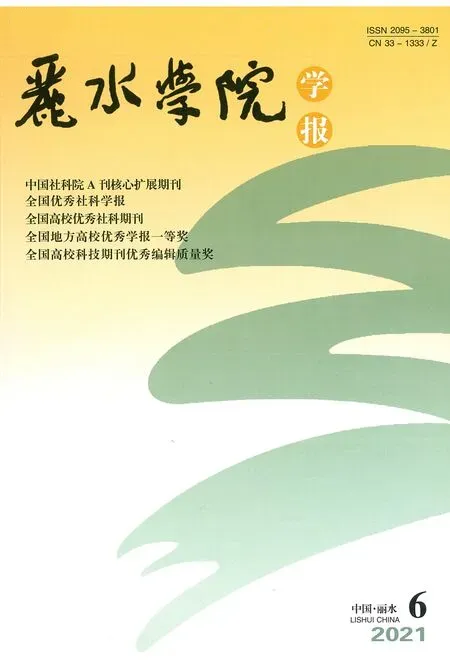論中國共產黨收入分配的理念與實踐
陳 婷
(上海政法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201701)
收入分配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中,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具有剝削屬性的價值體系逐漸消亡,社會經濟交往規則將會得到實質性提升。由此,他們提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分別實行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持馬克思主義關于收入分配的價值取向和目標,孜孜不倦地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分配正義。
一、革命和建設時期收入分配的均中求富理念與實踐
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鑒于經濟社會資源的有限性,為確保社會成員的基本社會需求,樹立了“均中求富”的價值理念,首次確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并始終堅持將其作為黨領導人民進行經濟社會建設的一項重要原則。
1.均中求富:收入分配的價值取向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深切感受到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中國人民的饑寒交迫,積極參與工人、農民運動,領導中國人民通過武裝斗爭推翻暴力的反動政權,廢除私有制,讓工人農民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同時,積極提高工人、農民的收入,改變人民生活貧困的狀況。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通過實施不同的土地政策和其他財產分配政策,確保不同時期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所需,采取的是一種相對平均主義的經濟分配原則。
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中,毛澤東等人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收入分配理論的設想,堅持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原則,確立了與此對應的收入分配理念。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對不同性質的所有制予以不同的分配原則,對國有企業和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工商業分別實行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社會的生產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公有制占據了主導地位。毛澤東提出要將收入分配的宗旨放在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上,“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1]。同時,毛澤東高度警惕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在他看來,“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2]。由此,體現出了毛澤東等人“均中求富”思想。“均中求富”的“均”不是追求絕對的平均主義,而是要求兼顧公平與效率。毛澤東既反對貧富兩極分化,又堅決反對平均主義。他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平均主義,那只是某些階級的一種幻想,絕對平均主義不僅有害于革命斗爭的勝利,而且會挫傷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分配也應根據生產和生活需要,遵循“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絕無所謂的“絕對平均”。“均中求富”的“富”體現的是共同的富。中共中央為了使人們盡快富裕起來,通過設計人民公社、公有制企業等體制,實行“按勞分配”,努力調動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使他們盡快富裕起來。“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3]對此,中共中央采取統籌兼顧的辦法,注重協調各方利益,反對將集體經濟活動管得太多、統得太死,鼓勵全體人民通過自身勞動,實現共同的“富”。
社會主義建成后,伴隨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列主義基本分配原理,以前蘇聯分配實踐探索為參照,結合中國的國情,逐步建立起了相應的計劃分配體系,形成了系統的分配思想。總而言之,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走的是“均中求富”的發展道路[4]。
2.工分制與工資制度的改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實行的按勞分配方式主要有:計件工資制、企業成員以“身份股”的形式入股分紅制、按質分等的個人分紅制。這種分配標準支持了蘇區、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經濟建設,調動了廣大群眾的勞動積極性。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農村地區基本確立起了按勞分配原則,其主要形式是工分制和勞動日制。人民公社運動開始,按勞分配主要是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形式(供給部分占三成,工資部分占七成)。但實際操作過程中,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壓得很低,許多公社因缺錢造成無工資可發的現象。此外,在食品上采取分配供給制。由于供給部分比例太高,結果干多干少都是吃一樣的飯。對此,1961 年中共中央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要求嚴格按勞動工分進行分配。隨后,在人民公社中實施了四年的“大鍋飯”停止了。除了供給制外,分配核算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負責統一分配的形式也容易帶來一些地方瞞產私分的弊端,極大挫傷了社員的勞動積極性。1962 年,中共中央再一次修改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重新強調農村應該盡可能在大體上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規定農村生產隊(生產小隊) 對社員應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質量與數量)公平合理地支付報酬。農民在生產隊內部按工分進行分配,大體上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政府直接管理收入分配的對象主要是國營企業、機關和事業單位等,分配制度既包括革命戰爭時期采用的供給制,也包括逐步實施的工資制。由于分配制度自身設計不合理和不能適應現實變化等原因,分配領域出現了一些混亂狀況。自1952 年開始,全國開始了第一次工資改革,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工資和獎勵制度,把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一起來,將供給制待遇納入工資制待遇之中。具體包括,國家不再統包承擔國家工作人員、企事業單位職工及其家屬的一切生活費用等,這些費用均由個人負擔。與此同時,國務院制定了國家工作人員的新的工資標準,將供給制統一改為貨幣工資制,并以“工資分”作為統一的計量單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級別工資等級制度,將工資標準分為30 個等級。這一改革有效地調動了勞動積極性。1956 年,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工資制度又進行新一輪的改革。這次改革主要是為了克服分配方式上的平均主義,重申按勞分配原則,使勞動者的工資報酬取決于勞動的數量、質量及對社會的貢獻。經過改革,取消了物價津貼制度和工資分制度,在產業部門內實行八級工資制,調整了不同產業、不同地區之間的一些不合理工資關系。此外,中共中央根據不同地區的物價和生活水平,在全國劃分了11 類工資區。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在部分企業推行并改進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對超額勞動的職工發放獎勵工資,對特殊環境條件下的勞動者發放津貼。工資形式的多樣化提高了干部職工的工作積極性,推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二、新時期收入分配的共同富裕理念與實踐
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立足于中國實踐,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基礎上,允許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突破了僵化的社會主義分配形式,將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一,并提出了“先富帶后富”的“共同富裕”實踐路徑。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張力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通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來激發社會競爭與活力。
1.共同富裕:收入分配的新思路
鄧小平站在對社會主義本質性認識的高度,多次強調社會主義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5]286他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在共同富裕的目標導向下,可以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裕起來。圍繞這一新思路,中共中央在收入分配上進行了改革。
中共中央依循“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理路,在收入分配上采取了更具現實性的實現方式和實施策略。其一,在分配方式上進行了變革。為了轉變平均主義思想、變革政府主導的分配方式、激發社會生產活力,中共中央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逐步采取以市場為主導的分配方式,開始注重物質激勵,主張勞動報酬應向多勞者、貢獻大的人傾斜。“對發明創造者要給獎金,對有特殊貢獻的也要給獎金。搞科學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對他的發明創造給予獎勵外,還可以提高他的工資級別。”[6]102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探索了適應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現實的分配結構,即允許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實現分配原則逐漸向“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方式轉變。其二,在收入分配策略上進行了調整。針對改革開放前存在的弊端和國民經濟發展不足的現實,中共中央通過激勵人民群眾解放思想、大膽創新,期望更快更大程度地激發生產力發展潛力。鄧小平認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6]152國家先鼓勵和支持發達地區加快發展步伐,率先富裕起來,再通過制定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給予貧困落后地區各個方面的幫助,實現共同富裕。總體而言,這一時期黨的分配思想不僅涵蓋了對個人收入適度合理差距的認可,采取的是讓“先富者”帶動全民“共同富裕”的發展步驟,而且也包含著不能導致兩極分化的深義。
收入分配要在“兩極化”與“適度化”之間找到平衡點,還需依據不同時期的實際情況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1993 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2002 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7]。 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一改十余年不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說法,第一次正式提出“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由此可見,新時期以來,收入分配堅持共同富裕理念的指引,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實現了由“注重效率”到“公平與效率相統一”的演進。
2.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工資制度改革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深入地討論農業的問題。我國率先從農村展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現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建立,使農民的收入分配方式由原來的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工分制轉變為將勞動努力程度和勞動成果作為分配依據的按勞分配方式。中共中央為克服平均主義,要求公社各級經濟組織嚴格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計算報酬,認真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以家庭為單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戶家庭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其經營收入按照“繳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方式獲得。在廢除人民公社、實施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將最初的臨時性的分產到戶的土地承包方案最終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了下來,并保持長期不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農民的經濟利益,有利于農民收入的穩定與增長。
緊隨農村收入分配改革,城市的收入分配也開始逐步打破原有的分配模式,朝著效率優先的方向穩步推進。國家針對城市收入分配的問題,采取了漸進式改革的方針政策。1982 年,黨的十二大指出,必須制止不顧生產銷售實際情況濫發津貼和各類獎金等現象,職工的平均收入增長水平不能高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1983 年之后,國家擴大國企的自主經營權,推動國企進行利改稅改革。在企業利潤微觀分配方面,國家也制定了一些調動企業職工勞動積極性的利益激勵政策,如盈虧包干責任制、計件工資、浮動工資和記分計獎等。1985 年,國營大中型企業開始實行職工工資總額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的辦法,國家以分級管理的辦法發放企業工資。隨后,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工資制度和正常增長的機制,根據各自不同的性質特點改革了原有的工資制度,一些部門和企業可以根據實際經濟效益,自主決定內部職工的分配方式和工資水平。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了職工的個人收入。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允許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存在其他的分配方式,這就使得收入分配方式逐漸走向多元。具體而言,除按勞動所得、個體勞動所得和經營管理者的勞動收入之外,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均可參與分配,利潤、利息、股息、債息、租金、分紅等合法的多種非勞動收入也得到批準和認可。不同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生產要素的收入分配的多寡由該生產要素的貢獻大小決定,貢獻越大,獲得的報酬就多;反之,報酬就少。2003 年,中共中央在進一步堅持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的基礎上,加強了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管,在強化個人所得稅征管的基礎上,規范職務消費,健全個人收入監測辦法。推進事業單位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規范國家公務員工資制度,推進事業單位分配制度改革。這一段時期,我黨在收入分配的實踐方面,因創新了原有的收入分配理念,從而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極大地激發了社會活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新時代收入分配的共享發展理念與實踐
自新時期以來,在收入分配的探索方面,鄧小平就曾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5]364。此后,胡錦濤同志進一步提出:“建構和諧社會,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9]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貧富不均、階層固化等頑瘴痼疾,提出了“共享”這一新發展理念。共享發展理念旨在以“消除貧困”“縮小分配差距”“打造公平社會”為抓手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對共同富裕價值理念的繼承與超越。如何讓人民共同享有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解決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毫無疑問成為關鍵所在。在共享發展理念的引導下,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收入分配的認識不斷深化,并進行了一些新探索、新實踐,提出了一些新論述、新思想,促進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創新發展。
1.共享發展:新時代收入分配的新指引
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分配不合理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通過“兩個同步”“兩個提高”,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機制,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要讓人民群眾公平合理地分享改革發展帶來的成果。
共享發展著力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與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集體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誠如習近平所指:“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8],“改革發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10]。與“共同富裕”相比,“共享發展”價值理念對收入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新要求體現于相關制度的設計與構建、目標實施的清晰度與精準度、先富對后富的幫扶關系等方面。新時代的“共享發展”價值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集中體現,是對新時期“共同富裕”理念的豐富與升華。
在“共享發展”價值理念的指引下,新時代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是更加注重分配的正義和公平,分配改革的重心由原來的一部分先富起來轉變為讓所有社會成員公正地共享發展成果。對此,習近平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來形象化說明發展與分配的問題。他明確要求,“蛋糕”不僅要做大,更要分好。習近平同志強調效率和公平的辯證統一,破解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不斷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解決好收入差距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11]因此,在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過程中,不僅要想方設法地夯實經濟基礎,更要注重解決其中的分配正義問題,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價值追求。
2.“三權分置”與增加一線勞動者報酬共存
進入新時代,在農村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我國推出了“三權分置”的改革措施。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三權分置”創造性地破解了制度剛性約束與保持經濟活力之間的矛盾,探索出了農地經營權資本化的多種實踐方式。“三權分置”完全基于農戶自愿互利原則,在保證耕地使用用途不變的前提下,將經營權從使用權中分離開。農戶也可以選擇自己耕種,從事兼業化經營,保留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由市場主體基于經濟理性的完全市場行為,通過競爭內生出適合不同地形地貌、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的最優種植模式。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加強宅基地管理,穩重謹慎地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分置有效實現形式。“三權分置”賦予農村經營者剩余索取權能,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拓展了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的上升空間。
中共中央將穩步提高勞動者收入作為新時代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內容,并開始著手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其主要內容包括“健全科學的工資水平決定機制、正常增長機制、支付保障機制,推行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12]。中共中央強調:“提高就業質量,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13]黨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也提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把蛋糕分好,增加一線勞動者收入,切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這實質上是讓社會增長的財富更多地流向千家萬戶,讓普通勞動者,尤其是廣大青年,在“勤勞致富”的道路上更有奔頭,從經濟發展中獲取更大的紅利。增加一線勞動者的工資報酬,是我們黨不斷完善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按貢獻分配激勵機制的一個重要體現,旨在打造和諧的分配格局,實現勞動者收入與其付出的正向刺激效應。為了確保工資增長機制的順利實施,黨委及政府部門采取了多種措施。其一,對不同企業進行分類指導,共同修訂勞動合同內容,明確權利義務,保障勞動者依法享受應有的福利待遇,將勞動者幸福程度的提升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指標。其二,先后出臺并實施了多部維護勞動者工資權益的法令法規,如《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等。其三,各地政府提高當地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標準,保障勞動者的工資利益等。
四、結語
自黨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雖歷經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革與發展,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從未改變。為了這一初心,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人民的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不懈探索。無論是從“均中求富”“共同富裕”“共享發展”的收入分配理念發展脈絡來看,還是從收入分配實踐方式的變革歷程來看,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歷史邏輯與現實邏輯、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的辯證統一,堅決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生動踐行著“人民至上”的宗旨。回顧中國共產黨百年收入分配的歷程,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有助于繼續深化收入分配理念創新、制度建設與實踐探索,有利于化解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貧富差距、階層固化等矛盾與問題,有益于進一步解放與發展社會生產力、凸顯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促進人的自由解放。
從“均中求富”到“共同富裕”、再到“共享發展”,中國共產黨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探索和認識不斷演進。在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探索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單一公有制的條件下實行按勞分配。新時期,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極大激發了經濟活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和政策也基本完成了歷史任務。新時代,中共中央進一步提出了“共享發展”理念,通過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解決分配差距問題,使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進一步拓展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內涵。與此同時,在社會主義分配方面還將消除貧困納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提出精準扶貧思想,創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理論,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