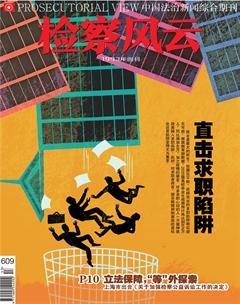日本擬出臺新規治理互聯網巨頭
梁曉軒

2020年3月15日,日本內閣在法律發展規劃中,明確加入了監管互聯網巨頭的議案,擬推動國會審議通過《數字平臺交易透明化法》。被監管的企業涉及各個領域的主要互聯網平臺,它們分別在各自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不少日本國內產經人士認為,日本政府的苛刻監管,將可能對該國互聯網技術的創新發展帶來阻礙。
互聯網巨頭濫用支配地位
“下載此應用,會開放較多的權限,包括一些敏感的隱私信息,您選擇繼續安裝嗎?”隨著互聯網及移動應用的快速普及,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已經從當初的“可選擇替代品”,成長為如今生活中無法割舍的“生活必需品”,進而互聯網平臺企業也得以不斷演化為托拉斯巨頭。這些巨頭在給使用者帶來便利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很多隱患。
互聯網巨頭濫用支配地位首先表現在歧視行為。日本政府公平貿易委員會的負責人杉本和行在接受日本媒體采訪時表示,已經針對亞馬遜、蘋果、谷歌、Facebook等互聯網平臺展開調查。他表示,調查將會著重“現有互聯網巨頭在掌握海量用戶信息之后,是否會阻礙其他公司進入相關市場,以及基于他們在行業內的主導優勢是否迫使日本本土合作伙伴公司降低價格”等問題。
其次,互聯網巨頭濫用支配地位也表現在信息安全方面。2019年10月31日發布的IT大型企業的調查報告則更加直觀,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將平臺經營者隨意操縱商品顯示順序的方法列為違規案例之一,要求運營企業說明決定商品顯示順序的機制。此外,濫用交易信息、隨意更改平臺規則等行為均被報告提及。報告稱,截至2019年9月30日,監管機構已經對網上商城、應用商店等914家平臺進行審查,從調查結果來看有以下情形:將交易數據用于自身平臺銷售,或支持其關聯公司的銷售活動;任意操作搜索算法,不公平地顯示商品的位置,阻礙競爭對手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限制其他運營商在應用商店下載,以搶奪用戶等。
事實證明,互聯網平臺企業屢屢曝出超大規模的信息泄露事件。從目前的狀況看,互聯網平臺企業往往以“商業秘密”“技術機密”等為由,拒絕向監管部門提供用戶信息等相關情況。即使出了紕漏,監管部門也很難獲取真實完整的一手資料——僅僅對表層合規作出處罰,卻很難發現實質問題出在哪。
此外,除了對數據的不合理收集,互聯網巨頭還存在通過數據及渠道資源整合與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嫌疑。不同領域的互聯網巨頭企業構筑起自己的商業模式,并利用強勢地位,迫使中小企業接受交易條件的單方面修改。上述這些行為明顯存在濫用市場優勢地位的嫌疑。更加隱蔽的是,由于互聯網行業的特殊性,巨頭們的很多交易條件甚至無人知曉,實際上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新法列舉了四種不當行為
《數字平臺交易透明化法》將互聯網平臺之不當行為列舉為以下四種:
一、不向消費者告知使用目的而獲取個人信息。例如:互聯網平臺A公司在取得消費者個人信息時,不通過本公司的網站等告知其利用目的,而直接獲取個人信息。
二、超過了達到使用目的所需的范圍,違背消費者意愿取得、利用個人信息。例如:互聯網平臺B公司在未取得消費者同意的情況下,向第三方提供了從使用其服務的消費者處獲取的個人信息。
三、沒有充分履行個人信息的安全管理職責,缺乏必要且適當的安全管理措施。例如:互聯網平臺C公司通過其服務獲取了個人信息,但在個人信息安全管理方面沒有采取必要且適當的措施,存在個人信息泄露風險。
四、互聯網平臺超越消費者使用對價,超出必要的限度獲取個人信息。例如:互聯網平臺D公司除了因提供服務所必需、從消費者處獲取作為對價的個人信息之外,還追加獲取與“消費”無關的其他個人信息——這類行為往往會對消費者造成不利影響。
此外,新法對互聯網平臺運營中的行為公正性做了專門規定。即“不當行為除了上述內容之外,還應制定法律上禁止進行一定交易上的不正當行為的規定,或是有可能阻礙革新性的措施,并舉例如下:禁止充分競爭、強制使用本公司服務、相對優先地表示本公司的商品(對非自營商品的歧視性檢索)、對企業運營產生重大障礙的單方面不利變更”。
來自質疑者的另一種聲音
在完善數字市場規則的基礎上,確保互聯網平臺及其利用經營者之間的交易透明度和公正性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制定具體規則時,互聯網平臺是一國推進數字經濟不可或缺的存在,過度的限制強化可能會導致數字領域整體技術革新的停滯。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2020年1月20日在其官網上表達了某種擔憂:“隨著互聯網平臺的事業領域擴大,其商業模式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期待著將來數字市場成長的同時,由于廣泛的互聯網平臺及其行為被作為規制的對象,可能導致未來日本互聯網平臺出現的創新萌芽被摘除。因此,我們期待著制定慎重的規則。”
質疑者首先表達了對主體定義的質疑,提出互聯網平臺的定義存在擴大化的嫌疑,即“應明確互聯網平臺的定義,讓法律規制的對象更加明確。《數字平臺交易透明化法》草案中擬定的三大特征很可能符合互聯網上提供的很多業態,模糊的定義會降低經營者的預見性,有可能阻礙創新創造”。
質疑者還提出沒有必要安排“特定互聯網平臺的運營狀況報告和監控審查機制”——特定互聯網平臺應定期報告運營狀況,并進行監控審查(報告的內容包括:互聯網平臺事業概要、數據信息公開的情況、運營體制的實際情況、糾紛等的處理狀況等)。質疑者的邏輯在于不應安排日常性的報告及審查,而采取應監管部門需要而展開調查,且調查主體應當是充分中立的。
質疑者還提出限制行政措施的過度擴張,如果監管當局要求特定互聯網平臺公開交易信息,則在規定“公開項目”及其程度時,應該客觀且合理,即“行政措施需要慎重地規定條件,應限定于違反數字平臺交易透明化法的規定,無正當理由不公開等情況”。同時,質疑者建議,在監管部門進行檢查監督、公開數據之前,應該充分保障相應互聯網平臺擁有就“正當理由”發表意見的機會。
多方利益博弈中的立法進行時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數字平臺交易透明化法》延遲至2020年3月15日由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日本政府旨在年內推動國會審議,通過該法案。但對于其出臺重要性,我們仍可以通過特殊時期的經濟現狀窺探一二。2020年第一季度,以游戲互娛與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經濟集體狂歡,這背后卻是實體經濟不斷凋敝。隨著互聯網經濟逆勢進一步崛起,AI科技進一步發展,可以想見,人工智能技術之后的人臉識別、基因測序等各類個人信息的泄露屢見不鮮。那么,對于互聯網巨頭,其將擁有大量用戶行為數據、消費數據,未來每一個人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數字化。如果管理不善或監管不善,被人盜用、泄露,或是以一定價格賣給商業組織都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從保護公民的角度,一定是要加強對互聯網巨頭的監管。另一方面,互聯網企業則不斷高呼“狼來了”,擔憂監管會遏制科技發展,認為在當前逆全球化趨勢下盲目推行強監管不利于維持優勢經濟部門的先發優勢。多方利益博弈,確是一個難題。但如僅從公平的角度出發,至少在互聯網數據方面,應當充分尊重“貢獻”數據的個人——使用者所產生的信息數據不僅僅是SQL語句中某一字段,而是活生生的存在。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