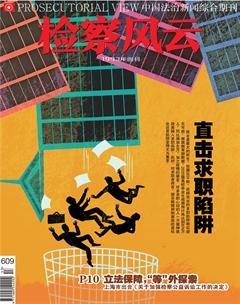亞文化:落地的呼喊
楊皓

人類學家不研究村莊,而在村莊里做研究。
——克利福德·格爾茨
亞文化一詞,直接翻譯自英語單詞subculture。1950年大衛·雷斯曼提出大眾文化和次文化的差別,并且將次文化詮釋為具有顛覆精神。大眾是“消極地接受了商業所給予的風格和價值”的人,而次文化則“積極地尋求一種小眾的風格(在當時為熱爵士樂)”。如今,亞文化一詞已經被普遍認可為與主文化相對應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現象,指在主文化或綜合文化的背景下,屬于某一區域或某個集體所特有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一種亞文化不僅包含著與主文化相通的價值與觀念,也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價值與觀念。
值得玩味的是,亞文化作為一個文化概念,在我國似乎長久地附著于一張污名化之網上,無論是早些年關于“喇叭褲”的大討論,還是如今社會對于各種亞文化群體的關注,似乎總是透露出一種“離經叛道”式的批判視角,而且背后,更是折射出一種懸浮其上的“優勢視角”,從社會大眾到學術視野,皆可在其中找到例證。
刷梗青年
“梗”,更準確地表述應該是“哏”,意為笑料、笑點。由于某些笑點被捕捉、被意會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識和語境,“梗”便成為群體成員的一種“接頭暗號”,由此形成了由“埋梗”“接梗”“玩梗”組合起來的“梗文化”。換一種更學術的表達,“梗文化”其實是互文性文本,即在一個開放性的文本中容納了多個文本,它們相互編織交叉,從而釋放出無窮意韻,而理解這樣的文本,顯然需要若干相關的“前文本”作為基礎。解釋每一個梗,往往需要足夠的“亞文化資本”。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網絡空間的自然發展中,某款頗為流行的網絡游戲社群中,“祖安人”成為了一個特殊的梗。其源于該游戲一個名為“祖安”的服務器,由于該服務器內的玩家間流行著動輒惡語相向的交流習慣,“祖安人”一詞便漸漸成為了素質較低、脾氣火爆且出口成臟人群的代名詞。但必須明確的是,如此的“社群認可梗”,往往只存在于“祖安人”群體自身內部,亦即是說,理解“祖安人”含義的網民們互相稱對方為祖安人,并且并不以此為侮辱,反倒是有著一種共有的認可與狂歡價值。在這樣一種意義稍顯封閉的亞文化行為中,亞文化群體之間并不急于尋求他人的理解,更不要求說服別人,而是把很大一部分關注度放在了社群內的相互取樂,甚至鼓勵。
Jack即是他自己口中的“祖安人”。
“我本身是這個群體內的成員,因為我就是這個游戲而且是這個服務器的老玩家了,沒錯,我就是大家口中的‘祖安人。”不難看出,Jack對于自己的“祖安人”身份并不感到尷尬,反倒有些許自豪。“必須承認,我們‘祖安人之間確實說話比較粗魯,但是其實大家并無字面意義上的惡意,很大一部分只是在宣泄對于游戲失敗的抱怨。而且很關鍵的一點是,玩家之間也早已形成了這種默契,并不會把別人的話當真。”
可惜的是,社群內部的默契并不能向外闡明亞文化本身的社會身份。“很大的困擾來自于外界,出于對這種‘祖安梗的喜愛,我把自己的微信名也改成了圈子內的話語,然后在與朋友聊天的時候,也會用到類似的表述。但是有時候,無意間朋友或者親戚看到我們的聊天方式,就會很反感。比如我某次發的一個朋友圈,被我父母看到了,就覺得我的行為很無禮。但說實在的,我本身也就是和社群內的朋友互動而已,更沒有冒犯誰的意思,長輩不理解也就算了,但我覺得真沒必要指指點點。”
聆聽Jack的講述,可以發現,在互相熟知且對某一領域相互理解的社群內部,互相刷梗的行為非但并無惡意,甚至有著某種友好互動的意思,這恰是學者庫爾德里所闡述的“媒介儀式觀”。庫爾德里認為,媒介儀式是圍繞關鍵的、與媒介相關的類別和邊界組織起來的形式化的行為,其表演表達了更廣義的與媒介有關的價值,或暗示著與這種價值的關系。更進一步,媒介儀式不僅僅可以表演、呈現既有社會核心群體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同時通過共享儀式起到召喚作用并且媒介儀式因為聚焦“核心”“中心”,從而在人們不知不覺中建構起了自身“社群中心”的迷思,這是媒介影響社會生活的潛在力量。
換言之,當社群內部圍繞某一主題互相刷梗之際,其實質是展現了一種網民之間“與你同在”的儀式感,是一群人用熱情、純愛、狂歡建構出來的“社群美學”。
學術關注
任何新鮮事物的產生與興起,勢必被學術界發現并仔細觀察。毫無疑問,作為文化研究課題中相當重要角色的“亞文化研究”,我國文化研究者也早已著述頗豐,觀察其主流研究方法與觀點,大致可分為兩種。
第一種研究方式沿襲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試圖以高屋建瓴式的傳統學術視角觀察亞文化群體的種種行為與背后意義。仍然以上一節所述的刷梗行為為例,在批判視角的分析之下,其主要判斷往往集中在輕浮的處世態度、集體狂歡的無意義行為、行為上癮的病態分析等等。為進一步闡明批評理論在分析此類亞文化行為時的慣常態度,援引某位學者對刷梗行為的論述:嘴上滿口亞文化爛梗終究導致的是年輕人審美的去個性化,快餐化甚至低俗化。內容火不一定真就做得好,只是剛好出現在這個地方迎合了年輕人想要從主流敘事里獨立出來又需要一個群體來獲取歸屬和認同而已。我也不認為刷梗做到了個性表達和集體儀式感的統一。彈幕亂刷爛梗恰恰是個體創造力和個性喪失的體現。總之不論好壞,目光短淺地吸食亞文化帶來的流量這一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觀察和反思。
第二種研究方法切換視角,更多地以兼容并包的視角來觀看新興事物的興起。其往往站在中立的角度觀察各類新事物新文化,并企圖在其中找到對文化乃至社會重新構建的可能與契機。仍然以刷梗行為為例,這一類研究文章往往關注到刷梗行為本身對互聯網交流、網民溝通的新發展,另外,還會用結構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刷梗行為本身所帶來的社群認可新可能。具體來講,刷梗行為嘗試給年輕人創造了不同于傳統“國家集體”一元化的大敘事神話,反倒是權力下放至每一個小群體本身。亦即是,每一個封閉梗文化的發散社群本身,閉合式地新建了無數互聯網時代下社群話語,一元化大敘事也在年輕人心中自然土崩瓦解,更進一步,多元化的社會必然得以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批判的角度還是兼容并包的文化研究視角,都似乎從未試圖真正從亞文化群體本身出發,去探究種種亞文化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以及背后訴求。
落地的呼喊
任何亞文化現象的出現,在簡單的話語表達背后,其本質是年輕群體尋找另一種生活可能的詩性追求。以亞文化鼻祖涂鴉現象為例,當涂鴉與滑板在美國方興未艾之時,美國社會對之同樣批判有加。但與我們如今面臨的情況不同,美國學術界出現了不少投身其中的研究人員,走進了亞文化群體的生活中去。也正是因此,涂鴉、滑板等最早被認真對待的亞文化群體在美國社會極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得益于研究人員以內化群體的身份做出的悉心闡釋。也正是因此,涂鴉從一種充滿反叛的地下行為,逐漸轉變為被社會所認可的藝術創作行為。這其中當然有一定的過程,但極為關鍵的是,其發展路徑從一開始便已被投身其中的研究人員打通。
目前我國亞文化群體所面臨的問題恰在于此。無論是社會還是學術界,雖偶有以開放視野提倡兼容并包的聲音,但真正試圖融入亞文化群體,去探尋背后原因,并且在明晰背后原因后,幫助亞文化群體找到重回主流文化或者幫助亞文化本身整合進主流文化的行為與研究卻極為少見。
這似乎在無形中鼓勵亞文化群體之間形成無數個孤島,并造成了Jack口中所述的無法被他人理解,甚至極易被他人誤解的尷尬現象。
當然,我們也不要急于把如此困境簡單歸咎于社會偏見,或者研究人員未充分投身其中。因為任何結構性的分析,乃至本質性的討論,都有其討論的局限性與現實限制。在某種社會環境之下,刷梗行為本身所代表的某種封閉話語、看重前置性理解,似乎在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中同樣存在,畢竟“學術俯身”,本身即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研究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