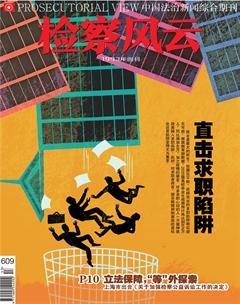朝鮮戰爭:美國需要反思的錯誤
李偉

在朝鮮戰區的“拳師”號上,艦勤人員將飛機推入機庫
美國《歷史》雜志根據美國海軍作戰部前部長、海軍上將詹姆斯·霍洛韋的回憶錄,分析了美國對于朝鮮戰爭需要反思的幾個嚴重錯誤。其中最重要的是:許多美國人錯判了這場戰爭的性質。
他協助陣亡者家屬起訴美軍
庫克·克里蘭德是美軍航空界的傳奇人物。二戰時,他是一名道格拉斯“無畏”式轟炸機飛行員,曾因在戰爭早期成功擊中日本戰列艦獲得美國海軍十字勛章。還有一次,他在美軍航母周圍實施反潛巡邏時,與后座的航炮手一起攔截了前來襲擊美軍艦隊的日本飛機編隊,并擊落一架敵機。
二戰結束后,克里蘭德雖然還屬于海軍后備隊成員,但他專注于競技飛行。1946年,在著名的克利夫蘭空中競賽中,克里蘭德駕駛由錢斯·沃特公司設計、固特異飛機制造廠生產的FG“海盜”式飛機參加了表演。后來,克里蘭德買下3架F2G型飛機,改裝后組建了一支飛行表演隊。從1947年到1949年,克里蘭德的機隊連續3年贏得克利夫蘭空中競賽的最高榮譽——湯普森杯。特別是在1949年的比賽中,克里蘭德的3架F2G飛機包攬了前三名,這讓他滿懷信心地想繼續自己的職業生涯。
然而,1950年,克利夫蘭空中競賽因朝鮮戰爭爆發而停辦。克里蘭德響應美軍的號召加入現役,并作了一個后來他認為是此生最嚴重的錯誤決定——動員他在二戰中的部下、26名軍機飛行員再度入伍。這些人都已經轉行,享受了幾年和平時期的平靜生活。
朝鮮戰爭中的“克里蘭德飛行團”在美國一度被傳為佳話。在克里蘭德的帶領下,他的下屬在朝鮮戰場上展現出了飛行和作戰技巧。其他美軍飛行員都羨慕他們的飛行技術,并競相模仿他們大膽的飛行方式。然而,克里蘭德的團隊戰損嚴重,在1951年到1952年的作戰行動中,26名飛行員中有12人陣亡——12個家庭就此失去了支柱。

朝鮮戰爭中的詹姆斯·霍洛韋
朝鮮戰爭結束后,這12個家庭中有8個家庭不滿政府給予的撫恤金。內心充滿愧疚的克里蘭德協助他們起訴美軍,在法庭上作證,以幫助這些家庭爭取更多的賠償金。
錯判戰爭的性質
《歷史》雜志指出,克里蘭德和他的團隊的遭遇,顯示出美國人在朝鮮戰爭中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錯判了這場戰爭的性質。
二戰時,美國海軍大量撥款訓練飛行員,挑選年輕且有天賦的人員,并耗費大量時間以及諸如訓練基地、飛機和教練員等資源進行訓練。二戰后,很多飛行員離開現役,轉入其他行業。但美國海軍有計劃地保留了這些人才資源,目的是有朝一日讓這些“特殊的平民”為國效力。美國海軍為此構建了一個遍布全國的航空站后備隊系統,將海軍航空部隊的老兵集中在人口聚居區的周邊,以便于戰時動員。海軍利用二戰剩余的飛機組建后備役中隊,與前海軍飛行員和航空技術人員保持聯系,并在后備隊航空站和市政機場開展訓練,以維持其作戰能力。由于要用1個中隊的飛機供4個后備役中隊的飛行員輪流使用,因此每個中隊每個月抽出一個周末進行訓練,以幫助非現役的飛行員保有嫻熟的飛行技藝。
在準備赴朝鮮半島作戰前,美國海軍啟封了足夠的艦載機供航母使用,同時需要大量飛行員和維護人員。此時,海軍的后備役部隊發揮了作用,為海軍航空兵的作戰行動增補人員。后備役人員編入現役后,可以馬上按照戰時的飛行序列執行任務。
事實上,那些后備役人員雖然熱愛飛行,但并不喜歡戰爭。他們之所以在二戰后還繼續參加內容多樣的作戰聯訓,而且有的訓練地點還在遠離其家鄉的航空站,是因為在他們的心中還保有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熱情。這些人大都有穩定的職業和幸福的家庭,他們沒弄清楚朝鮮戰爭的性質和二戰完全不同,從而卷入了一場“無意義的戰爭”。
被炸傷手臂的鐘表匠
第20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海軍上將詹姆斯·霍洛韋是朝鮮戰爭的親歷者。每當他想起自己的戰友約翰·錢伯斯,眼眶就會濕潤。在接受采訪時,他講述了自己和錢伯斯在朝鮮戰爭中的經歷。
1950年7月2日,我(詹姆斯·霍洛韋)所在的“拳師”號航空母艦進駐日本海,參加朝鮮戰爭。我要率領6架F9F“黑豹”飛機,攻擊對方的集結地——位于前線以北80公里處的朝鮮宋基尼。我駕駛首機,于上午7時準時起飛。我聽到彈射器的叮當聲,感到其對飛機施加壓力時,機尾略有下沉。彈射官向我發出“準備”的信號,我向前使勁推下油門操縱桿。等飛機的轉速盤顯示100%時,我盯住表盤,確定轉速平穩,然后扣緊連接彈射座椅靠背的安全帽,舉手示意。在短暫的延遲后,“砰”的一聲,彈射器發動,我的飛機在不到2秒的時間內被彈出,以125節的速度升空。我直上云霄,躍升到1200米,將速度保持在250節。3分鐘后,其他5架飛機都被彈出,我向左180度轉彎,隨后保持爬升,并與我的飛行編隊會合。
在接近目標地區上空時,我突然聽見“砰”的一聲,接著是彈片刮擦機身的刺耳的“咔嗒”聲——我知道我被防空火力擊中了。拉著操縱桿的我馬上作出反應,艱難地操控飛機。我的左翼油箱被防空炮彈擊中,帶著火光的燃油不斷泄漏。我通過警戒通信頻道(用于緊急狀態下的無線電頻道,比飛行員預設的任何通信頻道都重要)呼叫負責指揮我的航空大隊司令部,告訴他們我被擊中了,正全速墜落。因為需要緊急彈射或迫降,我希望在發動機失效或燃油燃盡之前盡量到達迫降地。我呼叫僚機飛行員與我同行,但沒有聽到對方應答。我感到事情不妙——錢伯斯去哪兒了?!
突然,一架“黑豹”飛機爬升到我身旁。我從機身的編號認出那是我的僚機——錢伯斯。他的飛機座艙頂上沾有血跡。他打手勢告訴我,其無線電接收裝置掉到機艙外面了。看到他舉起的左手上布滿血痕,我的心咯噔一下——他是個技術出色的鐘表匠。國家發出朝鮮戰爭動員后,他馬上關掉了父親傳給他的鐘表店,加入部隊趕赴東亞。可是,他的手……他的飛機翻轉時,炮彈擊中了座艙底部,并在座位下爆炸。雖然降落傘包緩沖了部分爆炸力,但是彈片還是無情地射入了他的胳膊和大腿。
通過警戒通信頻道,我呼叫戰術空中控制中心,告訴他們我的大體位置,請求其通過無線電將我引導至附近的搜尋和營救設施。我將雷達信標調到緊急狀態,便于飛機被友方雷達識別。幾乎同時,戰術空中控制中心的雷達捕捉到我的雷達信號,引導我飛往韓國江陵,那里有一條狹窄的鋼網(邊緣可扣接在一起的鋼板)跑道,作為第18戰斗機野戰機場。這個時候,我不知道錢伯斯傷勢如何,也不知道他能否獲救。
戰術空中控制中心將我引導到第18戰斗機野戰機場。跑道周邊遍布著蓋有黃褐色帆布的韓國部隊救護車和軍用吉普車。后來我知道錢伯斯比我先到,他的飛機滑行到跑道中部就損毀了。他立即被醫護人員救出,但吉普車無法及時清理鋼網跑道上的飛機殘骸。由于我的飛機燃油不多了,只好緊急迫降在跑道周邊空曠的稻田地里。我的飛機被撞得七零八落,而我竟然沒有受傷。
我被匆匆趕來的吉普車運到醫療帳篷里——錢伯斯正在那兒。他躺在手術臺上,醫生為他取出手臂和腿上的彈片,清洗傷口。那時我就知道,他的手不可能再修理和調試鐘表了。一小時后,他被直升機送往美軍戰地醫院,一周后被送往費城靠近他家的海軍醫院。
最令人難過的是,由于錢伯斯不能再當鐘表匠,他索性沒有退役,而是一直留在軍中。一年之后,他又能駕駛飛機了。在后來的越南戰爭中,他作為航母艦載機中校飛行員,陣亡在F—4“鬼怪”式戰斗機上。
詹姆斯·霍洛韋的戰友錢伯斯,是美國犯下的錯誤的縮影。他懷著滿腔熱情投入朝鮮戰爭,卻因負傷失去家傳的技藝,最終在另一場戰爭中成為亡魂。
高估美軍的空中優勢
《歷史》雜志指出,美國軍方在朝鮮戰爭中所犯下的其他錯誤,基本上都與過于自負有關,比如高估了自己的空中優勢。
1950年夏天,空中行動只是美軍在朝鮮作戰的輔助手段,但此后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軍事戰略,美軍的空戰部隊最大限度地支持所有作戰行動。
事實上,在朝鮮戰爭初期的“聯合國軍”戰斗機中,只有F—86“佩刀”飛機能與朝鮮方面的蘇制米格—15戰斗機抗衡。美國空軍從蘭利基地調撥了一批F—86“佩刀”,部署了一支聯隊到漢城(今首爾)附近的金浦空軍基地。F—86的主要任務是在朝鮮西北角鴨綠江以南對米格—15飛機實施攔截。美軍的這些F—86由位于朝鮮西海岸的一個叫尤多里的海島上的雷達引導。該基地由美國空軍人員控制,能追蹤鴨綠江上空的米格—15飛機,并引導從位于漢城附近的金浦和水原機場起飛的F—86戰斗機,在朝鮮西北角叫作米格谷的地方實施阻截。
但是,美軍的這種攔阻式空中巡邏效果有限,有一些朝方的米格—15機群沖過了F—86的防護幕,它們與航速慢但載荷大的飛機聯合行動,給美軍制造了很大的麻煩。
米格—15是一款性能非常優越的戰斗機,美軍分析師后來才意識到,它比F—86“佩刀”更先進。米格—15爬升速度較快,轉向迅速,機動性能較強。“佩刀”只是俯沖速度較快,瞄準具和機艙除霧系統先進一些。
據美國空軍最好的F—86戰斗機飛行員描述,對方的米格戰斗機飛行員表現出極佳的空戰能力。當時的蘇聯新聞媒體評述,蘇聯的米格戰斗機飛行員大都在二戰中與德國首批梅塞施米特和福克·沃爾夫戰斗機飛行員正面交鋒,具備非常豐富的作戰經驗。二戰中頂尖的蘇聯飛行員、曾擊落62架德國飛機的伊萬上校,正是朝鮮戰爭中米格—15第一空戰師的指揮員。可想而知,美國的空中作戰部隊在朝鮮其實很難占到便宜。
航母艦隊人員捉襟見肘
美軍的另一個自負之處是,高估了海軍的整體實力。
朝鮮戰爭爆發后不久,時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弗利斯特·謝爾曼決定,盡可能多地聚集航母到朝鮮戰區。然而,美國已經承諾將兩艘攻擊型航母部署到位于地中海的第六艦隊,以支援北約的行動。在維持兩艘航母部署于第六艦隊的同時,保障其他航母編隊在太平洋的戰斗行動,這對于當時的美國海軍來說困難重重。那個時候,美軍的航母部隊仍處于戰斗力形成階段,大量艦艇都是從后備役艦隊中恢復使用的,飛機也是從海軍后備隊中調集并從封存倉庫中啟用的。美國海軍難以掌控迅速增多的艦艇和飛機。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海軍仍然決定將4艘西太平洋的攻擊型航母分配到第七艦隊,從而隨時保持有兩艘航母在前線作戰。每艘航母實施前沿作戰行動的時間為30天。換班時,航母返回日本佐世保或橫須賀的美軍基地需要兩天,在港保養修理加上艦員休整需要9天,返回前線又需要兩天,這樣周而復始。
基于3比1的原則,要在西太平洋部署4艘攻擊型航母,共需要12艘航母。因為在平時的維修保養、訓練、本土行動、中途換班、前置部署的周期輪換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航母能夠進行作戰部署。當時美國的攻擊型航母數量無法做到部署12艘在太平洋艦隊,同時又不背棄對北約的承諾。減少支持北約的航母數量是不現實的,因為當時蘇聯是美國及其盟友的現實敵人。因此,美軍第七艦隊(部署朝鮮戰區)需要大西洋艦隊的持續協助,并縮短航母維護和訓練的周期,結果造成美國海軍幾乎全員疲于奔命。
人員換艦部署是克服一些關鍵崗位缺人的唯一方式。當一艘航母結束部署期從西太平洋返回美國本土時,其中一些船員不能回國,而是被轉移到日本,再分派到另一艘前來換班的航母上。這些人幾乎無法得到任何休整的機會。即便如此,美軍航母上的人員還是經常不夠用,尤其是技師和甲板工作人員。這直接影響了航母艦隊在戰爭中發揮作用。
編輯:姚志剛?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