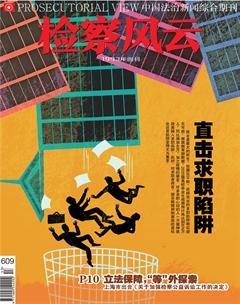“房子不賣(mài)給黑人”違法嗎
林海

近來(lái),美國(guó)黑人的境遇又引發(fā)關(guān)注。在美國(guó),黑人即使賺夠了錢(qián),有時(shí)也得不到足夠的尊重。1945年,雪萊一家在圣路易斯的一個(gè)社區(qū)買(mǎi)房,卻被告知這個(gè)社區(qū)的住戶(hù)已經(jīng)簽署協(xié)議,不會(huì)將房子賣(mài)給黑人。雪萊與社區(qū)協(xié)商不成,一怒之下將領(lǐng)頭的路易斯·克萊默先生告上了法庭。
布坎南案:沖擊種族隔離制度
雪萊一家是在選中那棟房子并簽約后,才得知社區(qū)有這一禁令的。而且這一約定已經(jīng)維持了三十多年。早在1911年2月16日,這個(gè)小區(qū)的39名業(yè)主就簽署了一份共同協(xié)議。
但問(wèn)題在于,那三十九名業(yè)主并不擁有小區(qū)內(nèi)的所有房產(chǎn)。他們只擁有該小區(qū)內(nèi)57棟房產(chǎn)中的47棟,另外10棟的業(yè)主并未簽署。更有爭(zhēng)議的是,簽署這一協(xié)議時(shí),小區(qū)里其實(shí)住著黑人家庭。特別是有一家人,他們是1882年就搬來(lái),在此住了30年之久。協(xié)議對(duì)他們有效嗎?當(dāng)最初簽署了協(xié)議的業(yè)主后來(lái)轉(zhuǎn)讓了一些房產(chǎn)(自然是轉(zhuǎn)給白人),這一協(xié)議的效力還及于受讓者嗎?這些問(wèn)題讓雪萊一家很是困惑。
雪萊一家本打算購(gòu)買(mǎi)的是一戶(hù)姓菲茨杰拉德的家庭的房產(chǎn)。這一家人自1911年協(xié)議生效時(shí)就未參與簽署。因此他們也未將所謂的“小區(qū)決議”當(dāng)回事。1945年8月11日,他們和雪萊一家簽署了房屋出售合同。這一消息令小區(qū)其他居民十分憤怒。他們于1945年10月9日向圣路易斯市巡回法庭提起訴訟,要求撤銷(xiāo)合同,禁止雪萊一家占有該房產(chǎn)。在今天看來(lái),這個(gè)請(qǐng)求看上去有點(diǎn)荒誕。但在當(dāng)時(shí),似乎是理所應(yīng)當(dāng)。那個(gè)時(shí)代的主旋律是“隔離但平等”。歷史上,美國(guó)黑人總數(shù)的90%仍然分布在南部地區(qū),而且主要在鄉(xiāng)村。
許多南部城市,比如巴爾的摩、里士滿(mǎn)、路易斯維爾、亞特蘭大等還制定了居住隔離法規(guī)。直到1917年,這樣明目張膽的官方政策才在“布坎南訴沃利”案中遭到挑戰(zhàn)。
布坎南案是美國(guó)歷史上對(duì)種族隔離制度產(chǎn)生重大沖擊的第一個(gè)判決案。像南部其他城市一樣,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市也制定了一項(xiàng)種族隔離法規(guī),既禁止黑人在以白人為主的社區(qū)內(nèi)購(gòu)買(mǎi)房產(chǎn),也禁止白人在以黑人為主的社區(qū)內(nèi)購(gòu)買(mǎi)房產(chǎn)。該法規(guī)通過(guò)以后,一位白人業(yè)主布坎南將白人社區(qū)的一份地產(chǎn)出售給一位黑人,從而引發(fā)了本案。1917年,肯塔基州上訴法院判決該法有效,然而該判決被該州的最高法院所推翻。后者認(rèn)為,不受限制地進(jìn)行房產(chǎn)交易是憲法所保障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該法沒(méi)有經(jīng)過(guò)適當(dāng)?shù)姆沙绦蚨鴦儕Z了公民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因而無(wú)效——布坎南案也成了對(duì)種族隔離政策的致命一擊。
“限制性契約”讓黑人無(wú)處容身
至此,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立法部門(mén)再也不能以官方行為明確地制定和實(shí)施種族隔離法規(guī)——然而,白人業(yè)主們?nèi)绻谏鐓^(qū)的主持下,簽訂私人協(xié)議,規(guī)定在一定的期限內(nèi)禁止將房產(chǎn)出售、出租和轉(zhuǎn)讓給黑人,卻無(wú)法被認(rèn)定為“官方行為”,因此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一種“潛規(guī)則”。
除了限制黑人買(mǎi)二手房外,白人控制的地產(chǎn)協(xié)會(huì)還進(jìn)一步要求,在新建住宅的出售合同中,要包含禁止未來(lái)白人戶(hù)主將該地產(chǎn)轉(zhuǎn)售、出租給黑人的條款。這種歧視行為不僅僅只是個(gè)別社區(qū)個(gè)別地產(chǎn)商的行為,而且還得到了全國(guó)地產(chǎn)商協(xié)會(huì)的大力倡導(dǎo)和支持。
此后,越來(lái)越多的開(kāi)發(fā)商在其地產(chǎn)合同中加入種族限制性契約,尤其是在鄰近黑人住區(qū)的地方。舊街區(qū)的業(yè)主也在地產(chǎn)協(xié)會(huì)的組織下簽署這種限制性契約,1927年,芝加哥地產(chǎn)協(xié)會(huì)甚至還草擬了一份限制性契約范本。這些限制性契約只要獲得一定比例的簽名就可生效——雪萊一家所購(gòu)社區(qū)的39名業(yè)主所簽的就是這種契約。契約不用所有業(yè)主簽署,只要85%至90%簽署即可生效。而且生效后,任何一位簽名者都可以控告另一位違約的簽名者。
當(dāng)時(shí),這種限制性契約是相當(dāng)普遍的,給黑人購(gòu)買(mǎi)住宅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他們別無(wú)選擇,只好擠進(jìn)本來(lái)就很狹小的黑人社區(qū)和有限的住宅中,因而導(dǎo)致了黑人社區(qū)的極度擁擠。當(dāng)時(shí),據(jù)芝加哥大都市區(qū)住宅委員會(huì)主席費(fèi)德·克萊默(巧的是他也姓克萊默)的報(bào)告,該市30萬(wàn)黑人所居住的住宅,按照正常情況只能容納這一數(shù)字的三分之一。
黑人的房源短缺導(dǎo)致了租金的上升,使黑人的經(jīng)濟(jì)狀況雪上加霜。而且,由于無(wú)須對(duì)房產(chǎn)進(jìn)行更多的投資維護(hù)也能順利出租,于是黑人社區(qū)普遍出現(xiàn)了住宅衰敗、缺乏設(shè)施等狀況,很快淪為貧民窟。貧民窟的泛濫又導(dǎo)致公共健康下降、成人犯罪、少年斗毆、賣(mài)淫嫖娼等一系列不良社會(huì)問(wèn)題,進(jìn)而使白人更加排斥他們的黑人鄰居。如果有一些相對(duì)富裕的黑人想搬進(jìn)白人小區(qū),小區(qū)居民就會(huì)拿出大多數(shù)業(yè)主簽的限制性契約,要求賣(mài)房者撤銷(xiāo)出售行為。而法院還總是支持他們的訴訟請(qǐng)求。后來(lái)人們?cè)u(píng)價(jià)說(shuō),司法的縱容在種族隔離這件事上成了幫兇。
雪萊勝訴:法院的縱容也是一種“官方行為”
不過(guò)在雪萊案發(fā)生的1945年,風(fēng)向已經(jīng)開(kāi)始有所變化。初審法院拒絕了業(yè)主們的訴求。理由是訴訟所依據(jù)的限制性協(xié)議不是完整的。因?yàn)樵搮f(xié)議并未獲得所有業(yè)主的簽名,至少菲茨杰拉德一家就沒(méi)有簽署。這一協(xié)議發(fā)生在那些簽署的業(yè)主之間,并不能干預(yù)第三人(比如未簽署的業(yè)主)。裁決生效后,雪萊一家很高興,完成了和菲茨杰拉德的交易,搬進(jìn)了社區(qū)。鄰居們則十分失望,其中帶頭的克萊默先生更是不服,他代表大家向密蘇里州最高法院提起了訴訟。
克萊默先生提出,這個(gè)協(xié)議的效力不只及于39名業(yè)主,而是涉及整塊土地和整個(gè)小區(qū)。只要是小區(qū)內(nèi)的房產(chǎn),都應(yīng)當(dāng)遵守由這些業(yè)主做出的決議。1946年密蘇里州最高法院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要求該契約得到執(zhí)行。法院除了判決克萊默先生等人簽署的契約有效外,還發(fā)布了要求強(qiáng)制執(zhí)行的司法令狀。雪萊一家不服,上訴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同一時(shí)間,此類(lèi)案件頻出。聯(lián)邦最高法院遂選擇了四個(gè)案件進(jìn)行集中審判。
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duì)這四個(gè)案件的調(diào)查和審理引起了全國(guó)的關(guān)注,全國(guó)律師指導(dǎo)協(xié)會(huì)等幾十個(gè)社會(huì)組織向最高法院提交了23份法律參考要旨,支持黑人上訴人。1948年1月22日和23日,聯(lián)邦最高法院舉行了兩天的庭審。5月3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文森公布了判決。有意思的是,聯(lián)邦最高法院并沒(méi)有責(zé)備那些簽署了“排黑契約”的白人業(yè)主,而是將板子打在各州法院身上。判決稱(chēng),各州法院的判決和強(qiáng)制執(zhí)行令狀屬于“官方”行為,應(yīng)該受到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限制,各州法院剝奪了上訴人的法律平等保護(hù)權(quán),因而無(wú)效。
在判決中,聯(lián)邦最高法院還特別提醒各州法院,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基本目標(biāo)就是要確保“所有的人,無(wú)論是有色人種還是白人,在州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而且就有色人種而言,該修正案的保護(hù)對(duì)其而言是首要的設(shè)計(jì)目標(biāo),不會(huì)因其膚色而受到法律的歧視”。同時(shí),聯(lián)邦最高法院也作出一些讓步,宣布該修正案的目標(biāo)僅僅是官方行為,而不是私人行為,首席大法官文森宣布,“只要這些契約在執(zhí)行中,各方均是自愿遵守其條款,顯然就不存在官方行為,就沒(méi)有違反該修正案的條款”。也就是說(shuō),假如雪萊自愿遵守了克萊默先生等人的協(xié)議,那么聯(lián)邦法院也不會(huì)作出干預(yù)。
這一判決看似沒(méi)有直接否定限制性契約,但其社會(huì)影響是極為深遠(yuǎn)的。它直接影響了聯(lián)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種族政策,聯(lián)邦住宅管理局(FHA)迅速修改了《房產(chǎn)抵押擔(dān)保的資格》和《擔(dān)保手冊(cè)》,宣布不應(yīng)該由于不同居民的進(jìn)入可能會(huì)影響該地區(qū)其他地產(chǎn)的價(jià)值,而拒絕對(duì)其進(jìn)行抵押擔(dān)保;應(yīng)該承認(rèn)美國(guó)公民機(jī)會(huì)均等的權(quán)利,不管其種族、膚色、信仰或民族來(lái)源如何。聯(lián)邦公共住宅管理局(PHA)也在其政策聲明中寫(xiě)道:“必須對(duì)各種族的符合條件的家庭平等對(duì)待。”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判決也成了此后相似案件作判的依據(jù)。
對(duì)于雪萊一家來(lái)說(shuō),他們終于可以安穩(wěn)地住進(jìn)新家。然而他們沒(méi)想到的是,由于案件成為經(jīng)典,他們的故事被拍攝成紀(jì)錄片《雪萊訴克萊默的故事》,2019年,該紀(jì)錄片在亞馬遜上線。然而,正如科普蘭所言:“有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障礙需要克服,進(jìn)入亞馬遜網(wǎng)站的概率實(shí)在是微乎其微。”距離真正消除種族歧視,或許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