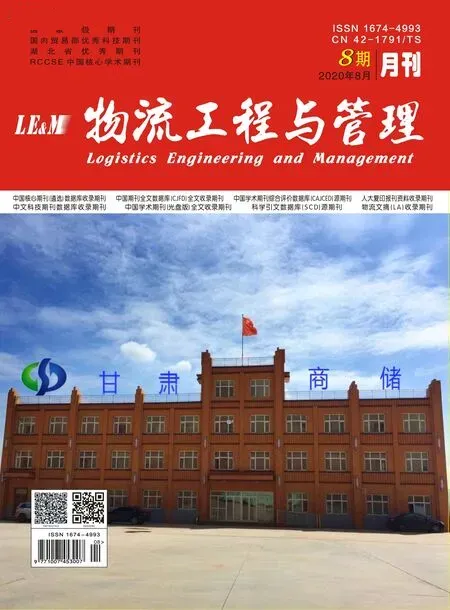交叉口行人手機使用對過街危險行為影響分析*
□ 黃霖霖,屈嘉宸,張夢瑤,林 麗
(南京林業大學 汽車與交通工程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8)
行人在過街時使用手機的現象愈發普遍,近年美國實施的一項調查顯示,調查對象中的成年人承認過街過程中分心使用手機的比例接近六成[1]。行人過街行為是一個根據實際交通場景進行復雜信息加工處理的過程,包括觀察感知和判斷決策兩個關鍵步驟[2],過街使用手機分散了行人過街時的注意力,影響了其感知能力和決策過程,增加了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的潛在風險,因而這一安全問題引起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Nasar和Troyer通過統計交叉口過街行人使用手機與交通事故的情況[3],識別出通話、發短信、瀏覽網頁是過街時最常見的三種手機使用方式,發現過街使用手機導致的分心情況增加了行人做出危險過街行為的風險。Dalibor[4]針對無信號燈交叉口處行人分心過街行為構建邏輯回歸模型,分析手機使用方式對過街不安全行為的影響程度,發現手機通話對行人的過街不安全行為影響最大,聽音樂對行人過街不安全行為影響最小。模擬實驗能夠有效控制過街環境,便于開展重復實驗,因而得到研究者重視。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多從模擬實驗角度探究手機使用對過街行為影響,實證性研究成果較少,趙艷等[5]2014年選取北京市數個交叉口與路段進行實地調查,發現行人過街使用手機的比例因路段區域功能的不同而分布在17.8%到35.2%之間。張存保等[6]建立了人車沖突量化模型,模型顯示低頭看手機屏幕對人車沖突影響最大,聽音樂對過街安全影響不顯著。
目前,國內部分實地調查研究對過街行人手機使用具體目的采用推測的方法造成了可靠性有限的問題,較少考慮手機自身因素影響。為此,本文選取南京市新莊廣場的人行橫道,實測記錄手機使用對行人過街行為的影響,并進行量化分析和建模,使用logistic模型識別危險過街行為的顯著影響因素與影響程度,為行人過街安全分析提供一定理論基礎,調查結果可以作為行人過街安全設計參考。
1 數據采集與處理
1.1 數據采集
調查地點選取在南京市新莊廣場跨越玄武大道的人行橫道,通道形式如圖1所示。調查時間分別安排在工作日午間12∶00-13∶00和休息日下午14∶00-15∶00,休息日選取下午時段的原因在于午間展覽中心休息,行人流量少。工作日調查時間提前則兼顧了學校作息,進而與該區域行人出行特征相符合,保證實驗的普遍性與穩定性。布置兩臺攝像設備拍攝,為了盡量減少設備對行人過街產生的干擾,設備被安置在通道兩側的綠化帶中。

圖1 攝像機安裝位置圖
1.2 數據處理
實驗觀察記錄雙向所有過街行人的性別、年齡、過街時間,對于使用手機過街的行人觀察其是否做出危險的過街行為,研究界定的危險行為包括闖紅燈、走出斑馬線范圍、缺少過街瞭望三類。如果使用手機行人在過街時同時做出多項危險行為,則分別記入各類危險行為中,在模型中繼續處理。行人過街后采用即時問卷調查的形式,獲取該行人手機使用相關數據,包括手機使用方式、手機型號、手機流量套餐等信息。
手機特征包括屏幕尺寸、流量套餐狀況兩類。使用手機用途設置打電話、翻閱社交媒體、使用即時通訊軟件、聽音樂四類。手機屏幕尺寸通過詢問手機型號,自行查詢對應尺寸的方法獲取。流量套餐分為有限、無限流量兩類。行人是否闖紅燈、過街中是否走出斑馬線范圍、過街瞭望的次數皆可以通過錄像直接獲取,據相關研究[7]設定行人過街過程中左右觀察來車瞭望次數少于2次被認為是缺少過街瞭望。調查內容與參數見表1。

表1 調查數據與參數
2 過街使用手機方式分析
調查共記錄樣本數722個行人樣本,發出調查問卷213份,回收有效問卷207份。使用手機行人占比29.5%。調查結果中過街使用手機觀看視頻、玩游戲的人數分別為2人與1人,考慮到模型實用性,故在后續分析中將這兩項從手機使用用途中剔除。圖2統計了年齡、性別對過街使用手機方式的影響,從圖2(a)中可知,青年使用手機聽音樂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年齡層的行人(23.64%),在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上也為最高(20%),中年人使用手機的主要用途是使用即時通訊軟件(45.1%),而老年人使用手機的行為以打電話為主(53.57%);圖2(b)顯示,使用即時通訊軟件是男女行人使用手機的首要用途,男性過街打電話的比例比女性高13.4%,而女性在過街聽音樂、使用社交媒體的比例上要高于男性。

圖2(a) 手機使用方式與年齡的關系
表2按使用手機的方式對過街行人進行了分組,以正常過街行人作為參照組,運用卡方檢驗探究了行人過街時間以及做出危險行為的比例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與其他各組相比,使用手機翻閱社交媒體的人群平均過街時間最長,比正常行人慢了2.52s。超過67%的行人缺少過街瞭望,使用通訊軟件過街的人群在過街時間上較之正常行人需要額外9.6%的時間才能完成過街,過街打電話的人群在過街時間上沒有與參照組表現出過大差異,但是在過街走出斑馬線的比例上較之正常過街人群高出了29%,體現出顯著不同(χ2=5.88,p<0.05)。過街打電話的人群闖紅燈的比例比正常過街人群高出了10%。

圖2(b) 手機使用方式與性別的關系

表2 手機使用方式對過街行為影響
3 手機使用影響分析
3.1 過街危險行為建模
針對三種過街危險行為分別建立三個二項邏輯回歸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過街危險行為與行人特征、手機使用方式、二次過街是否使用手機等自變量之間的關系。利用比值比(OR)計算自變量間對危險過街行為的影響程度。
在實驗中OR值代表觀察到使用手機過街的行人做出闖紅燈、走出斑馬線范圍、缺少過街瞭望三種危險行為的概率與不做出這三種行為的概率的比值,OR值與1的距離越遠表明該自變量與過街危險行為越相關,通常當OR值大于1.4或小于0.7時,認為兩者間關聯強度比較高。
由于因變量為是否做出危險行為,屬于二分類因變量,建模處理的主要方法有Logistics回歸、Probit分析兩種方法,Probit分析反應不同響應頻率下有效值的估計值,而Logistic回歸反應自變量的OR在不同置信水平下的估計值來進行不同實驗組之間的對比分析。總的來說,Probit分析適用于模擬實驗的研究,而Logistic回歸更適用于觀察研究。考慮到實驗通過實地調查獲取數據,采取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更合適,logistics回歸的基本形式為:
(1)
式中y為因變量,1代表危險行為發生,0代表危險行為未發生,e為自然對數,X為自變量向量,β為對應系數向量,p(y)為在X、β確定條件下是否做出危險行為的概率。
由此可得做出危險行為與不做出危險行為概率之比OR,并在兩邊取對數,得到危險行為對各自變量的logistic回歸模型為:
(2)

3.2 模型整體評價
利用Hosmer-Lemeshow Test對三個模型的擬合度進行檢驗(見表3),其顯著性水平皆明顯高于0.05,可以認為當前數據中信息已被充分提取,模型擬合度達到要求。

表3 Hosmer-Lemeshow檢驗結果
利用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及曲線下的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判斷模型的識別準確性。ROC曲線下的面積越接近于1,模型的識別準確性越高。從表4中可以看到三個模型顯著性水平皆小于0.05,拒絕原假設,即模型識別確有效果,闖紅燈、走出斑馬線范圍、缺少過街瞭望三類模型AUC值分別為0.657、0.753、0.740,模型的識別準確性在接受范圍內。

表4 識別準確性檢驗結果
3.3 模型結果分析
表5給出了95%C.I(置信區間)條件下回歸模型處理結果。在年齡對于是否做出危險行為存在部分影響,較之青年行人,中年行人更有可能走出斑馬線范圍(p<0.05,OR=2.19),而老年行人闖紅燈的可能性則最高(p<0.05,OR=1.89)但在過街時卻更愿意瞭望周圍環境(p<0.05,OR=0.26),反映老年行人過街心理上更為謹慎,另一方面,闖紅燈人群的行為更傾向于多次左右瞭望,并快速通過過街通道。性別在三個危險行為模型中影響皆不顯著。
與小屏幕手機相比,大于5英寸的手機屏幕和超過5.8英寸的超大屏手機分別有1.55倍和2.12倍的概率使得行人在過街過程中走出斑馬線,反映了更大的手機屏幕的確分散了過街行人的注意力,增加了潛在過街風險。流量套餐狀況對過街做出危險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
表5顯示過街使用手機打電話的人群最有可能產生闖紅燈的舉動(p=0.019,OR=1.65),或是走出斑馬線的范圍(p=0.024,OR=3.25)。翻閱社交媒體的人群,過街缺乏過街瞭望的風險為聽音樂人群的4.5倍(p<0.01,OR=4.54),也更可能走出斑馬線(p=0.037,OR=1.69)使用即時通訊軟件對過街觀察的影響較大(p<0.05,OR=1.84)。

表5 回歸分析結果
4 結語
通過實地記錄過街危險行為,同時對使用手機過街的行人進行問卷調查,獲取手機使用方式與使用者基本特征,從而建立三類二項logistic回歸模型以分析手機使用對過街危險行為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手機使用改變行人過街行為,增長過街時長,提升行人做出危險過街行為風險,影響過街安全,
從手機使用方式來看,瀏覽社交媒體、使用即時通訊軟件使得過街時間明顯增加。接聽電話最為顯著的增加了行人走出過街通道安全范圍以及闖紅燈的風險,使用手機瀏覽社交媒體的行人缺少過街瞭望的風險最大。
從手機特性來看。大尺寸手機屏幕吸引過街行人更長時間的注視屏幕,提高了行人走出斑馬線的風險。但是手機流量套餐狀況對過街危險行為影響不顯著。
實驗中發現當過街等待人群較少時,使用手機的行人闖紅燈的次數會明顯多于等待人群多時的次數,說明行人在人群中過街時與獨自過街時的決策過程存在差異,人群過街特性對過街安全的影響值得進行進一步的關注與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