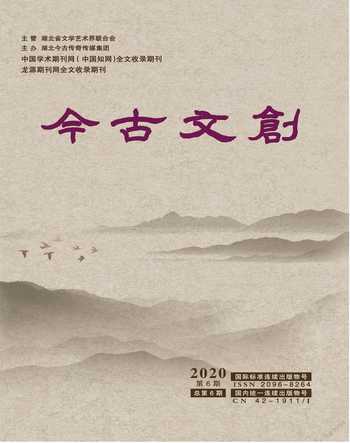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遠離塵囂》中的宿命論
【摘要】《遠離塵囂》也許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說”中最具“田園牧歌”風格的一部。哈代在這部小說中刻畫了一個“新女性”——芭斯謝芭·埃芙汀,她具有女性主義意識,反抗傳統婚戀觀和父權主義。然而,受困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她最終還是屈服于傳統,由“新女性”轉變為“舊女性”。本文將對這一悲劇進行論述,并從中詮釋哈代的宿命論。
【關鍵詞】《遠離塵囂》;托馬斯·哈代;女性主義;宿命論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06-0019-02
一、背景概述
托馬斯·哈代(1840-1928)擅于在作品中利用巧合、意外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推動情節發展,最終通過人物的結局體現“宿命論”。“宿命論”是一種人生觀,它承認所有的行為都受事物的本性或命運的控制。人物一直在努力掌控自己命運,然而僅因為某些不經意的行為,最終毀掉了其真正想獲得的人生。
在《遠離塵囂》中,父權與男權的在場,被賦予了某種神秘色彩與威權意味,其通過物化女性,并試圖剝奪、限制這一群體在財產繼承上的權利,實現著對于女性的規訓與控制(韓淑俊,2020)。哈代生活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是典型的父權制社會,女性被視為“第二性”,低于并從屬于男性,是生育的工具,男性欲望的對象。“貞潔、順從、忍耐、犧牲”是衡量女性好壞善惡的標準。遵循這些標準的女性被定義“房間里的天使”(秦豫晉,2010)。而企圖追求獨立自由的女性會被社會所排斥,甚至難以生存。
許多人認為《遠離塵囂》是哈代悲劇系列前的喜劇——全書基調活潑,并且女主人公有一個看似圓滿的結局。因此,國內評論家大都不把《遠離塵囂》放入哈代的悲劇小說系列。但這樣就無法看到哈代“宿命論”在書中的體現。本文將從女性主義角度對芭絲謝芭進行分析。只有從這一角度闡述該作品,才會發現它展示的依然是“宿命論”悲劇性的主題。
二、反抗傳統的“新女性”
維多利亞時代有一群女性,她們有自己的職業,為實現物質和精神上自由,爭取社會地位而努力奮斗著。評論家稱她們為“新女性”。哈代塑造出許多“新女性”形象。比如,身為農場主的芭斯謝芭;做擠奶工的苔絲;當老師的淑……這些女性有著美麗、迷人的特質。哈代以此來對比出那些沒有瑕疵的維多利亞“正派女性”形象,從而糾正人們對女性的“不正確”認識,恢復真實的女性。
芭絲謝芭在前往她姨媽家的路上偷偷拿出鏡子欣賞自己的容貌,表現出她的愛美與虛榮。人們看到了一個正常女性應有的天性:女性渴望被人欣賞和崇拜。她不愿受束縛,她不愿像“淑女”那樣騎馬。她繼承叔叔的莊園之后,就對所有的雇農說:“你們現在有了一位女主人,而不是男主人……我根本不需要管家,我已經下定決心用我自己的頭腦和雙手來管理一切。”(哈代,2008)她親自去卡斯特橋集市上推銷她的作物,與買家討價還價。集市上農場主伯德伍德對她的漠視傷害了她的自尊,于是芭絲謝芭耍了個花招,給他寄了張匿名情人節卡片。表面上這像是一個女孩輕佻的沖動行為,但根本上是對這個地區最受尊敬的男人甚至他所代表的男權社會的挑戰。從作者傾注、顯現的情感意蘊與價值取向來看,女主角芭斯謝芭則被形塑為具備自由人格、富有奮斗精神、攜帶某種本真野性的“祛魅者”,其面對父權意志與男權秩序的壓迫,采用了身份自證的方式去抗爭,即通過展現自己能夠獨立生存、且可以獲取豐厚的經濟收益,從而贏得公眾尤其是男性群體的尊重與認可。(韓淑俊,2020)
伯德伍德是威瑟伯里一位富有且受尊敬的農場主;奧克曾經是個很有前途的農民。他們倆都向她求婚,但都被芭絲謝芭拒絕。因為他們只想讓她做一個賢妻良母,前者想把她變成“芭絲謝芭·伯德伍德”,后者想把她變成“我的妻子”。他們誰也不希望她成為獨立的“芭絲謝芭·伊芙丁娜”。而這些是芭絲謝芭所抗拒的。
奧克向芭絲謝芭求婚時,描述了他理想的婚后幸福生活:“我有一個又漂亮又舒適的小農場,一兩年之內你就會有一架鋼琴——我要好好地練習吹笛子,好在晚上與你一起合奏……我們還會有漂亮的花和鳥……還有一個黃瓜架子——像那些紳士和淑女一樣……在家中的爐火旁,你舉目時,我必在那里。我舉目時候,你也必在那里。”(哈代,2008)奧克認為這是一個女人所渴望的生活。而這種生活的代價是失去自由,成為男人的財產。芭絲謝芭表示自己“討厭被認為是男人的財產”。
她選擇了特洛伊中士,一個沒有穩定收入、來歷不明的人。按照傳統婚戀觀,他絕不是理想的丈夫人選。芭斯謝芭卻不顧人們的質疑嫁給了他。她有資本隨心所欲,嫁給讓她動心的人。特洛伊只著眼于即時即刻的現世浮華,只追求眼前的享受。(楊堯維,2020)這樣的男性也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所以農民們不喜歡他。但恰恰是這種不羈迎合了芭斯謝芭不愿受拘束的心理。婚后,特洛伊甚至還得依靠芭斯謝芭的財產生活。芭斯謝芭的愛情選擇體現了她反抗父權社會,保護自身獨立的精神。
經濟上不獨立,“自由”如同沒有根基的浮萍,婦女終究無法擺脫對男性的依賴。正因為經濟上不依附于他人,芭斯謝芭才能按自己的意愿選擇、設計自己的愛情及生活。
三、淪為“舊女性”
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為二十世紀女性主義翻開了新篇章。她認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波伏娃,1949)。讓一個獨立自主的女人逐漸變成一個被他者化的女性,是“整個社會文明”。
芭斯謝芭繼承了一座農場,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按自己的意志選擇了伴侶,似乎將有一個理想的結局。而范妮的死拆穿了最大的謊言。
特洛伊的花言巧語滿足了芭絲謝芭的虛榮心,甚至讓她錯誤地認為他們是反抗傳統的“同盟”。然而,隨著特洛伊漸漸暴露他的真實人格,她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在范妮的尸體前,特洛伊無情地對芭絲謝芭說:“你對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算不上。”(哈代,2008)——特洛伊不僅欺騙了芭絲謝芭的愛情,還背叛了她的信任。他從未尊重過芭絲謝芭,更不用說支持她的信念。特洛伊走后,農場主伯德伍德重新瘋狂的追求芭絲謝芭,直到特洛伊戲劇性的回歸逼瘋了伯德伍德并槍殺了他。現實的殘酷讓芭絲謝芭感到孤獨而絕望,她所有的信念被徹底否定。她逐漸失去了反抗父權社會的勇氣和信心。
芭斯謝芭最終嫁給了奧克。這看似是一個好的結局。但人們忽視的事實是:二人的婚姻象征著一個“新女性”向“舊女性”的轉變。她和奧克的結合實際上是她接受傳統道德規范的開始。
對于飽受打擊的芭絲謝芭,奧克或許是她最理想的丈夫——他善良、誠實、勤奮,而且非常愛她。每當芭絲謝芭遇到麻煩,他總是義無反顧地幫助她。特洛伊死后,芭絲謝芭一度消沉,是奧克一直在幫她打理農場。當她聽說奧克要去美國時,居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無助,為要自己一人管理農場而恐慌。這和小說開頭的那個芭斯謝芭截然不同。奧克告訴芭絲謝芭,所有的人都認為他會娶她。芭絲謝芭脫口而出:“這樣說真是太荒唐了——太快了!”(哈代,2008),說明潛意識里,芭絲謝芭不想嫁給奧克。然而,她馬上改口:“‘實在是太快了’才是我想說的……我也請你原諒!”(哈代,2008),因為她現在不得不依靠男人了。這種矛盾反映了她開始無奈地對傳統父權屈服妥協,并依賴男性。
婚后的芭斯謝芭是什么樣的?婚禮當天,“在蓋伯瑞爾的要求下,她今天早上把頭發梳成幾年前奧克在諾科姆山上見到她時一樣。奧克笑了,芭絲謝芭也微微一笑(她現在很少肆無忌憚地放聲大笑過了)。”(哈代,2008)——原來的芭絲謝芭消失了,只留下一個失去財產、野心和自由的傳統女子。現在她只是“加百列·奧克的妻子”,一個沒有名字的女人。
四、結論
芭斯謝芭與三個男性的糾葛中,男性贏了;女性失敗了,敗給了束縛她們的社會與文化。芭斯謝芭從開始時女性意識高揚到最后向傳統低頭,一步步按照父權社會的規范變成“舊女性”,放棄了自我意志和權利。“女性終歸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便是“宿命論”在該小說中的體現。因此,《遠離塵囂》是一部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更是女性的悲劇。
哈代將社會對女性的束縛描寫得淋漓盡致。他贊美女性的力量和激情。但女性總是被忽視,被定義,被支配;男性左右著女性的經濟、地位甚至命運,終其一生也難逃命運的捉弄。哈代試圖告訴人們,是社會環境粉碎了一個女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在“宿命論”背后,是作者企圖從另一個角度激起讀者內心的波瀾,讓群眾反思社會對女性的壓迫。
芭絲謝芭雖未能擺脫父權制的擺布,但她有過決絕的抗爭。無論結果如何,抗爭過程是有意義的。這是哈代埋藏在故事中的那顆名為“希望”的種子。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我們如今看到了一個和維多利亞時代不同的社會與許多實現自我價值的“新女性”。然而,不平等依然存在,未來的抗爭之路還很長。因此哈代在作品中涉及的許多社會問題,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討論意義。
參考文獻:
[1]韓淑俊.本真呼喚·權力祛魅·自我追尋:《遠離塵囂》中的生態話語與主體建構[J].電影新作,2020,(02):72-75.
[2]秦豫晉.一只覺醒卻永遠被困的鳥兒——對《遠離塵囂》的女性主義解讀[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9(1):26-29.
[3]托馬斯·哈代.遠離塵囂[M].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
[4]王曉娜.哈代早期愛情觀在《遠離塵囂》中的滲透與體現[J].文化學刊,2019,(03):135-137.
[5]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II)[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
[6]楊兆維.現實的“塵囂”該不該“遠離”?—— 《遠離塵囂》中托馬斯·哈代的“現實主義”傾向[J].國際公關,2020,(05):186-187.
作者簡介
鄧宇萱(1999-),廣東省深圳市人,研究方向:語言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