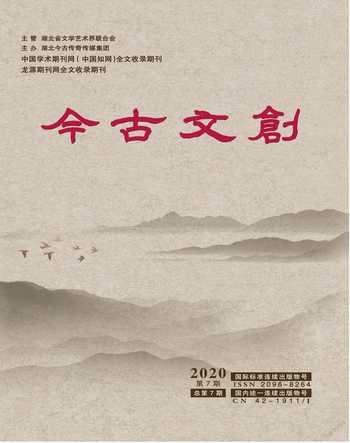論《達洛維夫人》中的空間敘述藝術
劉文艷 楊雁惠
【摘要】 當前,文學作品的敘事學研究日益關注空間理論。本文通過文本細讀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討了小說《達洛維夫人》中空間敘述藝術,分析了在大本鐘報時的物理時空下兩個主角人物的平行敘述線索,為空間理論與文本分析搭建了研究平臺,對今后敘事學的空間研究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關鍵詞】 空間敘述;《達洛維夫人》;意識流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07-0029-02
一、前言
柏格森(1965)對“時間流”的研究將學者們對時間的關注推向了高潮,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以意識流小說為代表的現代小說的創作和研究。敘述學界已對時間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諸如托多洛夫率先將敘事時間劃分為“時間”“語體”和“語式”三大范疇,熱奈特進而完善了敘事時間的研究體系,建立了“順序”“時距”“頻率”等一套標準的敘事時間研究術語。相比較而言,在文學批評和敘事研究領域中,對時間的空間意識還比較薄弱。20世紀,列斐伏爾在《空間生產》一書中首次提出“空間轉向”的概念(Lefebvre, 1991)。隨后“空間轉向”催生了廣泛的“空間研究”浪潮,“空間”問題開始受到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越來越多的關注。
《達洛維夫人》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代表作之一,被認為是意識流的經典之作。整個故事并不是按照線性的敘事順序排列,而是在六月的某一天,處在不同空間位置的人物心理活動片段的集合。以人物的意識流方式描繪了20世紀初倫敦從上流社會到普通大眾的倫敦社會全景。伍爾夫運用了“時間的空間化”等獨特的敘事技巧,使用某個特定的刺激作為連接點,從一個場景切換到另一個場景,從一個角色的意識切換到另一個角色,情節在同一時間展開并擴展到多個空間層面。多個事件幾乎同時發生,不同人物在同一時刻的不同反應被相互聯系在一起,將不同場景中不同人物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井然有序的空間結構。本文將主要探討小說中以大本鐘報時聲為準的物理空間和兩位主角人物的心理空間,在共同的物理時空下兩條平行的敘述線索。
二、大本鐘的物理時空
整部小說的故事脈絡是發生在一天的時間進程中,故事始終貫穿著傳統的時間線性順序,即大本鐘的物理時間,使讀者可以在紛繁錯落的意識描述中抓到現實時間的主線。大本鐘響亮的報時聲,既可用來表述現時當下的物理時間,又可把人物的心理活動從聯想拉回到現實,進行人物意識流的視角轉換。伍爾夫通過這種方式將時間和地理位置結合起來,將許多不相關的人物聯系在一起。
“聽!鐘聲隆隆地響起。開始是預報,音調悅耳;隨即是報時,千準萬確;沉重的音波在空中漸次消逝”(Woolf, 2002:3)。小說中,倫敦的大本鐘一共鳴響了9次。通過9次的物理報時,我們可以梳理一下的故事線索:早晨6點克拉麗莎出門采購,上午10點汽車追尾事件,11點彼得去拜訪達洛維夫人,11點45,賽普蒂默斯在攝政公園,12點賽普蒂默斯在診所接受精神治療,下午1點30,休·懷特布萊德和理查德·達洛衛去參加布魯頓夫人的午餐;下午3點,克拉麗莎在家準備晚禮服和晚宴,傍晚6點,宴會開始,接待眾多來賓,席間聽聞賽普蒂默斯的自殺,最后一聲鐘聲響起時,克拉麗莎得知賽普蒂默斯的死訊,躲在閣樓臥室里思考生與死的意義。
伍爾夫借助大本鐘作為空間敘述藝術表現的手段——象征性意象,通過對具體事物的描寫來達到象征或暗示的目的。小說中屢次描述大本鐘,一方面渲染當地的氣氛和畫面,更重要的是象征眼前的現實,把人物從意識或幻想中喚醒。例如,賽普蒂默斯在攝政公園正幻想著他看到了穿著灰衣服的戰友,“當下,鐘聲敲響了:一刻鐘——十二點差一刻了”(p.52)。大本鐘是連接意識與現實之間的媒介;同時,也是在敘述過程中將一個人物的意識轉到另一個人物上的轉折點。譬如在大本鐘第三次敲響時,“這時,大本鐘鏗鏘有力的鐘聲在他們之間鳴響,報告半點鐘,猶如一個強壯、冷漠、不近人情的青年正使勁地左右開弓扯著啞鈴”(p.35)。借助鐘聲的敲響,作者將筆觸從克拉麗莎幻想嫁給舊情人彼得轉到了彼得對克拉麗莎感情的回憶。在大本鐘報時的物理時空下,故事時間沿著鐘表時間進行,故事發展有了清晰明確的線性順序。讀者才能在人物意識流動再現過去、現在、將來之間的生活場景轉換中依舊思路清晰。伍爾夫通過鐘聲的震懾,將不同人物的思想意識進行彼此轉移。此外,借助汽車的爆炸聲、飛機在空中盤旋的轟鳴聲,伍爾夫將同一時刻不同空間下毫不相關的人物之間進行自由轉換和相連,擴大了敘事范圍。
三、主角人物的心理時空
小說中,伍爾夫將物理時空和心理時空交織在一起,在大本鐘報時的同時,人物在各自的心理時空中穿梭馳騁,相互滲透、彼此交融,塑造出豐富的人物形象。小說《達洛維夫人》中存在兩個主要人物,達洛維夫人克拉麗莎和精神病患者賽普蒂默斯。實際上,二者是未曾謀面、毫不相干的兩個人,同時又是惺惺相惜、彼此相似的兩個人。伍爾夫在《達洛維夫人》中采用了兩條平行的敘事線索,第一條線索是以克拉麗莎為中心,從早晨出門為宴會采購到晚宴結束的一天生活;第二條線索是精神病患者賽普蒂默斯在妻子的陪同下去醫院治療,傍晚回到家卻跳樓自殺的故事。
克拉麗莎和賽普蒂默斯是社會身份和生活經歷完全不同的人,一個是生活優越的貴夫人,另一個是生活窘迫的退役戰士。伍爾夫以兩個人物的對立設置了兩個平行敘事空間。然而,克拉麗莎和賽普蒂默斯也存在相同之處,他們都飽受精神折磨,迷惘于生命的意義。
表面上,克拉麗莎是個熱衷舉行晚會的“完美女主人”,舉行宴會她是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因而克拉麗莎覺得舉辦晚會是“一種奉獻和創造”(p.103),這“給了她一種成就感”(p.35)。在晚會上,克拉麗莎是萬眾矚目的中心,她感到“雀躍和閃閃發光”(p.144),感到“當下的陶醉和心臟神經的擴張”(p.145)。實則,聚會的盛況就像鏡子中的幻象,是克拉麗莎想象的虛構空間,每當她離開聚會上樓時,她感到自己“像是修女隱退”(p.29),感到強烈的孤獨感和生命的空虛感。她自省道:“這個她稱之為生活的東西,對她來說有什么意義?”(p.103)。
賽普蒂默斯與克拉麗莎一樣存在對生活的孤獨感與恐懼感。賽普蒂默斯懷著保衛祖國的一腔熱血去前線參戰,而在戰爭中目睹了殘忍和血腥后,他的想象與殘酷的現實脫節。退役后,患有戰爭遺留下來的精神創傷,賽普蒂默斯的腦海中常浮現出他在戰爭中犧牲的朋友埃文斯,看到他在倫敦飄蕩,在柵欄后張望,在家中踱步。賽普蒂默斯還聽到麻雀在唱歌,看得麻雀在向他招手,他大聲呼喚人們要停止戰爭、珍愛生命。賽普蒂默斯的內心活動反映出了人們對喪失親友的悲痛和對和平的渴望。最終,在現實的折磨下,賽普蒂默斯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就像最后一次鐘聲敲響時,克拉麗莎得知他自殺后,覺得自己很像這個年輕人,替他感到高興,“他拋棄了生命,而她們繼續活下去。鐘聲還在響,滯重的音波逐漸消逝在空中”(p.103)。此時的鐘聲象征著生命一直延續向前,鐘聲還在持續,就像是無盡的時間長流不斷地向前涌進。
賽普蒂默斯的死使克拉麗莎徹底意識到了生活的虛假和真實的自我。她突然發現“晚會的光彩蕩然無存,獨自穿著華麗的禮服進來是如此奇怪”(p.152)。她頓悟到“狂歡消退,只剩她獨自一人”(p.153)。她意識到“雖然她熱愛晚會,能感受到它的激動和刺激,但這些表面上東西,很是空虛”(p.145)。當聽到塞普蒂默斯自殺時,她默默走進臥室,在這個安靜、不受干擾的空間里思考生與死的意義。克拉麗莎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生命在每天無聊的閑談中湮沒,而那年輕人卻通過死亡保留住了生命的核心。她在死亡的沉思中得以蛻變,重新理解了生命的意義,對生命的流逝不再感到畏懼,表現出豁達的人生態度。隨后克拉麗莎振作起精神,從臥室踅回客廳。在小說結尾,兩條毫無交集的平行線因靈魂相通和對生死的思考而匯聚在一起。伍爾夫采用平行的敘事結構,在最后通過主題升華將平行線凝聚在一起,展現出深遠的生命意義。
四、結語
《達洛維夫人》是意識流小說的經典之作,伍爾夫對敘事結構的獨特處理技巧,使讀者可以隨著不同人物的意識跳躍,自由穿梭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馳騁在三十多年的時間長流中,游歷人物在不同時空下的內心和人生,同時伴隨大本鐘響亮的報時聲,不至于在紛繁錯落的長河中迷失,精準地回到現實當下。每個人物不同的心理時間都被賦予了空間性,因而三十多年來的一段段往事得以在被賦予了空間性的時間片段里延綿展開。在物理時空下,大本鐘的報時聲推動了情節發展;在主角人物的心理時空下,身份和生活經歷互補卻毫不相干的兩個平行人物產生了靈魂的互通,小說主題也在此匯聚,對生與死的意義的思考深化了小說的思想內涵。外部的物理時空與內在的心理時空彼此相輔相成、互相滲透,極大地增強了小說的整體性和空間感,這種絕妙的空間敘述藝術使《達洛維夫人》成為當之無愧的意識流小說經典之作。
參考文獻:
[1]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 S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2]Woolf, V. Mrs. Dalloway [M]. New York: RosettaBooks LLC, 2002.
[3]Bergson, H. Duration and Simultaneity [M].Leon Jacobson (tran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5.
[4]董曉燁.文學空間與空間敘事理論[J].外國文學(2):117-123.
作者簡介:
劉文艷,女,漢族,山東臨沂人,天津財經大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語料庫語言學。
楊雁惠,女,漢族,山西朔州人,天津財經大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語料庫語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