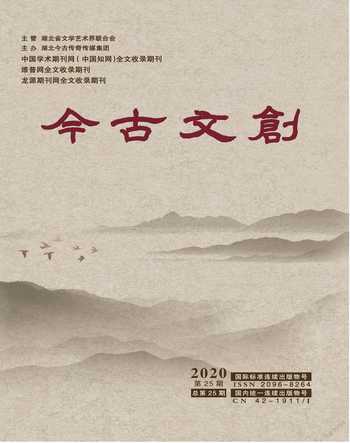淺析孟子的天命觀
【摘要】 孟子的天命觀是對先秦時期天命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在他看來,天命是不可捉摸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在順應天命的同時,在解決問題時要“盡心”,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但不可違背天命。孟子的天命思想豐富了儒家學說,為個人與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理論依據,對后來的哲學思想產生了重要作用,也為我國的民主思想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孟子;天命觀
【中圖分類號】B22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25-0052-02
一、孟子之前天命觀的發展概況
“天命”是儒家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先秦時期的哲學家們討論的中心話題。“天命”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源于遠古時期人們對神靈的敬仰。其中“天”是指最高的統治者,在給予人民關懷的同時,以道德為標準,對人間進行賞罰;“天命”即“天之所命”,也就是上天的命令,是根據人的道德水平來決定天命的授予或者剝奪,人們只能通過提高自身的修養來達到“祈天永命”的目的。“天”本來是自然之天,是客觀存在的,在這里卻被意化為統治世界的最高主宰,使其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意志和權力。
隨著時間的推進,到了春秋時期,“人”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凸顯,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是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緊密聯系的。春秋時期社會動蕩、戰爭頻繁,周天子名存實亡,出現了諸侯爭霸、大夫掌權的局面,從而使這種所謂的“天權神授”的社會等級制度產生了動搖,人們逐漸意識到人事與神意天命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人事的發展與變化取決于人自身的努力程度。這時的“神”不再是絕對權威,而變成了一種象征,人的意志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彰顯。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儒家學說的創始者,更是中國思想文化的奠基者。孔子的天命觀部分繼承了殷商和西周時期的主宰化的天命觀,與此同時,又更加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認為人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以及運用某些人生體驗和生活閱歷的經驗來達到“知天命”的目的,但是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知天命的。受到西周時期天命觀的影響,他相信“天”,說“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天”具有至高的權威,是有意志的,可以主宰人間萬物,并主張“畏天命”,提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觀點;而孔子本人思維嚴謹,尊重客觀事實,對天命鬼神敬而遠之、存而不論,持有一種懷疑的態度,這是孔子天命觀的獨特之處,他提出“天道遠,人道彌”,認為既然神靈之事難以捉摸,無法解釋,倒不如將“天”“帝”“鬼”“神”的問題拋開,把關注的目光投向可以看到、可以感知的人世上來,用“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的態度來對待神靈之事。在此基礎上,又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觀點,最終得出“務民之意,敬鬼神而遠之”的結論。孔子的天命觀雖然有一定的階級局限性,但是他將人的思想意志作為重心,對于遠古時期具象性的神靈信仰只是保留了敬畏的態度,并且以此來提倡仁愛、誠信的道德品行。這種對“人”的關懷和重視為不僅為儒家的人學思想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對孟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帶來了一定的啟示。
二、孟子的天命思想
孟子,戰國鄒縣人,相傳是魯國貴族孟孫代的后代,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他曾游說齊、梁、魯、鄒、滕、薛、宋等國,做過齊宣王的客卿。
殷周的天命觀對儒家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孟子的天命觀是對孔子天命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一方面,他承認“天”具有主宰萬物的能力,在《萬章》篇中有這樣的記載:萬章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之”又進一步解釋道,“昔者堯薦舜于天而天受之。”在這里,“天”就成為舜得天下的根本;另一方面,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指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在孟子看來,發展人的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對天命有所了解。與此同時,他認為人的道德品行是天的性質的一定表現,人便可以以此和上天溝通,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
首先,孟子認為“天命”是決定一切事物發展的力量,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這里的“天”和“命”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客觀形成的,包括其蘊含的某種不確定的神秘力量。人們被這種神秘的力量所支配,從主觀上說是人自身的“命”,從客觀上說是“天”的旨意,于是,孟子就將“天”與“命”放在一起合稱。孟子指出:“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面對“天”,人們是無法把握的,也是難以捉摸的,所以人們只能接受現狀、順應天命,并對此帶有一定的敬畏之情。倘若違背天命,就會受到懲罰或被天所拋棄,這與孔子提出的“畏天命”是一致的。
孟子強調人的力量,注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他將“命”分為“正名”和“非正命”,在《盡心上》中他指出:“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酷死者,非正命也。”雖然天和命都是人不能左右的,但人在天和命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動、無能為力的,如果人的所作所為遵命運的必然規律,不管結果怎樣,都是獲得正命的;相反,如果人一意孤行,明知道危墻有倒塌的危險,卻還要固執地立于其下,結果因此而失去性命,或者是因為犯罪而被處死,這些都是非正命的。所以,孟子主張“人性善”,這種“性善”也是一種良知和良能的體現。他所說的“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的意思是說人的德行是先天的,就像人為什么可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因為先天本來就是如此,是不能反駁的,也是沒有什么道理可循的。就是因為“天”的這種無可反駁,人的性善才更加體現出它的必然性,人們只能接受和遵循,從中體會“思誠”的含義。這一學說首次對人的德性的形而上進行闡發,對于宋明理學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盡管人的“性本善”來源于天命,是一種天性的顯現,而世間的一切并不都是“善”的,那么“惡”又是從何而來?在《孟子·告子上》中,有這樣一句話:“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矣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天之所與我者。”這句話明確地指出先天賦予人的“善”只是“善”的基礎,人在現實生活中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影響,如果人不能發揮其“心”作為神明之主的作用,就會被事物的表面現象所蒙蔽,人的道德品行就會遭到破壞,也就是說,人能否將先天賦予的“性善”發揮和表現出來,關鍵是看能不能發揮“心”的“思”的作用。因此,孟子強調心的作用,面對學問之道,只有盡心,才能進一步感受天的旨意,從而深刻理解“善”的含義,這樣才是真正的順應天命。不難看出,孟子的天命思想并不是一味地要求人們“聽天命”,而是在天命賦予人的“善”的本性的基礎上,要求人們在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時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將這種“善”的天性進一步發掘,用這種積極的方式來“知天命”,并以此來指導人的思想和行為,提高人的品性修養,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
孟子強調“心”,主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那么事情發展的結果是由人的努力程度來決定的嗎?答案是否定的。對于社會發展而言,孟子說“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就是說努力做好自己的事,至于成功與否就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了;他還指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從這句話中我們既能讀出孟子眼中君子的豪氣,更能看出他對天命的無奈,因為天下是否能夠得到有效治理,他也是沒有能力去把握的。從個人的角度而言,孟子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意思是人積極追求自身具有的善性是一定能有所收獲的,而對于其他的一些身外之物,即使努力追求也未必能夠得到。
其次,孟子天命觀中另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其“重民思想”,這是他將“人”的力量與具有主宰性的“天”相結合的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集中體現。孔子就很重視民,表現在《論語》中的:“子之所重,民食喪祭。”孟子在此基礎上,將人民的意志提高到天命的高度,提出了眾所周知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他充分認識到民眾的重要,指出民意就是天意,是不可違背的,也是必須順應的,皇帝只有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實施仁政,才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否則,失去民意的支持,必將導致國家的滅亡。這時的“天命”不再只是上天的意志,而是通過民意來表達的,是以重民的思想為指導,實行仁政為手段,最終達到“保民而王”的目的。
三、結語
綜上所述,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以來的儒家的天命觀,與此同時,又更加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和道德倫理自覺性的發揮,從而形成了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天命觀,為神秘的“天命”注入了人性的“道德”因素,為道德宗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他將人的性善歸結為天命的安排,從另一個角度上說明天命也是性善的,從而為人類主動追求“善”,社會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開辟了道路。孟子將“善”看作是天命的本性,每個人先天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即使人犯了錯誤,只要本性是向善的,都會悔悟和改正,這不僅從心理上樹立了向善的信心,更從思想上為保持優良傳統,提高道德覺悟奠定了基礎。他的民本思想是現代民主思想的前提,要求以民為天,統治者必須順應民意,以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作為治國的根本,從而形成“君為民,民愛君”的良性循環。這已經與現代的民主思想很接近了。孟子的天命觀具有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在體現天命的神秘性的同時,又給予了它人文的關懷,在孔子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人的主體性的重要性,在豐富儒家思想的同時,促成了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優良傳統的形成,對于提高人的道德品行及個人思想修養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2]楊澤波.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道德底蘊[J].天津社會科學,2006,(02).
作者簡介:
王力博,女,漢族,甘肅平涼人,講師,文學碩士,研究方向: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