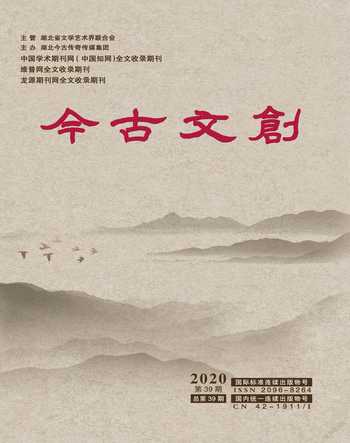西夏漢文楷書碑刻賞析





【摘要】 西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西夏時期相關石刻資料的出土,學界對于西夏社會各方面的了解都有了進一步加深。其中,西夏時期的漢文楷書碑刻不僅具有歷史價值,還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因此,對西夏出土的漢文碑刻進行書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運用圖像對比的方法,對碑刻文字進行分析。從筆法、字法方面指出西夏漢文楷書的特點,并說明與中原書法的關系。
【關鍵詞】 西夏漢文;楷書;碑刻;書法
【中圖分類號】H123?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39-0072-03
一、引言
西夏是公元11世紀至13世紀初,位于我國西北地區的一個政權,共歷10主,存在190年。黨項及西夏存續期間,在不斷地學習、借鑒、模仿中原王朝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黨項和西夏文化,為中國古代多元的民族文化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采。[1]
隨著西夏石刻資料的出土,學者們對西夏石刻資料的整理研究也不斷深入,全面真實地展示了西夏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和文化等,同時彌補了西夏研究過程中的很多缺失。
其中,西夏文書法碑刻和西夏漢文書法碑刻更是成為中國古代碑刻書法藝術的有機組成部分。但目前關于西夏石刻資料的研究多側重于考古和文學領域,學者們關于西夏時期書法藝術價值探討的文章也集中在西夏文方面。對于西夏時期的漢文書法,尤其對漢文楷書碑刻還鮮有研究,因此本文將著重對西夏時期漢文楷書碑刻的書法藝術價值進行分析。
二、西夏漢文碑刻書法研究
隨著西夏政權的相對穩定,其社會生活方式在發生變化的同時,文化藝術也得以蓬勃發展。
西夏的文化藝術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其書法也是以西夏文和漢文楷書為主的書法藝術,如銀川市西夏王陵出土的西夏文字石碑殘塊、漢字石碑殘塊和永寧縣閩寧鎮西夏墓出土的漢字石碑殘塊等。
出土的石刻形制不一,有墓志、碑銘、經幢等;書法風格多樣,有勁秀的秦代小篆風格、飄逸的北魏造像風格和精美遒勁的唐楷風格。碑刻字體以楷書為主,有少量隸書碑刻和篆書碑額。
西夏出土的漢字碑刻大多為殘塊,但仍能從中發現一些寶貴的信息,窺一斑而知全貌。
首先引起筆者注意的是幾塊頗具北魏風格的漢字殘塊拓片。閩寧鎮西夏墓出土的殘碑(拓片)(圖2),從整體風格上來說與北齊天保三年(552年)的《牛景悅為亡人李景仲造石浮圖記》(圖1)風格相類。
總體上呈方整樣式,字形偏古但卻已完全褪去古隸的波磔,兩個“人”字可以看到有清晰的“捺角”,已是明顯的楷書樣式。用筆含蓄,但同時充滿了意趣,比如“旌”“旗”二字。字的結體也相對比較疏朗,有的筆畫外放,比如“家”“秋”二字,相對于后來高度成熟的楷書風貌來說,這顯得更加古茂而有趣味。
第二種(圖5)是接近隋代墓志的風格,比如隋文帝仁壽三年(603年)立的《蘇慈墓志》(圖3)。
可以看到這張拓片上字的技法更加成熟。字內重心上提,中宮收緊,“持”“及”二字是也。筆畫的起收轉折表現得更加確定,如“未”“司”二處的“鉤”和“及”字的“捺”,清晰的彰顯出一種力量感,整體線條變得纖細、挺拔后,更加具有“善筆力者多骨”的美感。
自衛夫人在《筆陣圖》中提出將書法線條的力量感作為一種美學意象來賞析后,后世的書家對于書法線條的力感就高度關注,像“力為骨體”之類的論述數不勝數。
筆力是書法藝術審美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書法藝術審美的最高要求之一,[2]筆力對書法藝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件作品中所蘊含美學意象,既符合書法審美范疇,同時也表明西夏這一時期的楷書走向更加成熟的方向。
第三種接近顏真卿楷書的風格。1974年于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夏陵區6號陵出的漢字石碑殘塊(圖6)。石質,灰砂巖。殘長63.5厘米,殘寬20厘米,殘厚16.5厘米,陰刻漢文楷書,殘存3行31字。內容為崇宗乾順《靈芝頌》句。上部碑緣飾刻蔓草紋,殘寬11厘米。[3]
此殘碑書法明顯取法于唐人顏真卿的楷書。為了更加直觀地看出此碑與唐楷之間的關系,下文將殘碑中的個別單字做截圖提取,與顏真卿書法作品《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下文簡稱《多寶塔碑》)中同樣內容的單字做對比,從筆法、字法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筆法分析
王陵出土的殘碑中“時”字(圖7)左邊部首部分,豎畫入鋒起筆;橫折鉤筆畫,起筆橫向右上稍微傾斜,頓筆換鋒,自然地在筆畫外部形成一個切面再向下行筆,結尾時有一鉤,《多寶塔碑》(圖8)中這個鉤被結尾的一橫所覆蓋,而這樣書寫過程中的細節卻在這塊殘碑中看得更為清楚;最后一橫露鋒入筆且翻鋒向右上方提,兩碑中的這一筆都是如此。再如“多”字(圖9)和“及”字(圖10)無論是從整體的字形外貌上,還是具體到某一筆畫中的筆法比如起、行、收等,都與顏真卿《多寶塔碑》(圖11、12)中的字十分相似。
又如殘碑中的“首”字(圖13),此字的橫畫仍如《多寶塔碑》(圖14)中般是露鋒側入起筆,二者的發力點都落在入筆后立刻由側鋒轉入中鋒的地方,再向右上行筆,橫畫走勢左低右高;收筆時筆鋒往右下方重按、稍頓,至此完成這一橫畫。
用南宋姜夔《續書譜》中論述真書的“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來品評此處,不為過。還有“首”字,橫畫下點的位置都與《多寶塔碑》中的“首”字的點位置一樣,都在起筆第一點的正下方,用筆上都是由重到輕,點畫都呈三角狀且連接下部分的筆畫,但值得注意的是,“首”字下部“目”字的轉折卻不像《多寶塔碑》中一樣豎直。
從(圖13)筆畫的右緣中可以看出帶有弧度,這與顏真卿另外兩件作品《顏家廟碑》(圖15)和《自書告身》(圖16)中的“首”字類似,此碑的書丹者可能不僅只師法顏真卿一件作品,應是對顏真卿的其他書法作品也有過學習的經歷。
不難看出西夏出土的這塊漢文楷書碑刻中的筆法應是繼承于顏真卿。此外,這塊殘碑中字起收筆的方圓;線條的粗細變化;結字的欹正;以及用鋒、提按等,都充分表明了西夏書法對于唐代書法的學習。
(二)字法分析
從此殘碑來看,西夏時期的漢文楷書結字上,總體亦符合書法審美所強調的中和之美。“効”字在結體上,左部高于右部。
左邊部分的所有筆畫位置皆高于右邊的筆畫位置,且往右上方傾斜取勢,若取右部三個筆畫的起筆位置,會發現處在同一豎線上;而右部三個筆畫的收筆處也處在同一線上,不過呈斜向,雖是一正一斜好似有所調和,但左部實則還是一種傾斜狀態,有隨時跌倒的感覺。這時,右部來加以支撐,整個右部全在左部筆畫之下,又很巧妙的在筆畫之中的空間里進行穿插,每一筆都有自己適當的位置,最后達到“彼此映帶得宜”的效果。
更精彩的是,書者對右部筆畫位置精心布局的同時,為了避免出現高低輕重失調的情況,書寫右部筆畫得同時三次加重書寫力度:即撇畫起筆時露鋒重按;下一筆轉折時第二次重按,將筆鋒完全鋪開進行書寫;在最后鉤的地方再次發力,利用之前已經完全打開的筆鋒將此鉤刻畫得飽滿有力。
這不僅加強了右部筆畫的視覺重心,還將整個字的重心也轉移到了右下部,平衡了整個左部的斜勢。右部的橫折鉤一畫,在結構上是此字的主筆,在字法上亦是整個字的“字眼”所在。調節中和之美時還不失奇正的思想,“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伏,騰凌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
再如“祉”字,同是左右結構、同是左邊部分高于右邊部分,但卻重心上移。此字左部筆畫多纖細修長,重心又在右部,主筆是“止”的中間一豎,若此時左部都纖細則“勢”上會完全被右部所吞噬。
于是左部兩個“點”畫,都不約而同地加重了書寫力度,從而各自成形,達到平衡。此字的結構還有另一細節,即左右兩部中間的豎畫,相互牽制的同時又互相呼應。
一豎畫輕盈巧麗,另一豎畫則表現出粗壯有力,這正如羲之所言“凡作一字……或如壯士佩劍,或似婦女纖麗”。
又有左部豎畫偏長、收筆與走勢相反,故右部豎畫勢向下時做到“點畫出入之跡,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爾”,將矛盾的主張帶到字中,使字具有精神和力量,達到力透紙背的效果,同樣,這也是筆力的體現。
從“効”字和“祉”字來看,二字均為左右結構,但字的結體卻不相同,最后依然在視覺上給人以中正平穩的感覺,這一點上可以說西夏漢文楷書深得唐人楷書法度森嚴、一絲不茍的精髓。
三、結語
姜夔在《續書譜》中說:“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池;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4]是要求書寫時在雙方各自收斂節制中達到調節和適度。西夏漢字楷書碑刻用筆不受字形拘束;結構安排中保持中和之度、平衡之勢;書寫和刻碑過程中結字上的排斥和沖突,通過避讓穿插等手法,得到協調,做到了“彼此相讓,方為盡善”。
在漢字楷書中滲透的陰陽、平衡等哲學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唐代楷書的結字規律、審美范式等,同樣在西夏的漢文楷書碑刻中得到體現。
整體書法風格上,也充滿中和之氣,自始至終以平整秀拔、圓而方、方又圓、正有奇、奇卻不失正的致中極和境界。
從這些西夏時期的漢字楷書碑刻中可以看出,繼承于唐代中原地區的西夏漢字書法具有一定的藝術賞析價值,也是我國古代書法藝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喬娟.論西夏的石刻檔案[D].銀川:寧夏大學,2013.
[2]杜濱.論筆力在書法藝術中的表現[D].蕪湖:安徽師范大學,2015.
[3]李進增.西夏文物[M].北京:中華書局,2015.
[4]崔爾平校點.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作者簡介:
余翔伊,女,漢族,重慶人。寧夏大學美術學院,碩士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少數民族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