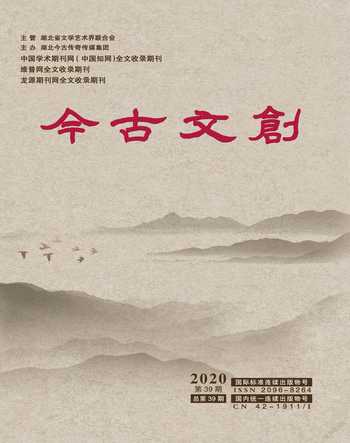音樂對于建筑文化的表現(xiàn)性分析
樊景怡
【摘要】 劉文金先生在《長城隨想曲》中,將具有民族思維的音調(diào)和音樂語言賦予濃郁的傳統(tǒng)韻味,極大程度上增強(qiáng)了音樂表現(xiàn)力,使民族樂器的表現(xiàn)功能有了更大的空間。音樂語言對建筑文化的傳達(dá)在于其表現(xiàn)性、塑造性和多聲部的合奏傳達(dá)性。音樂與建筑在社會功能上有著非傾向性的審美功能。
【關(guān)鍵詞】 音樂;建筑;長城文化;表現(xiàn)性;《長城隨想曲》
【中圖分類號】J605?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39-0075-04
一、前言
文章以民族樂器合奏曲《長城隨想曲》為例,結(jié)合長城文化內(nèi)核,介紹和分析該作品在表現(xiàn)性、塑造性和多聲部的合奏傳達(dá)性上的音樂特性以及該作品在文化方面的音樂化和音響的具象化。
長城作為最能承載國家精神、歷史積淀和人民意志的中國建筑,《長城隨想曲》這部音樂作品在長城作為靈感來源的特殊創(chuàng)作背景之下,更增添了時代意義與無國界的文化標(biāo)簽,民族樂器對于長城的多方位“建造”也將這首曲目打上了中國烙印。
中華歷史文化悠久,以建筑為主題題材的優(yōu)秀音樂作品非常豐富,無一不準(zhǔn)確地使用音樂語言表現(xiàn)該主題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深蘊(yùn)。
本文以《長城隨想曲》為例,探討該曲目的文化及音樂層面的獨(dú)特風(fēng)格和對建筑的表現(xiàn)能力以及對民族精神的深刻反映,目的在于研究建筑與音樂的共同審美特征和建筑與音樂在表現(xiàn)審美途徑的相通性。
二、《長城隨想曲》概述
音樂家劉文金先生在中美恢復(fù)邦交的前夕,于1978年隨同中國藝術(shù)團(tuán)訪美,在第一次踏出國土的路途中,盡管受到了友好的接待也感受到了他鄉(xiāng)的新奇與幻境般的朦朧美,但作者內(nèi)心仍然始終伴隨著陌生與漂泊感,思鄉(xiāng)之情在內(nèi)心如暗流不斷匯聚。
在一次參觀紐約聯(lián)合國大廈的活動過程中,一幅巨大彩色壁毯——萬里長城圖,在一間專為各國重要人物開放的休息廳,幾乎覆蓋大廳正面的整張墻壁,引起了視覺的高度集中。
畫面中的萬里長城氣勢恢宏,有著中國獨(dú)有的歷史氣韻,展現(xiàn)著中華民族偉大的氣魄與璀璨的歷史,觀者無不感到一股熱流涌上心頭。
音樂家劉文金先生也找到了祖國的文化象征在異國他鄉(xiāng)傲然挺立的標(biāo)志,他與二胡演奏家閔惠芬不謀而合地想到應(yīng)用民族器樂表現(xiàn)長城這一歷史古老的建筑所代表的文化內(nèi)涵。
在學(xué)習(xí)大量傳統(tǒng)音樂,比如古琴、戲曲、說唱音樂以及各類民間傳統(tǒng)音樂之后,提煉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神韻”美,利用協(xié)奏曲的表現(xiàn)形式,大量采用中國傳統(tǒng)樂曲的創(chuàng)作技法和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形成若干緊湊、舒展、以及音響層次豐富的整體布局。
長城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guī)模最大的軍事項(xiàng)目之一,是古代中國為抵御塞爾維亞和塞爾維亞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在不同時期建造的。
它建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十一世紀(jì),今天提到的長城主要是指明代建造的長城,從遼西丹東市后山延伸到甘肅省嘉峪關(guān)。
如今,長城的審美魅力在兩面性歷史演變中越來越明顯,實(shí)用軍事功能逐漸削弱,文化的精神作用不斷增強(qiáng),不斷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展現(xiàn)人類的意志和勇氣。長城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象征,也是人類文明與地球和平的象征,全人類都將受益于這一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
它作為古代建筑文化遺產(chǎn),歷來被視為中華民族大一統(tǒng)的象征,是意志、力量與凝聚力的標(biāo)志,同時其背后含有豐富的人文內(nèi)涵,集中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磅礴底蘊(yùn),展現(xiàn)了民族的理想、情懷與價值觀。在歷史推進(jìn)的過程中,長城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凝聚著中國人共同的愛國之心。
《長城隨想曲》展現(xiàn)人民的心靈寄托,在世界格局紛繁變換的當(dāng)今,長城就像每一個具有中國氣節(jié)、中國文化和中國內(nèi)涵的眾多優(yōu)秀歷史建筑一樣,成為人民生活中的具象寄托,而它又作為民族團(tuán)結(jié)的代表象征,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
幾千年來,友好的中外使團(tuán)經(jīng)常在這條古道上旅行,中外文化得以充分融合、交流。長城是世界其他地區(qū)了解中國歷史、文化和民族的最佳起點(diǎn)。
1987年,教科文組織宣布長城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以表明其歷史、文化和人類價值得到全世界的承認(rèn)。
《長城隨想曲》這一優(yōu)秀的音樂作品,正是站在民族歷史的肩膀上而譜寫出的長城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贊歌,在今天也依然具有長遠(yuǎn)發(fā)展的境界,時刻提醒著每一位奮斗者不忘初心、銘記歷史、為祖國事業(yè)添磚加瓦。
三、音樂語言表現(xiàn)性分析
音樂語言對建筑文化的傳達(dá)在于其表現(xiàn)性、塑造性和多聲部的合奏傳達(dá)性。
音樂的調(diào)性之于建筑的規(guī)線,二者的都是表現(xiàn)語言的基石,以建筑為主題的音樂作品是處于兩個客體對象之間的媒介,將同一主題下的建筑與音樂的個性進(jìn)行凝練,音樂語言在此基礎(chǔ)上不斷發(fā)展、交織,最終形成具有人文內(nèi)涵且富有欣賞性的音樂作品。
音樂語言的表現(xiàn)性可以通過樂器音色以及樂器的組合等方式呈現(xiàn)。
開篇以長時間低沉的打擊樂輪奏、弦樂弱顫音、彈撥樂單音重復(fù)、琵琶輪指、京胡長短弓快速交替、擂鼓等等樂器技法,在大樂團(tuán)眾多樂器的共同的烘托之下,仿佛時光正在倒退耳邊掠過的陣陣風(fēng)聲,將聽眾帶入歷史的海洋并逐漸下沉,營造沉浸的氛圍并成為整個樂曲的“地基”,具有緩緩揭開薄紗將要遇見長城這一古老建筑的儀式感。
嗩吶等管樂的第一句旋律給整曲定調(diào),用具有中國樂器特有音色將整曲打上中國標(biāo)簽,并渲染昂揚(yáng)的氣勢。
前19小節(jié),管樂與弦樂交互相成,交叉演繹特性音調(diào),敘述主題,打擊樂鋪墊并不斷推動和展開。
音樂主題對于長城的建筑文化風(fēng)格相呼應(yīng),引出民族氣派的主題。大提琴聲部與琵琶等彈撥樂聲部撥奏開啟第二樂段,切分的節(jié)奏型突出了跳躍性,仿佛看到車馬運(yùn)載著木柱和磚石,沿路有商販叫賣的集體感與動感。
二胡與管樂的音樂旋律在低音聲部的鋪墊下,作為主旋律在框架內(nèi)進(jìn)行宣敘,在厚重的歷史感中帶來一絲輕松的市井生活氣息,彈撥的再現(xiàn)性旋律更豐富了音響效果,增加了音樂樂句結(jié)構(gòu)的趣味性,強(qiáng)調(diào)了音響的具象化。
塑造這一詞語,對于音樂來說是一個常見的用詞,通常說塑造音樂主題的形象、音樂角色的音色塑造和塑造整體框架渲染氛圍等等。
對于《長城隨想曲》這一以建筑為題材的音樂作品來說,并沒有一個鮮明的人物或角色,所以除了上述的塑造,更多的是在歷史中思考長城這一建筑的性格以及它代表的人文內(nèi)涵等深層次的內(nèi)容上著手,在表現(xiàn)長城綿延雄偉的視覺印象的同時塑造具有民族精神的建筑之氣。
《長城隨想曲》在塑造一個具有立體性格的長城方面,運(yùn)用不同民族樂器的獨(dú)特多變的演奏技法,例如琵琶輕巧的挑、低音聲部的半音級進(jìn)拉奏、二胡跳音頓弓和嗩吶的連續(xù)吐音等等,編寫多樣的節(jié)奏型,充分發(fā)揮各樂器在情感表現(xiàn)、音色融合和整體塑造方面的優(yōu)勢。
多聲部的合奏傳達(dá)性方面,音樂與建筑一樣需要具有合理的層次以及適度的空間感,整曲大量運(yùn)用中國樂器,音色獨(dú)特且有辨識度,因?yàn)椴煌闹匾l率范圍,所以也具有框架性,音響效果多元且飽滿。
低音鼓通常在27到146Hz,軍鼓響度為2KHz,吊镲在130到2.6KHz,大提琴合適區(qū)間在300到500Hz,琵琶通常在600到800Hz,二胡在293到1318Hz,笛子頻率一般在220到2.3KHz。樂器的不同與技法的運(yùn)用會影響到頻段的接收,60到100Hz的頻率是低音的基音區(qū),因此,通過配器與編曲在頻率的組合上也與建筑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頻率豐滿則旋律渾厚感強(qiáng),頻率不足會導(dǎo)致音色效果失力,而如果頻率過強(qiáng)則會出現(xiàn)低頻共振造成轟鳴的音效。100到500Hz,包含了和弦根音的頻率和語音的主要音區(qū)頻率,在組織上需要將幅度豐滿,避免發(fā)軟或者生硬單調(diào)。800到2KHz包含接近人聲基音的頻率區(qū)域,通透感明顯順暢感強(qiáng),要注意幅度的調(diào)整,否則會朦朦朧朧,從而缺乏跳躍感。
不同頻率的樂器,通過配器與編曲,像鋼筋一般將聽覺的空間撐開,旋律進(jìn)入到不同層頻率的空間和節(jié)奏中,塑造恢宏的“音樂長城”。
另外,根據(jù)不同樂段的情感方向的不同,音樂對于長城的塑造不止停留在它雄偉的外在,音樂更能表現(xiàn)時代的印記,在長城文化等精神層面,給人深層的感動,構(gòu)筑“內(nèi)心的長城”。
總的來說長城文化通過音樂語言傳達(dá)的有效性在于音樂特有的表現(xiàn)形式與其存在的形式,音樂是時間的藝術(shù),在表現(xiàn)深厚文化意蘊(yùn)的過程中,需要融入時空進(jìn)行表現(xiàn),這就體現(xiàn)在表演的現(xiàn)場性或者音樂的可獲得性和音樂本體美。
《長城隨想曲》作為民族樂器合奏曲,雖然存在的形式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響在文化傳達(dá)方面的可接收性。此類題材音樂的出現(xiàn)要求受眾有一定的歷史知識,良好的綜合素養(yǎng)與較高的欣賞能力,《長城隨想曲》體現(xiàn)出來的長城文化,接受門檻適合大眾,樂曲當(dāng)中體現(xiàn)出的“特性音調(diào)”是民族音樂與現(xiàn)代的融合,具有辨識度的同時擁有廣泛的接受度,不論是在慢板或是快板都運(yùn)用不同風(fēng)格體現(xiàn)了長城建成前后以及在當(dāng)今的多樣人文風(fēng)貌。
長城文化與音樂語言的融合,飽含中華民族神韻的律動感,反映了80年代時人民對文化的深沉思考,展望古老民族的開闊未來,在中西音樂文化中碰撞出絢麗的火花。劉文金先生將京劇“黑頭”腔調(diào)、京劇伴奏旋法、說唱音樂的歌唱性、口語化的北方書鼓音調(diào)等具有民族思維的音調(diào),將語言賦予濃郁的傳統(tǒng)韻味,極大程度上增強(qiáng)了音樂表現(xiàn)力,使民族樂器的表現(xiàn)功能有了更大的空間。
作為我國20世紀(jì)80年代民族音樂的重要作品,在民族樂隊(duì)等方面的發(fā)展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xiàn),是我國民族管弦樂創(chuàng)作的一座里程碑。
四、音樂與建筑文化的共同延伸
建筑常被稱為是“凝固的音樂”,建筑作為一門藝術(shù)與音樂等其他藝術(shù)不斷發(fā)生聯(lián)系。
而建筑與音樂的聯(lián)系很早就有所體現(xiàn),在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中,有一個城邦的一位優(yōu)秀的音樂家,他演奏的琴曲飽含情感同時又技巧嫻熟,色雷斯城中的花鳥蟲魚甚至巖石都因此動容,悠揚(yáng)的音樂在空中回蕩,其旋律凝結(jié)成了建筑一般的模樣,人們便在這音樂凝成的城市里徜徉。
長城隨著山的動勢進(jìn)行建造,雖然是靜態(tài)的空間藝術(shù),但其中與具有獨(dú)特的節(jié)奏感,《長城隨想曲》正是抓住了長城綿延的形態(tài),通過抒情的節(jié)奏演奏出來。此同時,音樂也被稱為是“流動的建筑”。
音樂的創(chuàng)作作品不僅是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情感的單純堆疊和表現(xiàn),優(yōu)秀的作品更是受審美經(jīng)驗(yàn)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探索符號多樣表現(xiàn)的可能性并蘊(yùn)藏主題、象征和寓意在文化語境中的意義。
《長城隨想曲》中的長城文化在樂段與情感的轉(zhuǎn)換與遞進(jìn)中充實(shí)著整曲的文化內(nèi)涵。
音樂的樂理性旨在體現(xiàn)和諧、均衡與邏輯,在建筑中這三點(diǎn)依舊十分重要,羅馬時代的建筑師維特魯夫在建筑理論的第一本書《建筑十書》中寫道,建筑的要素應(yīng)該既功能性強(qiáng)又要堅(jiān)固與美觀(utilitas、firmitas、venustas)。
上述三點(diǎn)相通之處就表現(xiàn)在:第一,音樂與建筑在社會功能上有著非傾向性的審美功能。雖然音樂是以非具象的形式,而建筑則是切實(shí)能夠刺激視覺觸覺等一系列感官的,但其在社會存在方面表現(xiàn)的內(nèi)容都有一定的反映性和還原性,例如將音樂、建筑與政治在同一時期比較,秦始皇仿造被攻陷的國家之皇城,修筑了阿房宮等宮殿樓宇,此類建筑的增多影響到了樂工編制的擴(kuò)大,宮廷音樂與當(dāng)時的建筑共同發(fā)展,反映了那一時期中國古代建筑以及宮廷音樂的高峰。古羅馬建筑與音樂在一定給程度上也都同時反映了樸素莊重的社會意識,客觀表現(xiàn)了社會存在通過新的社會存在展現(xiàn)其自然的思想原則,反映了所在時期人們對于規(guī)律與美的探索。長城的社會存在趨于名片化多元化,《長城隨想曲》作為音樂作品,通過旋律展現(xiàn)中國音調(diào)和中西結(jié)合的創(chuàng)作思想,在審美方面結(jié)合了長城的建筑美與旋律的音樂美;第二,音樂與建筑在社會存在上有著和目的性。受客觀生產(chǎn)力影響,音樂與建筑在不同時期有不盡相同或完備或滯緩的發(fā)展,但不論發(fā)展進(jìn)度如何,人類對于所在社會的有目的的改造是持續(xù)的,音樂與建筑都是改造和創(chuàng)造的眾多形式當(dāng)中的形式類型,自然有著若干功能上的交集。長城等等在某些特定指向性或代表性等具有象征性的建筑,以《長城隨想曲》為代表的在意識以或者內(nèi)容上有著人文內(nèi)涵,傳達(dá)深厚意蘊(yùn)的音樂作品,既是時代、社會的反映,同時也是通過人類能動性的創(chuàng)造在改變和創(chuàng)造新的世界;第三,音樂與建筑都追求和諧的比例。外在方面,建筑的輪廓展現(xiàn)線條美和輪廓美,建筑耗材的質(zhì)感美和組織美,建筑整體的動勢美和協(xié)調(diào)美,建筑四維的空間特性將時間滲透進(jìn)相應(yīng)的空間之中,音樂的風(fēng)格美與意象美,音樂配器的融合美與多元美,音樂樂理的協(xié)和美與邏輯美,音樂的主觀感受性是通過空氣振動傳達(dá)的空間感與音樂內(nèi)容的結(jié)構(gòu)內(nèi)化。
建筑在空間藝術(shù)范圍,空間同時也是解釋音樂對內(nèi)心發(fā)生影響的主要因素。
建筑中強(qiáng)調(diào)比例原則,這是一種形而上的藝術(shù)規(guī)則,當(dāng)代設(shè)計(jì)將空間的概念涵蓋進(jìn)創(chuàng)作原則,成為解釋建筑在藝術(shù)方面對心理影響的一部分。
音樂當(dāng)中的比例關(guān)系,《長城隨想曲》在樂律的基礎(chǔ)上通過旋律追求民族性與和諧,例如3:2、4:3、2:1、3:1、4:1對應(yīng)的五度、四度、八度、十二度、十五度音程關(guān)系。
建筑可以從數(shù)的關(guān)系以及音樂和諧的法則出發(fā),在建筑設(shè)計(jì)與音樂創(chuàng)作間相互借鑒,使得作品充分傳達(dá)思想與精神。
長城文化作為長城與《長城隨想曲》的精神支柱,在兩者的表達(dá)方式中以同樣的內(nèi)容存在,可以將兩者合二為一,表達(dá)明確的數(shù)理原則和抽象的邏輯線條。
五、結(jié)語
音樂的創(chuàng)作、演奏及欣賞,與建筑的規(guī)劃、建造及存在,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共同的審美特性。
這也是為什么通過《長城隨想曲》這首民族樂器合奏曲,可以更深刻的在認(rèn)識長城方面擁有比單純視覺沖擊的優(yōu)勢,優(yōu)秀的以建筑為主題的音樂作品可以得到廣泛流傳和流行,尤其是以民族文化建筑遺產(chǎn)及其歷史文化與當(dāng)代文化的宏觀視野下的結(jié)合,更能發(fā)揮音樂與建筑雙方的優(yōu)勢,在視覺聽覺以及整體觀感的共同作用下,深入人心,力圖在情感層面尋找與創(chuàng)造共鳴。
本文以《長城隨想曲》為例,聚焦長城文化,探討音樂對建筑及其文化的表現(xiàn)性,思考音樂與建筑及其文化在可能范圍內(nèi)的延伸。
近年,許多關(guān)于音樂與建筑的審美共通性的探索,擴(kuò)充了對于交叉作品的實(shí)踐,藝術(shù)家們對這一課題在實(shí)踐和理論上的研究也使得針對性研究擁有更大可能性。
參考文獻(xiàn):
[1]劉文金.樂曲《長城隨想》的創(chuàng)作及其他[J].文藝研究,1984,(4).
[2]吳愷峰.淺析建筑與音樂的歷史相通性以及審美通感[J].科教文匯,2018,(12).
[3]李存波.建筑與音樂的共通共融——評《建筑與音樂》[J].工業(yè)建筑,2020,(6).
[4]閔惠芬.風(fēng)雨同舟筑“長城”[J].樂器,2002,(8).
[5]劉彥玲. “音樂效果”與“音樂建筑”——19世紀(jì)“豐碑性”美學(xué)的源起[J].黃鐘,2018,(4).
[6]馮清華,盧穎.長城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傳承[J].人民論壇,2017,(25).
[7]唐孝祥,陳吟.建筑美學(xué)研究的新維度——建筑藝術(shù)與音樂藝術(shù)審美共通性研究綜述[J].建筑學(xué)報,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