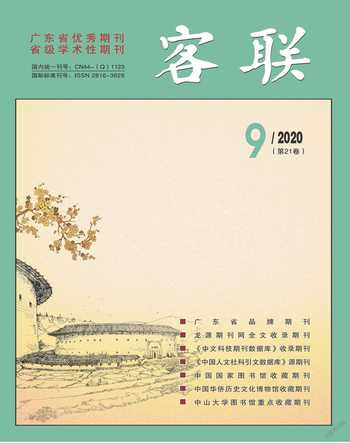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管理及協調發展
胡佳霖
【摘 要】從社會生產實踐出發,唯物主義歷史觀把人類社會理解成一個復雜而又龐大的系統,而各個系統遵循整體性原則為前提,各自發展優化。在不斷的演進過程中,我國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問題較為凸顯,而系統間復雜矛盾的關系將作為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故本文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從實證角度驗證我國環境規制政策下的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收入分配公平問題的矛盾進行探討,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生態環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協調發展
一、問題提出
我國經過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方面交上了滿意的答卷,但同時也付出了不可忽視的環境成本。國外學者研究估計,我國環境污染所帶來的成本損失每年大概占我國GDP的5%以上。
從我國國情出發,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之間的矛盾問題已經較為突出,盡量做到相互作用和諧發展,響應國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但社會系統是一個復雜龐大的系統,在追求協調發展理念的同時,不可忽視的是環境規制的社會效應。社會系統這個有機體牽一發而動全身,環境規制的政策會沖擊到社會經濟系統中各個子系統,從而波及到居民的收入問題。
關于經濟效應,學者們主要從環境規制對經濟增長,外商投資,企業技術創新等幾個方面的影響入手。環境規制政策對于收入分配效應的影響不是中性,且針對不同地區的收入分配影響也有可能因為地區差異性而不一致,故針對環境規制的收入分配效應問題進行研究,從而探究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問題。
二、計量模型和數據
(一)計量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正式環境和非正式環境規制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這一部分用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檢驗,以各省收入不平等水平(Gini)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各省正式環境規制指標(ER)和非正式規制指標(INER)同時納入計量方程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在借鑒原毅軍等(2014)、宋珺等(2020)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構建以下模型:
(二)變量與數據
為了衡量中國各省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選擇各省基尼系數來表示地區內收入差距,基尼系數的取值介于0-1,數值越大表示收入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正式環境規制方面,本文參照余東華等(2016)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污染物排放量,如二氧化硫排放量、煙粉塵排放量、廢水排放量三個單項指標,參照朱平芳等(2011)的綜合指標構建法進行構建。
對于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本文借鑒Pargal et al.(1996)的方法,選取人均收入、受教育水平、人口密度和年齡結構等指標來綜合度量。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文采用系統GMM模型進行動態面板估計。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和收入差距的狀況差異較大,因此本文將樣本數據劃分為東部和中西部進行下一步分析,針對不同區域內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對于收入分配效應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進行檢驗。
首先,從東部地區來看,正式環境規制對于該地區收入分配效應的影響并不顯著,而非正式環境規制有利于縮小該地區的收入差距。由于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第三產業占比較大,能夠抵御部分正式環境規制帶來的調整成本,從而緩解對于收入分配的沖擊。而東部的非正式環境規制強度在全國內也較為凸顯,是由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導致年輕人才聚集,對地區環境程度敏感。
其次,從中西部地區來看,正式環境規制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而非正式環境規制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區會受到調整成本的沖擊,從而影響到地區內的收入分配。這些產業在正式環境規制的作用下,加大技術投資或引入綠色創新技術,對高技術勞動力的需求大于低技術勞動力,從而加大收入差距,帶來收入不平等。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基于2003~2015年全國的省級面板數據,本文從正式環境規制和非正式環境規制角度實證分析生態環境系統對于社會經濟系統下的收入分配平等的效果,并且考慮到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不同,政策波及到收入分配的程度存在差異性。本文研究發現,在全國以及中西部地區,非正式環境規制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收入平等;但在全國、東部以及中西部地區,正式環境規制會加大省域居民收入差距。
本文的研究結論得到以下的政策啟示:一是對于生態環境系統的治理,需要考慮到系統間的整體性原則。因為系統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掣肘,會波及到社會經濟系統,顯著影響到該地區的收入分配狀況。
二是對于生態環境系統的環境規制政策需要因地制宜,針對經濟發展質量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正式環境規制的強度可以以生態環境系統承載能力進行制定,并鼓勵社會公眾參與民間環境保護組織,加大非正式環境規制力度。
三是需要正確認識及處理現存的社會矛盾,社會發展中這種非對抗性的矛盾將貫穿社會發展的全部進程,它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各自演進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不同領域之間的矛盾,基于社會系統研究方法,可以具體問題具體研究,針對不同地區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正確的化解矛盾,力求做到整個社會有機體的統籌兼顧。
【參考文獻】
[1]田衛民.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數測算及其變動趨勢分析[J].經濟科學,2012(2):48-59.
[2]張樂勤.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系統協調視角下的安徽省高質量發展判別及障礙診斷[J].貴州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37(03):35-42.
[3]PARGAL S,WHEELER D. 1996. Inform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4( 6) :1314 -1327.
[4]李幫喜,劉充,趙峰,黃陽華.生產結構、收入分配與宏觀效率——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與經驗研究[J].經濟研究,2019,54(03):181-193.
[5]陳鵬.環境—社會系統管理與可持續發展[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03):9-12.
[6]鄧陽.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基于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J].改革與戰略,2019,35(02):1-6.
[7]安亞軍.社會系統研究方法視角下的環境治理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8,39(27):135-136.
[8]宋珺,鄢莉莉.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研究[J/OL].開發性金融研究:1-17[2020-06-11].https://doi.org/10.16556/j.cnki.kfxjr.20200402.001.
[9]余東華,胡亞男.環境規制趨緊阻礙中國制造業創新能力提升嗎?——基于“波特假說”的再檢驗[J].產業經濟研究,2016(02):11-20.
[10]原毅軍,謝榮輝.環境規制的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研究——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J].中國工業經濟,2014(08):57-69.